

我並不是特別喜歡驚悚故事的人,因為膽小,連翻動書頁時的窸窣聲都猶如驚弓之鳥。《熱帶夜》卻不同,令人顫動的並非來自外在的威嚇恐懼,而是對現實的渺茫無奈,直到一無所有之前,任何事物都可以是唯一的慰藉。
──編笑編哭經營者/B編
趙禮恩的《熱帶夜》是夢、情感與恐怖搭建的馬戲團帳篷,小說使用的元素時而夾雜些許科幻,又時而鑽入怵惕情緒的起源。她理解苦楚,卻能直觀單純地切入遺憾跟幻想交織的邊界。讀這些作品總會使人激動,因為將期待下一秒,乍然下潛後的潮燠與冰涼。
──作家/陳育萱
《熱帶夜》裡的連篇奇想,是一種飛高高。起初是小小的飛翔,輕鬆愉快地深入故事,然後,在沒有預想到的其中一次,會飛得特別高,高得彷彿在時空停止的片刻,可以望進宇宙深處的另一個世界。
而其中有幾個瞥眼,會讓我們在回到地面後,還默默想念著,希望有一天能再造訪。
──小說家/劉芷妤
作者竟然把科幻做成了蛋糕,敲破乾冰巧克力球殼,裡面裝著一層杏仁餅,一層開心果洋梨慕斯,一層甘王草莓……把原本虛無荒涼的科幻經典,填進韓劇《我們的藍調時光》和《我的大叔》那樣友情親情愛情的摩卡奶油餡,令人嘴角失守慘叫媽鴨太可愛了。
──作家/盧郁佳


趙禮恩(조예은/Cho Yeeun)
曾以《疊刀,刀》榮獲第二屆金枝出版社「跳躍時空」徵文展優秀獎、《Shift》榮獲第四屆教保文庫故事徵文展大獎。連續兩年入圍韓國YES 24「韓國文學未來年輕作家」。
從日常題材中獲取靈感,並將偏愛的驚悚、浪漫元素融入其中,形成具有獨特品味的趙禮恩世界觀。她希望她筆下的故事永遠充滿浪漫。目前持續積極創作,思索何謂好的故事。
另著有長篇小說《新首爾公園果凍商人大屠殺》、《水晶玻璃球兜風》,短篇小說集《雞尾酒、愛、殭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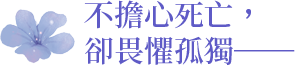

肉與石榴
她聽見一陣咀嚼聲。那聲音彷彿是餓了好幾天的野獸,正著急地撕咬著生肉的聲響。玉珠轉過頭去,望向那未知噪音的來源。她的視線停在店門前的電線杆旁,只見一個披頭散髮的腦袋正在那翻著垃圾堆。
「你在做什麼?」
陌生的光景令玉珠看得目瞪口呆,問句下意識脫口而出。時間已經超過晚上八點,但八月的夜晚依然炎熱。玉珠眼前這名怪漢身材矮小,比起人類,更像是迷了路誤闖城市的野獸。真要說起來,無論是野獸還是男人,對玉珠來說都同樣危險。在胡亂搭話之前,她應該先報警或叫救護車。但玉珠實在沒有餘力回頭看看有什麼地方能讓她躲起來報警,更沒有尖叫求救的力氣。她僅剩的力氣,只夠她張嘴說個幾句話。而且不知是不是因為天氣太過炎熱,連帶使她無法正常思考,才會又一次開口提問。
「是誰在那?」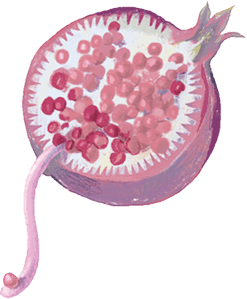 那名披頭散髮的怪漢聽見玉珠的聲音,便從垃圾堆中抬起頭來轉頭望向玉珠。瞬間,玉珠與「那個」對上了眼,那是一張如死屍般毫無血色的臉。
「……」
那有如石榴籽般鮮紅的瞳孔藏著敵意與警戒,被蒼白的膚色襯得更為鮮艷。冷汗流過玉珠的太陽穴,她的雙唇顫抖,只是這次卻發不出聲。她呆站在原地,而「那個」也沒有任何反應。食物因高溫而腐敗的惡臭刺激著鼻尖,此刻,玉珠只想立刻洗去一身的汗水與臭味。她趕緊掏出鑰匙來,顫抖的雙手令她始終無法將鑰匙準確插入鑰匙孔中,這也使她煩躁了起來。先生還在世時,她便要求好幾次要更換成密碼鎖,先生卻嫌記密碼麻煩,始終不肯換掉老舊的鑰匙鎖。他原本就是這種人,痛恨所有陌生的事物,習慣待在熟悉的同溫層裡,所以最後才會那樣離開人世。
好不容易把鑰匙插進孔裡轉開門鎖,很快的,玉珠聽見與往常一樣的門鎖開啟聲。這一帶實在太過安靜,門鎖開啟的聲音顯得更為清脆。玉珠不自覺往旁邊看了一下,恰好從因汗水與污垢而結塊的頭髮之間,看見「那個」似乎正慌忙地不知拿起什麼往嘴裡塞。仔細一看,那是一塊早已爛透發綠的生肉。「那個」似乎餓了很久,瘦成了皮包骨,毫不在乎肉早已腐爛發霉。就在玉珠透過眼角餘光往後頭瞄時,他仍不斷咀嚼著那塊肉。不知不覺間,玉珠接受了外型神似人類的「那個」。也許就像野狗或野獸等野生動物一樣,如今也出現了在野外遊蕩的人類,或者是她不小心將殯儀館的髒東西給帶回家,再不然就是因為先生剛離世不久,連帶自己的精神狀況也出了問題,才會看見這種怪東西。她躲進鐵門內,思考著各種可能。直到進了屋內、關上門並重新將門鎖上之後,她怦怦跳個不停的心才稍稍平靜下來。
玉珠的家是棟屋齡超過四十年的住商混合建築,從餐廳兼肉品處理區的大廳往內走,便是玉珠日常主要活動的小房間。經過原本是廚房的空間,就是一道隨便以水泥砌出來的陡峭樓梯。樓梯一邊通往地下,一邊通往二樓。地下室做倉庫使用,二樓則是她先生生前臥病時待的房間,而在先生生病之前,那裡則是他們的主臥室。沒事的話,玉珠通常不會上二樓。這多少是因為樓梯太陡,爬上去總讓她膝蓋疼痛,但實際上還有其他原因。
玉珠還沒能整理掉先生去世前所躺的那床棉被。生病之後,她先生就像被困在透明監獄裡一樣,只能在那長方形的空間裡動彈不得。一想到當時的情景,她就像是被人一口氣硬塞了一大把年糕似地,痛苦得就要窒息。這並不是在接受先生死亡的過程,而是因為她總忍不住想像自己也同樣躺臥在那的醜態。要說這兩者之間有什麼不同,那就是先生臥病在床時,身旁還有玉珠照顧、賺取生活費、送飯、擦澡,但若是玉珠臥病在床,就只有她自己,沒有人能為她做這些事了,她想必會孤零零地離開這個世界。她深知那使先生喪命的癌細胞也可能在她體內滋長,但憑空想像跟實際聽到醫師如此宣判,又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她在小房間與廚房之間的浴室裡,用大水盆接了些水洗澡。直到這時,她才終於覺得滲入皮膚的那些氣味不再那麼重。玉珠習慣性地將手指湊到鼻尖聞了聞,那洗去了豬腥味,染上獨特自來水味的手指令她感到舒暢。她泡在溫水裡閉上眼,短暫沉浸在思緒中,嘗試思考她的未來、思考是否有可能讓自己不要在悲慘與孤獨之中迎接死亡。年紀比她大十歲的先生因癌症而死,唯一的兒子則在十年前為了創業而前往菲律賓,之後便再沒了消息,連是生是死都不知道。而她也沒有會定期碰面的朋友或信仰的宗教,如果說有一棟位在地區邊陲,可以稱作家的老舊建築是一種幸運的話,那還真是不幸中的大幸。玉珠舀起盆子裡的水,緩緩淋在臉上、肩上、胸上。她將手按在長出腫瘤的大腸附近摸了摸。為了仔細確認這可疑的腫瘤究竟是惡性還是良性、是否轉移到任何地方,醫生表示必須做組織切片檢查。醫生還說,畢竟也有些年紀了,盡快掌握腫瘤的狀況比什麼都更重要。玉珠點點頭表示明白,但走出診間後並沒有預約下一次看診,而是直接返家。無論肚子裡的腫瘤代表的是怎樣一種癌症,她身旁沒有人陪伴、她遲早會死的事實,也都不會改變。既然這最重要的兩件事不會變,那何必去在乎其他的小事呢?年過六十的她,在這樣的情況中還要去想未來的事,實在令她感到很吃力。是因為這樣嗎?是因為身體日漸虛弱,才會看到奇怪的東西吧?玉珠想起進家門前驚鴻一瞥的那雙陌生眼睛。她開始想像那如石榴籽一般鮮紅的眼,以及令人難受到願意翻找垃圾堆的飢餓。
殯儀館的同事之中,也有人經常看到一些異樣的東西。那位同事每次下班都不會立刻回家,而是會去超市或市場等人多的地方走一走,或是先在家門口撒點鹽巴再進門。畢竟是在殯儀館工作,會有這樣的迷信也是無可厚非。不久前,住在隔壁社區的劉氏說,她婆婆死前一天,曾經像個孩子一樣哭訴說晚上有黑色的物體來到她身旁要帶她離開。她婆婆年逾九十又有失智症,因此劉氏當時並沒有多想,不知道為何她會突然想起這件事。
玉珠洗好澡後便來到廚房,從櫥櫃裡舀了一匙粗鹽裝在碟子裡。隨後推開小房間的門,穿越以前用來處理肉品的大廳,並在玄關門前停了下來。越過滿是刮痕的玻璃窗,她看著剛才「那個」所在的垃圾桶。她剛才所目擊的景象並非是夢,只見專用垃圾袋破了一地,裡頭的東西散了開來。「那個」去了哪?她打開只足夠讓一隻腳站出去的門縫,朝外頭看了看。時間已經接近午夜,這位於舊市區邊陲的巷弄沒有任何行人往來,寂靜無聲。玉珠想起同事所說的話,便拿起一小撮鹽往門外撒去。鹽巴掉落在地上的聲音意外悅耳。唰、唰,她聽見不知何處傳來波浪拍打海岸的聲音。她打算繞著房子外圍撒一圈鹽巴,於是便走出大門,接著便再一次面對雙腳併攏,蜷縮在垃圾桶旁打瞌睡的「那個」。
「那個」的身影太過清晰,既不像是幻象,卻又無法斷定是人類。以防萬一,玉珠在它周圍灑了點鹽巴,但那個卻依然靠在骯髒的垃圾桶旁打著瞌睡。玉珠將盤子放在地板上,小心翼翼地跪坐在「那個」面前。油膩膩的頭髮之下,是一張傷痕累累、白到發青的臉孔。玉珠知道,那偶爾會微微顫抖的睫毛下,是一雙鮮紅的眼睛。稍後,玉珠才注意到「那個」握在手裡的腐肉、指節泛紅的乾枯雙手,以及不知穿了多久都沒換過的破爛衣服。玉珠不自覺伸手,她的指尖觸碰到粗糙的皮膚、摸到了肩胛骨的形狀。「那個」確實存在,沒有變得模糊也沒有消失,以一個尚未成熟的孩子的姿態,依然存在於那個地方。
這該怎麼辦才好?這是個炎熱的夜晚,應該不至於凍死。既然已經確認眼前的形體既非鬼魂也非幻象,那玉珠就無法冷眼旁觀。該打電話報警嗎?那警察應該就會過來把那個帶走,應該會把他留置在局裡一個晚上,然後便送到設施去安置。這顯然是最簡單的方法。就在思考下一步時,玉珠聽到「那個」發出的聲音。
嘎吱吱、嘎吱吱⋯⋯
那是人磨牙的聲音。就像心中還留有怨恨的人一樣,那個的嘴裡發出了嘎吱聲。記得現在生死不明的兒子,兒時也曾經像這樣磨過牙。玉珠沒有收回伸向「那個」的手,而是用力地握住了他的肩。「那個」皺起了眉頭,玉珠抓著他的肩搖晃了幾下。蒼白的眼皮突然一陣痙攣,沒過多久「那個」便睜開眼。是剛才看錯了嗎?他的眼不是如石榴籽一般的鮮紅,而是普通的黑色。看他睜著眼的模樣,像極了一個孩子,而玉珠也在一股莫名的情緒驅使之下主動開口說道:
「別待在這,進來吧。」
「那個」眨了眨眼,玉珠十分肯定,他的眼睛在一瞬之間變成了紅色。
怯弱源自於每個難以放下的夜晚,你總能在本書中找到,隱藏心底最深的懼怕。讓我們一起在沁涼深夜中,閱讀這八個交織恐懼與愛的短篇奇幻故事,讓書中有點可愛又浪漫的文字,溫暖你的心窩……
那名披頭散髮的怪漢聽見玉珠的聲音,便從垃圾堆中抬起頭來轉頭望向玉珠。瞬間,玉珠與「那個」對上了眼,那是一張如死屍般毫無血色的臉。
「……」
那有如石榴籽般鮮紅的瞳孔藏著敵意與警戒,被蒼白的膚色襯得更為鮮艷。冷汗流過玉珠的太陽穴,她的雙唇顫抖,只是這次卻發不出聲。她呆站在原地,而「那個」也沒有任何反應。食物因高溫而腐敗的惡臭刺激著鼻尖,此刻,玉珠只想立刻洗去一身的汗水與臭味。她趕緊掏出鑰匙來,顫抖的雙手令她始終無法將鑰匙準確插入鑰匙孔中,這也使她煩躁了起來。先生還在世時,她便要求好幾次要更換成密碼鎖,先生卻嫌記密碼麻煩,始終不肯換掉老舊的鑰匙鎖。他原本就是這種人,痛恨所有陌生的事物,習慣待在熟悉的同溫層裡,所以最後才會那樣離開人世。
好不容易把鑰匙插進孔裡轉開門鎖,很快的,玉珠聽見與往常一樣的門鎖開啟聲。這一帶實在太過安靜,門鎖開啟的聲音顯得更為清脆。玉珠不自覺往旁邊看了一下,恰好從因汗水與污垢而結塊的頭髮之間,看見「那個」似乎正慌忙地不知拿起什麼往嘴裡塞。仔細一看,那是一塊早已爛透發綠的生肉。「那個」似乎餓了很久,瘦成了皮包骨,毫不在乎肉早已腐爛發霉。就在玉珠透過眼角餘光往後頭瞄時,他仍不斷咀嚼著那塊肉。不知不覺間,玉珠接受了外型神似人類的「那個」。也許就像野狗或野獸等野生動物一樣,如今也出現了在野外遊蕩的人類,或者是她不小心將殯儀館的髒東西給帶回家,再不然就是因為先生剛離世不久,連帶自己的精神狀況也出了問題,才會看見這種怪東西。她躲進鐵門內,思考著各種可能。直到進了屋內、關上門並重新將門鎖上之後,她怦怦跳個不停的心才稍稍平靜下來。
玉珠的家是棟屋齡超過四十年的住商混合建築,從餐廳兼肉品處理區的大廳往內走,便是玉珠日常主要活動的小房間。經過原本是廚房的空間,就是一道隨便以水泥砌出來的陡峭樓梯。樓梯一邊通往地下,一邊通往二樓。地下室做倉庫使用,二樓則是她先生生前臥病時待的房間,而在先生生病之前,那裡則是他們的主臥室。沒事的話,玉珠通常不會上二樓。這多少是因為樓梯太陡,爬上去總讓她膝蓋疼痛,但實際上還有其他原因。
玉珠還沒能整理掉先生去世前所躺的那床棉被。生病之後,她先生就像被困在透明監獄裡一樣,只能在那長方形的空間裡動彈不得。一想到當時的情景,她就像是被人一口氣硬塞了一大把年糕似地,痛苦得就要窒息。這並不是在接受先生死亡的過程,而是因為她總忍不住想像自己也同樣躺臥在那的醜態。要說這兩者之間有什麼不同,那就是先生臥病在床時,身旁還有玉珠照顧、賺取生活費、送飯、擦澡,但若是玉珠臥病在床,就只有她自己,沒有人能為她做這些事了,她想必會孤零零地離開這個世界。她深知那使先生喪命的癌細胞也可能在她體內滋長,但憑空想像跟實際聽到醫師如此宣判,又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她在小房間與廚房之間的浴室裡,用大水盆接了些水洗澡。直到這時,她才終於覺得滲入皮膚的那些氣味不再那麼重。玉珠習慣性地將手指湊到鼻尖聞了聞,那洗去了豬腥味,染上獨特自來水味的手指令她感到舒暢。她泡在溫水裡閉上眼,短暫沉浸在思緒中,嘗試思考她的未來、思考是否有可能讓自己不要在悲慘與孤獨之中迎接死亡。年紀比她大十歲的先生因癌症而死,唯一的兒子則在十年前為了創業而前往菲律賓,之後便再沒了消息,連是生是死都不知道。而她也沒有會定期碰面的朋友或信仰的宗教,如果說有一棟位在地區邊陲,可以稱作家的老舊建築是一種幸運的話,那還真是不幸中的大幸。玉珠舀起盆子裡的水,緩緩淋在臉上、肩上、胸上。她將手按在長出腫瘤的大腸附近摸了摸。為了仔細確認這可疑的腫瘤究竟是惡性還是良性、是否轉移到任何地方,醫生表示必須做組織切片檢查。醫生還說,畢竟也有些年紀了,盡快掌握腫瘤的狀況比什麼都更重要。玉珠點點頭表示明白,但走出診間後並沒有預約下一次看診,而是直接返家。無論肚子裡的腫瘤代表的是怎樣一種癌症,她身旁沒有人陪伴、她遲早會死的事實,也都不會改變。既然這最重要的兩件事不會變,那何必去在乎其他的小事呢?年過六十的她,在這樣的情況中還要去想未來的事,實在令她感到很吃力。是因為這樣嗎?是因為身體日漸虛弱,才會看到奇怪的東西吧?玉珠想起進家門前驚鴻一瞥的那雙陌生眼睛。她開始想像那如石榴籽一般鮮紅的眼,以及令人難受到願意翻找垃圾堆的飢餓。
殯儀館的同事之中,也有人經常看到一些異樣的東西。那位同事每次下班都不會立刻回家,而是會去超市或市場等人多的地方走一走,或是先在家門口撒點鹽巴再進門。畢竟是在殯儀館工作,會有這樣的迷信也是無可厚非。不久前,住在隔壁社區的劉氏說,她婆婆死前一天,曾經像個孩子一樣哭訴說晚上有黑色的物體來到她身旁要帶她離開。她婆婆年逾九十又有失智症,因此劉氏當時並沒有多想,不知道為何她會突然想起這件事。
玉珠洗好澡後便來到廚房,從櫥櫃裡舀了一匙粗鹽裝在碟子裡。隨後推開小房間的門,穿越以前用來處理肉品的大廳,並在玄關門前停了下來。越過滿是刮痕的玻璃窗,她看著剛才「那個」所在的垃圾桶。她剛才所目擊的景象並非是夢,只見專用垃圾袋破了一地,裡頭的東西散了開來。「那個」去了哪?她打開只足夠讓一隻腳站出去的門縫,朝外頭看了看。時間已經接近午夜,這位於舊市區邊陲的巷弄沒有任何行人往來,寂靜無聲。玉珠想起同事所說的話,便拿起一小撮鹽往門外撒去。鹽巴掉落在地上的聲音意外悅耳。唰、唰,她聽見不知何處傳來波浪拍打海岸的聲音。她打算繞著房子外圍撒一圈鹽巴,於是便走出大門,接著便再一次面對雙腳併攏,蜷縮在垃圾桶旁打瞌睡的「那個」。
「那個」的身影太過清晰,既不像是幻象,卻又無法斷定是人類。以防萬一,玉珠在它周圍灑了點鹽巴,但那個卻依然靠在骯髒的垃圾桶旁打著瞌睡。玉珠將盤子放在地板上,小心翼翼地跪坐在「那個」面前。油膩膩的頭髮之下,是一張傷痕累累、白到發青的臉孔。玉珠知道,那偶爾會微微顫抖的睫毛下,是一雙鮮紅的眼睛。稍後,玉珠才注意到「那個」握在手裡的腐肉、指節泛紅的乾枯雙手,以及不知穿了多久都沒換過的破爛衣服。玉珠不自覺伸手,她的指尖觸碰到粗糙的皮膚、摸到了肩胛骨的形狀。「那個」確實存在,沒有變得模糊也沒有消失,以一個尚未成熟的孩子的姿態,依然存在於那個地方。
這該怎麼辦才好?這是個炎熱的夜晚,應該不至於凍死。既然已經確認眼前的形體既非鬼魂也非幻象,那玉珠就無法冷眼旁觀。該打電話報警嗎?那警察應該就會過來把那個帶走,應該會把他留置在局裡一個晚上,然後便送到設施去安置。這顯然是最簡單的方法。就在思考下一步時,玉珠聽到「那個」發出的聲音。
嘎吱吱、嘎吱吱⋯⋯
那是人磨牙的聲音。就像心中還留有怨恨的人一樣,那個的嘴裡發出了嘎吱聲。記得現在生死不明的兒子,兒時也曾經像這樣磨過牙。玉珠沒有收回伸向「那個」的手,而是用力地握住了他的肩。「那個」皺起了眉頭,玉珠抓著他的肩搖晃了幾下。蒼白的眼皮突然一陣痙攣,沒過多久「那個」便睜開眼。是剛才看錯了嗎?他的眼不是如石榴籽一般的鮮紅,而是普通的黑色。看他睜著眼的模樣,像極了一個孩子,而玉珠也在一股莫名的情緒驅使之下主動開口說道:
「別待在這,進來吧。」
「那個」眨了眨眼,玉珠十分肯定,他的眼睛在一瞬之間變成了紅色。
怯弱源自於每個難以放下的夜晚,你總能在本書中找到,隱藏心底最深的懼怕。讓我們一起在沁涼深夜中,閱讀這八個交織恐懼與愛的短篇奇幻故事,讓書中有點可愛又浪漫的文字,溫暖你的心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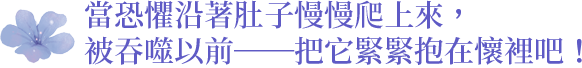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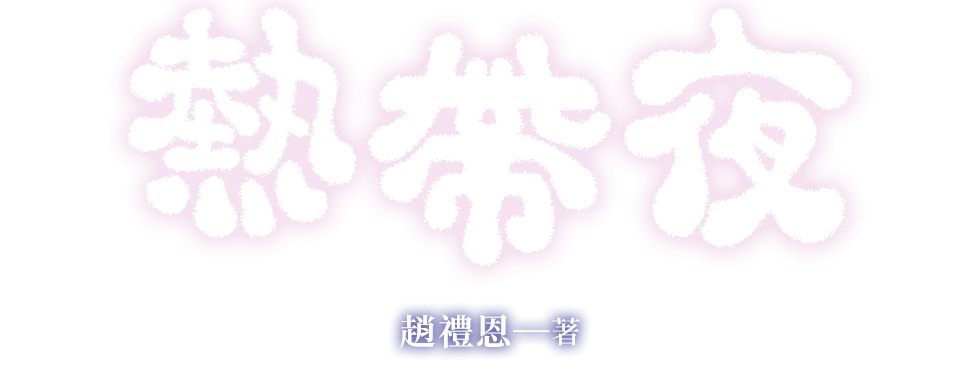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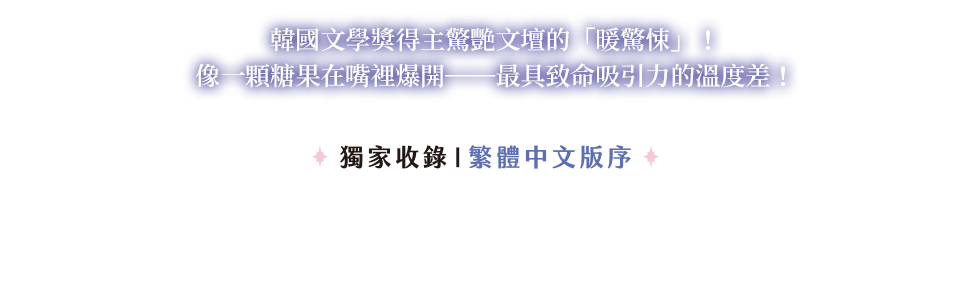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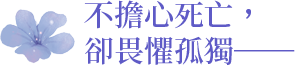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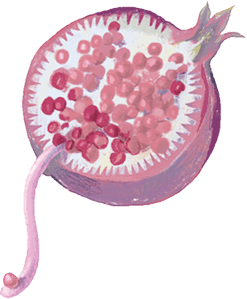 那名披頭散髮的怪漢聽見玉珠的聲音,便從垃圾堆中抬起頭來轉頭望向玉珠。瞬間,玉珠與「那個」對上了眼,那是一張如死屍般毫無血色的臉。
「……」
那有如石榴籽般鮮紅的瞳孔藏著敵意與警戒,被蒼白的膚色襯得更為鮮艷。冷汗流過玉珠的太陽穴,她的雙唇顫抖,只是這次卻發不出聲。她呆站在原地,而「那個」也沒有任何反應。食物因高溫而腐敗的惡臭刺激著鼻尖,此刻,玉珠只想立刻洗去一身的汗水與臭味。她趕緊掏出鑰匙來,顫抖的雙手令她始終無法將鑰匙準確插入鑰匙孔中,這也使她煩躁了起來。先生還在世時,她便要求好幾次要更換成密碼鎖,先生卻嫌記密碼麻煩,始終不肯換掉老舊的鑰匙鎖。他原本就是這種人,痛恨所有陌生的事物,習慣待在熟悉的同溫層裡,所以最後才會那樣離開人世。
好不容易把鑰匙插進孔裡轉開門鎖,很快的,玉珠聽見與往常一樣的門鎖開啟聲。這一帶實在太過安靜,門鎖開啟的聲音顯得更為清脆。玉珠不自覺往旁邊看了一下,恰好從因汗水與污垢而結塊的頭髮之間,看見「那個」似乎正慌忙地不知拿起什麼往嘴裡塞。仔細一看,那是一塊早已爛透發綠的生肉。「那個」似乎餓了很久,瘦成了皮包骨,毫不在乎肉早已腐爛發霉。就在玉珠透過眼角餘光往後頭瞄時,他仍不斷咀嚼著那塊肉。不知不覺間,玉珠接受了外型神似人類的「那個」。也許就像野狗或野獸等野生動物一樣,如今也出現了在野外遊蕩的人類,或者是她不小心將殯儀館的髒東西給帶回家,再不然就是因為先生剛離世不久,連帶自己的精神狀況也出了問題,才會看見這種怪東西。她躲進鐵門內,思考著各種可能。直到進了屋內、關上門並重新將門鎖上之後,她怦怦跳個不停的心才稍稍平靜下來。
玉珠的家是棟屋齡超過四十年的住商混合建築,從餐廳兼肉品處理區的大廳往內走,便是玉珠日常主要活動的小房間。經過原本是廚房的空間,就是一道隨便以水泥砌出來的陡峭樓梯。樓梯一邊通往地下,一邊通往二樓。地下室做倉庫使用,二樓則是她先生生前臥病時待的房間,而在先生生病之前,那裡則是他們的主臥室。沒事的話,玉珠通常不會上二樓。這多少是因為樓梯太陡,爬上去總讓她膝蓋疼痛,但實際上還有其他原因。
玉珠還沒能整理掉先生去世前所躺的那床棉被。生病之後,她先生就像被困在透明監獄裡一樣,只能在那長方形的空間裡動彈不得。一想到當時的情景,她就像是被人一口氣硬塞了一大把年糕似地,痛苦得就要窒息。這並不是在接受先生死亡的過程,而是因為她總忍不住想像自己也同樣躺臥在那的醜態。要說這兩者之間有什麼不同,那就是先生臥病在床時,身旁還有玉珠照顧、賺取生活費、送飯、擦澡,但若是玉珠臥病在床,就只有她自己,沒有人能為她做這些事了,她想必會孤零零地離開這個世界。她深知那使先生喪命的癌細胞也可能在她體內滋長,但憑空想像跟實際聽到醫師如此宣判,又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她在小房間與廚房之間的浴室裡,用大水盆接了些水洗澡。直到這時,她才終於覺得滲入皮膚的那些氣味不再那麼重。玉珠習慣性地將手指湊到鼻尖聞了聞,那洗去了豬腥味,染上獨特自來水味的手指令她感到舒暢。她泡在溫水裡閉上眼,短暫沉浸在思緒中,嘗試思考她的未來、思考是否有可能讓自己不要在悲慘與孤獨之中迎接死亡。年紀比她大十歲的先生因癌症而死,唯一的兒子則在十年前為了創業而前往菲律賓,之後便再沒了消息,連是生是死都不知道。而她也沒有會定期碰面的朋友或信仰的宗教,如果說有一棟位在地區邊陲,可以稱作家的老舊建築是一種幸運的話,那還真是不幸中的大幸。玉珠舀起盆子裡的水,緩緩淋在臉上、肩上、胸上。她將手按在長出腫瘤的大腸附近摸了摸。為了仔細確認這可疑的腫瘤究竟是惡性還是良性、是否轉移到任何地方,醫生表示必須做組織切片檢查。醫生還說,畢竟也有些年紀了,盡快掌握腫瘤的狀況比什麼都更重要。玉珠點點頭表示明白,但走出診間後並沒有預約下一次看診,而是直接返家。無論肚子裡的腫瘤代表的是怎樣一種癌症,她身旁沒有人陪伴、她遲早會死的事實,也都不會改變。既然這最重要的兩件事不會變,那何必去在乎其他的小事呢?年過六十的她,在這樣的情況中還要去想未來的事,實在令她感到很吃力。是因為這樣嗎?是因為身體日漸虛弱,才會看到奇怪的東西吧?玉珠想起進家門前驚鴻一瞥的那雙陌生眼睛。她開始想像那如石榴籽一般鮮紅的眼,以及令人難受到願意翻找垃圾堆的飢餓。
殯儀館的同事之中,也有人經常看到一些異樣的東西。那位同事每次下班都不會立刻回家,而是會去超市或市場等人多的地方走一走,或是先在家門口撒點鹽巴再進門。畢竟是在殯儀館工作,會有這樣的迷信也是無可厚非。不久前,住在隔壁社區的劉氏說,她婆婆死前一天,曾經像個孩子一樣哭訴說晚上有黑色的物體來到她身旁要帶她離開。她婆婆年逾九十又有失智症,因此劉氏當時並沒有多想,不知道為何她會突然想起這件事。
玉珠洗好澡後便來到廚房,從櫥櫃裡舀了一匙粗鹽裝在碟子裡。隨後推開小房間的門,穿越以前用來處理肉品的大廳,並在玄關門前停了下來。越過滿是刮痕的玻璃窗,她看著剛才「那個」所在的垃圾桶。她剛才所目擊的景象並非是夢,只見專用垃圾袋破了一地,裡頭的東西散了開來。「那個」去了哪?她打開只足夠讓一隻腳站出去的門縫,朝外頭看了看。時間已經接近午夜,這位於舊市區邊陲的巷弄沒有任何行人往來,寂靜無聲。玉珠想起同事所說的話,便拿起一小撮鹽往門外撒去。鹽巴掉落在地上的聲音意外悅耳。唰、唰,她聽見不知何處傳來波浪拍打海岸的聲音。她打算繞著房子外圍撒一圈鹽巴,於是便走出大門,接著便再一次面對雙腳併攏,蜷縮在垃圾桶旁打瞌睡的「那個」。
「那個」的身影太過清晰,既不像是幻象,卻又無法斷定是人類。以防萬一,玉珠在它周圍灑了點鹽巴,但那個卻依然靠在骯髒的垃圾桶旁打著瞌睡。玉珠將盤子放在地板上,小心翼翼地跪坐在「那個」面前。油膩膩的頭髮之下,是一張傷痕累累、白到發青的臉孔。玉珠知道,那偶爾會微微顫抖的睫毛下,是一雙鮮紅的眼睛。稍後,玉珠才注意到「那個」握在手裡的腐肉、指節泛紅的乾枯雙手,以及不知穿了多久都沒換過的破爛衣服。玉珠不自覺伸手,她的指尖觸碰到粗糙的皮膚、摸到了肩胛骨的形狀。「那個」確實存在,沒有變得模糊也沒有消失,以一個尚未成熟的孩子的姿態,依然存在於那個地方。
這該怎麼辦才好?這是個炎熱的夜晚,應該不至於凍死。既然已經確認眼前的形體既非鬼魂也非幻象,那玉珠就無法冷眼旁觀。該打電話報警嗎?那警察應該就會過來把那個帶走,應該會把他留置在局裡一個晚上,然後便送到設施去安置。這顯然是最簡單的方法。就在思考下一步時,玉珠聽到「那個」發出的聲音。
嘎吱吱、嘎吱吱⋯⋯
那是人磨牙的聲音。就像心中還留有怨恨的人一樣,那個的嘴裡發出了嘎吱聲。記得現在生死不明的兒子,兒時也曾經像這樣磨過牙。玉珠沒有收回伸向「那個」的手,而是用力地握住了他的肩。「那個」皺起了眉頭,玉珠抓著他的肩搖晃了幾下。蒼白的眼皮突然一陣痙攣,沒過多久「那個」便睜開眼。是剛才看錯了嗎?他的眼不是如石榴籽一般的鮮紅,而是普通的黑色。看他睜著眼的模樣,像極了一個孩子,而玉珠也在一股莫名的情緒驅使之下主動開口說道:
「別待在這,進來吧。」
「那個」眨了眨眼,玉珠十分肯定,他的眼睛在一瞬之間變成了紅色。
怯弱源自於每個難以放下的夜晚,你總能在本書中找到,隱藏心底最深的懼怕。讓我們一起在沁涼深夜中,閱讀這八個交織恐懼與愛的短篇奇幻故事,讓書中有點可愛又浪漫的文字,溫暖你的心窩……
那名披頭散髮的怪漢聽見玉珠的聲音,便從垃圾堆中抬起頭來轉頭望向玉珠。瞬間,玉珠與「那個」對上了眼,那是一張如死屍般毫無血色的臉。
「……」
那有如石榴籽般鮮紅的瞳孔藏著敵意與警戒,被蒼白的膚色襯得更為鮮艷。冷汗流過玉珠的太陽穴,她的雙唇顫抖,只是這次卻發不出聲。她呆站在原地,而「那個」也沒有任何反應。食物因高溫而腐敗的惡臭刺激著鼻尖,此刻,玉珠只想立刻洗去一身的汗水與臭味。她趕緊掏出鑰匙來,顫抖的雙手令她始終無法將鑰匙準確插入鑰匙孔中,這也使她煩躁了起來。先生還在世時,她便要求好幾次要更換成密碼鎖,先生卻嫌記密碼麻煩,始終不肯換掉老舊的鑰匙鎖。他原本就是這種人,痛恨所有陌生的事物,習慣待在熟悉的同溫層裡,所以最後才會那樣離開人世。
好不容易把鑰匙插進孔裡轉開門鎖,很快的,玉珠聽見與往常一樣的門鎖開啟聲。這一帶實在太過安靜,門鎖開啟的聲音顯得更為清脆。玉珠不自覺往旁邊看了一下,恰好從因汗水與污垢而結塊的頭髮之間,看見「那個」似乎正慌忙地不知拿起什麼往嘴裡塞。仔細一看,那是一塊早已爛透發綠的生肉。「那個」似乎餓了很久,瘦成了皮包骨,毫不在乎肉早已腐爛發霉。就在玉珠透過眼角餘光往後頭瞄時,他仍不斷咀嚼著那塊肉。不知不覺間,玉珠接受了外型神似人類的「那個」。也許就像野狗或野獸等野生動物一樣,如今也出現了在野外遊蕩的人類,或者是她不小心將殯儀館的髒東西給帶回家,再不然就是因為先生剛離世不久,連帶自己的精神狀況也出了問題,才會看見這種怪東西。她躲進鐵門內,思考著各種可能。直到進了屋內、關上門並重新將門鎖上之後,她怦怦跳個不停的心才稍稍平靜下來。
玉珠的家是棟屋齡超過四十年的住商混合建築,從餐廳兼肉品處理區的大廳往內走,便是玉珠日常主要活動的小房間。經過原本是廚房的空間,就是一道隨便以水泥砌出來的陡峭樓梯。樓梯一邊通往地下,一邊通往二樓。地下室做倉庫使用,二樓則是她先生生前臥病時待的房間,而在先生生病之前,那裡則是他們的主臥室。沒事的話,玉珠通常不會上二樓。這多少是因為樓梯太陡,爬上去總讓她膝蓋疼痛,但實際上還有其他原因。
玉珠還沒能整理掉先生去世前所躺的那床棉被。生病之後,她先生就像被困在透明監獄裡一樣,只能在那長方形的空間裡動彈不得。一想到當時的情景,她就像是被人一口氣硬塞了一大把年糕似地,痛苦得就要窒息。這並不是在接受先生死亡的過程,而是因為她總忍不住想像自己也同樣躺臥在那的醜態。要說這兩者之間有什麼不同,那就是先生臥病在床時,身旁還有玉珠照顧、賺取生活費、送飯、擦澡,但若是玉珠臥病在床,就只有她自己,沒有人能為她做這些事了,她想必會孤零零地離開這個世界。她深知那使先生喪命的癌細胞也可能在她體內滋長,但憑空想像跟實際聽到醫師如此宣判,又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她在小房間與廚房之間的浴室裡,用大水盆接了些水洗澡。直到這時,她才終於覺得滲入皮膚的那些氣味不再那麼重。玉珠習慣性地將手指湊到鼻尖聞了聞,那洗去了豬腥味,染上獨特自來水味的手指令她感到舒暢。她泡在溫水裡閉上眼,短暫沉浸在思緒中,嘗試思考她的未來、思考是否有可能讓自己不要在悲慘與孤獨之中迎接死亡。年紀比她大十歲的先生因癌症而死,唯一的兒子則在十年前為了創業而前往菲律賓,之後便再沒了消息,連是生是死都不知道。而她也沒有會定期碰面的朋友或信仰的宗教,如果說有一棟位在地區邊陲,可以稱作家的老舊建築是一種幸運的話,那還真是不幸中的大幸。玉珠舀起盆子裡的水,緩緩淋在臉上、肩上、胸上。她將手按在長出腫瘤的大腸附近摸了摸。為了仔細確認這可疑的腫瘤究竟是惡性還是良性、是否轉移到任何地方,醫生表示必須做組織切片檢查。醫生還說,畢竟也有些年紀了,盡快掌握腫瘤的狀況比什麼都更重要。玉珠點點頭表示明白,但走出診間後並沒有預約下一次看診,而是直接返家。無論肚子裡的腫瘤代表的是怎樣一種癌症,她身旁沒有人陪伴、她遲早會死的事實,也都不會改變。既然這最重要的兩件事不會變,那何必去在乎其他的小事呢?年過六十的她,在這樣的情況中還要去想未來的事,實在令她感到很吃力。是因為這樣嗎?是因為身體日漸虛弱,才會看到奇怪的東西吧?玉珠想起進家門前驚鴻一瞥的那雙陌生眼睛。她開始想像那如石榴籽一般鮮紅的眼,以及令人難受到願意翻找垃圾堆的飢餓。
殯儀館的同事之中,也有人經常看到一些異樣的東西。那位同事每次下班都不會立刻回家,而是會去超市或市場等人多的地方走一走,或是先在家門口撒點鹽巴再進門。畢竟是在殯儀館工作,會有這樣的迷信也是無可厚非。不久前,住在隔壁社區的劉氏說,她婆婆死前一天,曾經像個孩子一樣哭訴說晚上有黑色的物體來到她身旁要帶她離開。她婆婆年逾九十又有失智症,因此劉氏當時並沒有多想,不知道為何她會突然想起這件事。
玉珠洗好澡後便來到廚房,從櫥櫃裡舀了一匙粗鹽裝在碟子裡。隨後推開小房間的門,穿越以前用來處理肉品的大廳,並在玄關門前停了下來。越過滿是刮痕的玻璃窗,她看著剛才「那個」所在的垃圾桶。她剛才所目擊的景象並非是夢,只見專用垃圾袋破了一地,裡頭的東西散了開來。「那個」去了哪?她打開只足夠讓一隻腳站出去的門縫,朝外頭看了看。時間已經接近午夜,這位於舊市區邊陲的巷弄沒有任何行人往來,寂靜無聲。玉珠想起同事所說的話,便拿起一小撮鹽往門外撒去。鹽巴掉落在地上的聲音意外悅耳。唰、唰,她聽見不知何處傳來波浪拍打海岸的聲音。她打算繞著房子外圍撒一圈鹽巴,於是便走出大門,接著便再一次面對雙腳併攏,蜷縮在垃圾桶旁打瞌睡的「那個」。
「那個」的身影太過清晰,既不像是幻象,卻又無法斷定是人類。以防萬一,玉珠在它周圍灑了點鹽巴,但那個卻依然靠在骯髒的垃圾桶旁打著瞌睡。玉珠將盤子放在地板上,小心翼翼地跪坐在「那個」面前。油膩膩的頭髮之下,是一張傷痕累累、白到發青的臉孔。玉珠知道,那偶爾會微微顫抖的睫毛下,是一雙鮮紅的眼睛。稍後,玉珠才注意到「那個」握在手裡的腐肉、指節泛紅的乾枯雙手,以及不知穿了多久都沒換過的破爛衣服。玉珠不自覺伸手,她的指尖觸碰到粗糙的皮膚、摸到了肩胛骨的形狀。「那個」確實存在,沒有變得模糊也沒有消失,以一個尚未成熟的孩子的姿態,依然存在於那個地方。
這該怎麼辦才好?這是個炎熱的夜晚,應該不至於凍死。既然已經確認眼前的形體既非鬼魂也非幻象,那玉珠就無法冷眼旁觀。該打電話報警嗎?那警察應該就會過來把那個帶走,應該會把他留置在局裡一個晚上,然後便送到設施去安置。這顯然是最簡單的方法。就在思考下一步時,玉珠聽到「那個」發出的聲音。
嘎吱吱、嘎吱吱⋯⋯
那是人磨牙的聲音。就像心中還留有怨恨的人一樣,那個的嘴裡發出了嘎吱聲。記得現在生死不明的兒子,兒時也曾經像這樣磨過牙。玉珠沒有收回伸向「那個」的手,而是用力地握住了他的肩。「那個」皺起了眉頭,玉珠抓著他的肩搖晃了幾下。蒼白的眼皮突然一陣痙攣,沒過多久「那個」便睜開眼。是剛才看錯了嗎?他的眼不是如石榴籽一般的鮮紅,而是普通的黑色。看他睜著眼的模樣,像極了一個孩子,而玉珠也在一股莫名的情緒驅使之下主動開口說道:
「別待在這,進來吧。」
「那個」眨了眨眼,玉珠十分肯定,他的眼睛在一瞬之間變成了紅色。
怯弱源自於每個難以放下的夜晚,你總能在本書中找到,隱藏心底最深的懼怕。讓我們一起在沁涼深夜中,閱讀這八個交織恐懼與愛的短篇奇幻故事,讓書中有點可愛又浪漫的文字,溫暖你的心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