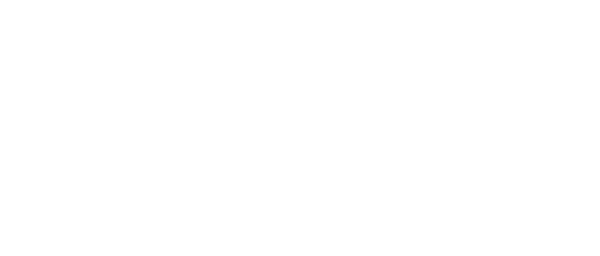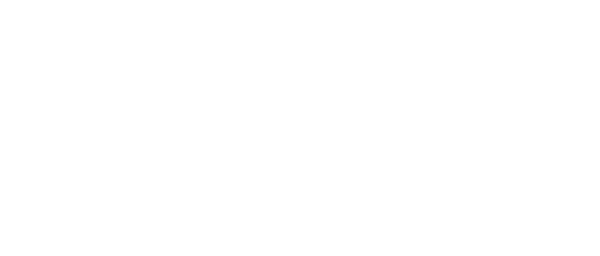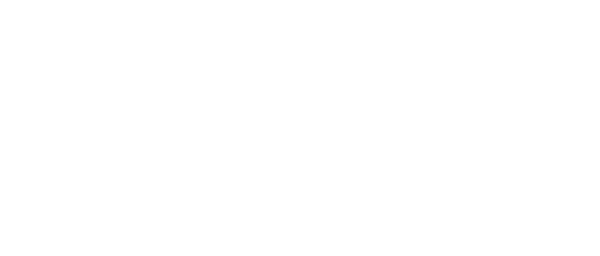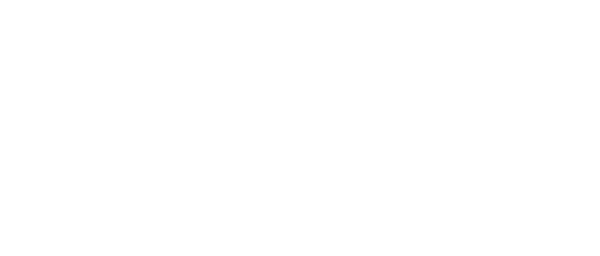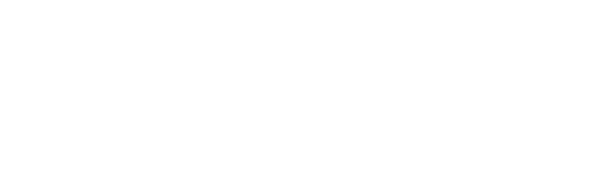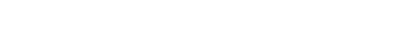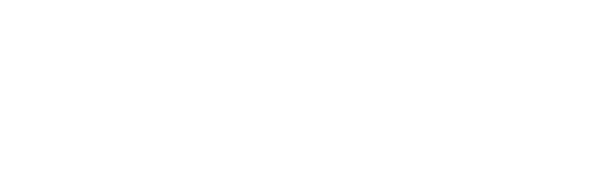我很難訴說雅歌塔的經典之作《惡童三部曲》對我的震撼。那不僅是善與惡,也不只是對扭曲人世的細微觀察。而是作者經歷了殘酷世事,仍能輕撫著人哀痛的靈魂,深信愛能以寫作這個方式,讓最沉痛的呼喊都有了善的堅持。
——作家/馬欣
《惡童三部曲》像一個沒有盡頭的黑森林,閱讀的旅程如同穿過一部冰冷到時間就此被凍結、遺忘的成長電影,主人翁似乎篤定但更多是漠然的凝視,令人感到窒息,既是為了那些場景,更是通過那個所被塑造出來的他們與我們。
——影評人/黃以曦
早在學生時代我就讀過《惡童三部曲》,但從來沒想過竟有一天能夠處理版權!權利人來信詢問我是否願意代理版權時,我一時還不敢相信這是真的。皇冠也在第一時間表達高度意願,積極爭取版權,並找來翻譯名家尉遲秀操刀新版翻譯,賦予經典新時代的語言生命,實在是讀者之福。
——光磊國際版權資深經紀人/武忠森
《惡童三部曲》以最簡白的文字寫出深邃、驚悚和悲傷。不動聲色的敘述娓娓推進,幾乎不倚靠任何隱喻、象徵或詞藻鋪陳。一切尋常都扭曲成不尋常,而所有不尋常卻變得尋常。三部曲的結構有如莫比烏斯環,彼此怪異相連,不停在堆疊也同時在傾頹,最終連結成只存在於紙上的虛構,卻無比真實。
——小說家/黃崇凱
世道比惡童更惡,虛構的罪反而是殘酷現實的救贖。假如我們回到八十年前的匈牙利,我們會成為加害者、復仇者還是寬恕者?無論如何,在雅歌塔離去後的世界,我們似乎仍可以依賴她犀利的語言與真正的惡格鬥。
——詩人、作家/廖偉棠
《惡童》在青少年時代的閱讀記憶中震撼了我,到第二部曲才發現不止如此,再到第三部曲又不止如此,戰爭與命運多冷多殘酷,故事究竟帶來撫慰還是謊言,尉遲秀的譯筆令人期待,不論真相為何都讓人極其痛苦,這套小說太好看了,希望所有人都能再被這部經典虐一次。
——劇作家/簡莉穎
我永遠難忘年輕時讀到《惡童三部曲》內心受到的震撼,那時作為小說練習生的我,初次見識到寫小說可以這樣寫,簡單的文字書寫著艱難的題材,字字句句驚心動魄,多年後重讀,《惡童三部曲》依然是我最愛的小說之一。
——作家/陳雪
閱讀《惡童三部曲》是不可能遺忘的閱讀體驗。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用比《蒼蠅王》更殘酷的方式,推翻我們對人性的假想,並隨著三部曲的進行一再翻轉,是徹底展現虛構威力的奇詭經典。
——作家/朱嘉漢
戰爭最可怕之處,不是讓我們對敵人殘暴。戰爭最可怕之處,是讓我們對自己撒謊。成功欺騙自己的人,成為的不是騙子,而是兇手。而《惡童三部曲》讓我們明白,戰爭中的兇手,其實也是戰爭中的受害者——縱然他們是存活的那一方,是溫飽的那一方——他們失去的那樣東西,比這些都更巨大。
——寫作者、編輯/蕭詒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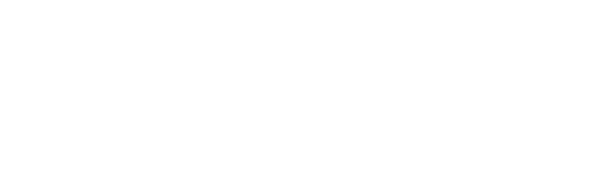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Agota Kristof
1935年10月30日生於匈牙利奇克萬德,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匈牙利遭俄國占領,1956年匈牙利反共革命失敗,與丈夫及仍在襁褓中的女兒流亡至瑞士納沙泰爾。
14歲起她便用母語寫詩,到瑞士後開始學習法語,創作也轉向廣播劇,但於電台播出時,因名字與阿嘉莎.克莉絲蒂相似,曾一度化名為「薩伊克」。1986年小說處女作《大筆記本》於法國出版,隨即震驚當代文壇,1988與1991年又相繼發表了《證據》與《第三個謊》,三本書合稱「惡童三部曲」,總計售出40多種語言版本並獲獎無數,確立了不可動搖的文壇地位。
1986年榮獲法語作家協會頒發的「歐洲圖書獎」,1992年榮獲法國「圖書文學獎」,1993年獲選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1998年榮獲義大利「莫拉維亞獎」,2001年榮獲瑞士「凱勒獎」,2005年全作品獲頒瑞士「席勒獎」,2006年榮獲德國西南廣播公司「最暢銷書排名獎」,2008年獲頒奧地利「歐洲文化獎」,2009年榮獲瑞士「納沙泰爾學院獎」,2011年獲頒匈牙利最高文化榮譽「科蘇特獎」。
其他作品包括:劇作集《怪物》(1994)、《傳染病》(1995),長篇小說《昨日》(1995),自傳體作品《文盲》(2004),中篇小說《惡夢》(2005)等。其文字冷酷、簡約、低調,但又充滿了諷刺感與獨創性,創作主題圍繞在成長與動亂、自由與壓迫、真實與虛構、死亡與命運,同時也承載了關於戰爭、流亡、苦難與人性等深刻面向。
2002年《昨日》改編拍成電影,入圍第52屆柏林影展「金熊獎」,並獲義大利多納泰羅影展八項提名。2013年《大筆記本》改編拍成電影,入圍第86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並榮獲捷克卡羅維瓦利影展「最佳影片」。
2011年7月27日於家中去世,享年75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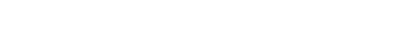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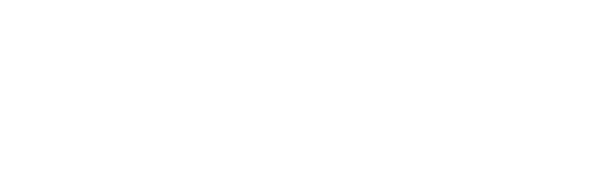
到外婆家
我們從大城過來。我們旅行了一整夜。我們的母親眼睛都紅了。她帶了一個大紙箱,我們兩個各帶一個小行李箱裝衣服,還有我們的父親的大字典,我們抱在手上,手痠了就換另一個人拿。
我們走了很久。外婆家離車站很遠,在小城的另一頭。這裡沒有電車,也沒有公車,也沒有汽車。只有一些軍隊的卡車在路上走。
路上的行人很少,城裡很安靜。我們聽得到自己的腳步聲。我們走路的時候沒講話,我們的母親走在我們兩個人的中間。
在外婆家的院子的門外,我們的母親說:
「在這裡等我。」
我們等了一下,然後走到院子裡,繞到屋子後面,蹲在一扇窗戶底下。我們聽到聲音從裡面傳出來,那是我們的母親的聲音:
「我們家裡什麼吃的都沒有了,沒有麵包,沒有肉,沒有蔬菜,沒有牛奶,什麼都沒有。我沒辦法養他們了。」
另一個聲音說:
「所以,你就想起我了。十年了,你都沒有想到我。你人沒來,也沒寫信給我。」
我們的母親說:
「您很清楚是為什麼。我的父親,我太愛他了。」
另一個聲音說:
「是啊,然後現在你才想起來你也有個母親。你來了,然後你求我幫你。」
我們的母親說:
「我沒有為自己求什麼,我只是希望我的孩子可以活過這場戰爭。大城日日夜夜都被轟炸,那裡已經沒有食物了。大家都把孩子疏散到鄉下,去親戚家或是陌生人的家,去哪裡都好。」
另一個聲音說:
「你可以把他們送去陌生人家啊,送去哪裡都好。」
我們的母親說:
「他們是你的孫子。」
「我的孫子?我根本不認識他們。他們有幾個?」
「兩個。兩個男孩,是一對雙胞胎。」
另一個聲音問:
「你把其他小孩怎麼了?」
我們的母親問:
「其他小孩?」
「母狗一胎生四隻或五隻小狗,通常只會留下一隻或兩隻,其他的就把牠們淹死。」
另一個聲音笑得很大聲,我們的母親完全沒笑,然後另一個聲音問:
「他們至少有個父親吧?就我所知,你沒有結婚。我沒有被邀請去參加過婚禮。」
「我結婚了。他們的父親在前線,我已經六個月沒有他的消息了。」
「我看你已經可以幫他插上十字架了。」
另一個聲音又笑了,我們的母親哭了。我們跑回院子的門前。
我們的母親和一個老女人從屋子裡走出來。
我們的母親對我們說:
「這是你們的外婆,你們要在她家待上一段時間,直到戰爭結束。」
我們的外婆說:
「戰爭可能會持續很久。不過別擔心,我會讓他們做事。這裡的食物也不是讓人白吃白喝的。」
我們的母親說:
「我會寄錢給您。行李箱裡有他們的衣服,紙箱裡面是床單和毯子。你們要乖,我的小寶貝,我會寫信給你們。」
她親吻我們然後就哭著走了。
外婆笑得很大聲,然後對我們說:
「床單、毯子!白襯衫和漆皮皮鞋!我會好好教你們怎麼過日子!」
我們對外婆吐舌頭。她笑得更大聲了,一邊笑還一邊拍大腿。
外婆
我們的外婆是我們的母親的母親。來住她家以前,我們不知道我們的母親還有一個母親。
我們叫她外婆。
這裡的人叫她巫婆。
她叫我們「狗娘養的」。
外婆又瘦又小。她的頭上包著一塊黑色的方巾,她的衣服是深灰色,她穿一雙舊的軍用皮鞋。天氣好的時候,她就赤腳走路。她滿臉都是皺紋、褐色的斑點和小肉瘤,上面還有毛。她已經沒有牙齒了,至少已經看不到了。
外婆從來不洗澡。她吃完東西或喝完酒的時候,會用頭巾的一角擦嘴巴。她不穿內褲。她需要尿尿的時候,不管走到哪,她就停下來,打開雙腿,用裙子遮著尿在地上。當然,她不會在屋子裡做這件事。
外婆從來不把衣服脫光。我們在晚上看過她的房間。她脫掉一件裙子,裡面還有另外一件裙子。她脫掉上衣,裡面還有另一件上衣。她就這樣睡覺。她不會把頭巾拿下來。
外婆很少說話。除了晚上。晚上,她從架子上拿一瓶酒,直接對著瓶口喝。很快地,她開始講一種我們沒聽過的語言。那不是外國軍人講的語言,是一種完全不同的語言。
外婆用這種沒聽過的語言問自己問題,然後自己回答。她有時候笑,有時候生氣,有時候大叫。最後,幾乎每次都是這樣,她哭起來了,她搖搖晃晃走到房間裡,倒在床上,然後我們聽到她在夜裡啜泣的聲音,好久好久。
工作
我們一定得幫外婆做一些工作,不然她什麼都不會給我們吃,還會把我們趕到外面去過夜。
一開始,我們不聽她的話。我們睡在院子裡,我們吃生的水果和蔬菜。
早上,在日出前,我們看到外婆走出屋子。她不跟我們說話。她要去餵那些動物,給山羊擠奶,然後帶牠們去河邊,她會把牠們拴在一棵樹上。接下來,她在院子裡澆水,然後摘一些蔬菜和水果,裝進她的獨輪推車裡。她還會在推車裡放一籃蛋、一個小籠子,裡頭有一隻兔子和一隻雞或一隻鴨,兩腳都綁起來了。
她推著她的獨輪推車去市場,推車的寬皮帶掛在她瘦瘦的脖子上,壓得她抬不起頭。車子太重害她搖搖晃晃,路上的隆起和那些石頭害她走不穩,不過她走路時兩腳往內翻,像鴨子在走。她往城裡走,一直走到市場都沒有停,獨輪推車一次都沒有放下來。
她從市場回來,就拿沒有賣掉的蔬菜來煮湯,再用水果做果醬。她吃,她在葡萄園裡睡午覺,睡一個小時,然後整理葡萄園,如果那裡沒事可做,她就回家,劈柴,再餵一次動物,把山羊帶回來,幫牠們擠奶,她去森林裡,帶回來一些蘑菇和乾柴,她做乳酪,她把蘑菇和菜豆曬乾,她把其他蔬菜醃漬成好幾罐,再給院子裡的蔬菜水果澆一次水,整理地窖裡的椅子,諸如此類的工作,直到天黑。
第六天早上,她走出屋子的時候,我們已經在院子裡澆完水。我們從她手上接過沉甸甸、裝滿豬食的桶子,我們帶山羊走到河邊,我們幫她把獨輪推車裝滿東西。她從市場回來的時候,我們正在劈柴。
吃完飯,外婆說:
「你們明白了吧。屋頂和食物,你們要配得上才會有。」
我們說:
「不是這樣的。工作是痛苦的,可是看別人工作,自己卻什麼都不做,那更痛苦,特別是那個人是老人。」
外婆冷笑著說:
「狗娘養的!你們的意思是你們同情我?」
「不是,外婆,我們只是為自己感到羞恥。」
下午,我們去森林裡找木柴。
從此,所有我們能做的工作我們都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