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女與祖母一起珍重孵育的鳥蛋,孵化出了一隻玄鳳鸚鵡。兩人將小鳥取名為「Ribbon」,悉心照料牠長大,兩人一鳥的快樂生活,彷彿永遠不會迎來終點。然而有一天,Ribbon卻飛離了她們的身邊——飛向廣闊天空的背影,看上去就像是一條真正的緞帶。
那天開始,Ribbon這條緞帶,將漂泊無依的生命,重新繫在一起。誤以為窗邊的小鳥是天使,成為喪子母親最大的安慰;痛失愛鳥的飼育員,重拾有鳥相伴的雀躍;與小鳥相依為命的畫家,決心將最後的時間奉獻於創作;過世姊姊留下的小鳥,為她說出「歡迎回來」代替道別。他們一生中最重要的寶物,便是與Ribbon共度的每一天。
Ribbon帶來了相遇的喜悅,卻也同時孕育著離別。當被現實擊倒的人們找回棲身之處,便是牠振翅出發之時。一度繫上的結不會輕易鬆開,這次,牠的目的地是那年春天,那棵茂盛的櫻花樹下,那對祖孫的身邊……


小川糸
 © Cedric Diradourian
© Cedric Diradourian


雛鳥誕生之後過了一週,另外兩顆蛋果然還是毫無動靜。阿堇還打算繼續孵蛋嗎?我才剛這麼想,阿堇就交辦了任務給我。
「雲雀,妳能幫我把沒有孵化的孩子們埋進土裡嗎?」
我從阿堇頭頂上頭髮編成的鳥巢之中,取出那兩顆蛋,將它們輕輕包裹在手帕裡,走到戶外。阿堇還得顧小寶寶,總是寸步不離地陪在雛鳥身邊。我想了又想,最後決定將兩顆蛋埋葬在樹爺爺的根部。
樹爺爺長在隔壁家的院子裡,不過從中里家鑽過灌木叢也能過去。小時候,隔壁鄰居常常讓我在他們家後院裡隨便玩耍,把鳥蛋埋在那裡也不會被責罵的。
我撥開各種顏色的落葉,用木棒和尖石挖出一個土坑,將兩顆蛋放進去,再把土蓋了回去。
我哀悼完畢,回到家裡,雛鳥比先前更拚命地吃著飼料。與剛出生的時候相比,牠現在的身體渾圓了不少,但仍然幾乎看不出牠是隻小鳥。牠的鼻子和嘴喙像蠟塊一樣突兀地黏在身上,只有這一部分暗示著牠將來會長成一隻鳥兒,除此之外,牠看上去仍然像個外星人。
雛鳥不顧一切地大口進食,位於牠頭部底下的袋子撐得鼓鼓的,像摘瘤爺爺臉上的瘤一樣。一開始看見時我嚇了一跳,不過阿堇告訴我,這是鳥類特有的構造,叫做嗉囊,是個透明的袋子,牠們吃下的餌料就通過這裡,流進胃袋。
偶爾會發生食料堆積在嗉囊的情況,這時就會引發消化不良,聽說有可能危及雛鳥的性命。所以,阿堇總是仔細檢查飼料有沒有好好流進胃裡。嗉囊裡還殘留食物的時候,她不會急著餵下一口,而是讓雛鳥喝點四十度左右的溫開水,輕輕替牠按摩嗉囊,據說這樣對消化比較好。這種事我絕對、絕對不可能做得來。
「那個呀,阿堇。」
看著阿堇專注哺餵雛鳥的側臉,我這麼開口。阿堇的包頭裡已經一顆蛋也沒有,空空蕩蕩的了,這讓我有點落寞。
「怎麼了,雲雀?」
阿堇看著雛鳥,心不在焉地回答。
「我們是不是該幫這隻鳥取個名字了呀?」
我一直很在意這件事。阿堇經常用「小寶寶」之類的詞稱呼雛鳥,但這樣叫牠好像有點太沒趣了。而且實際上,牠沒有名字也常常帶來不便。
「是呀……」
阿堇輕輕按摩著雛鳥的嗉囊,再次心不在焉地回應。在這種時候,阿堇也總會先用熱毛巾一一溫熱過指尖,再碰觸雛鳥。她說,因為雛鳥還沒長出羽毛,所以特別怕冷。
「我也一直在幫這孩子想名字。」
吃完晚飯,我寫完作業,來到阿堇房間的時候,她突然提起了這個話題。我們家最先泡澡的人一定是阿堇,現在阿堇又能泡澡了。所以在阿堇洗澡的時候,我就像這樣陪在雛鳥身邊,絕對不會放著雛鳥無人照顧。
我保持沉默,阿堇便從抽屜深處拿出了一個小盒子。
「拿這個當名字怎麼樣呢?」
那不是她平常放手鏡、體溫計的上面那層抽屜,而是最底下的那一層。阿堇像刻意賣關子似的,緩緩掀起盒蓋。那盒子有著漂亮花紋,感覺是外國巧克力之類精緻小東西的包裝盒,裡面裝著好多五彩繽紛的緞帶,粗細、材質都各不相同,每一條都仔細捲成一圈收好。
「緞帶?」我問。
「是呀,緞帶,Ribbon。」
「妳是說,這隻小鳥的名字就叫Ribbon?」
「是的。」
然後,阿堇好像突然失去自信似的,又問我:妳覺得怎麼樣?
雛鳥已經躺在阿堇大腿上的帽子底部,安穩地睡著了。阿堇腿上放著毛毯包裹的充電式懷爐,牠肯定睡得溫暖又舒服。
「妳是不是不喜歡這個名字?」
我一時出神,這才發現阿堇一臉不安地看著我。
「妳言重了!」
我連忙否認。阿堇偶爾會自然流暢地說出「是你言重了」這種話,所以我也耳濡目染地學會了這種說法。
「叫Ribbon對吧?我覺得這個名字很棒哦。」
其實,我自己也偷偷幫這隻小鳥想了幾個名字。可是我只想到巧克力、牛奶糖、豆沙、金平糖這種又甜又好吃的名字,沒什麼特別好的點子,正在傷腦筋呢。
在這種狀況下,阿堇的提議替我打開了另一扇門,通往我從未想過的廣闊世界。這個名字很可愛,叫起來感覺也滿順口的,我舉雙手贊成。
「雲雀,這孩子就像一條緞帶,會永遠將我和妳綁在一起。」
阿堇仰頭望向天花板,突然喃喃這麼說,好像許下非常重要的誓言似的。
在阿堇眼中,天花板上的汙漬一定就像銀河,白斑看上去就像閃亮的星點吧。她望著天花板上鋪展開來的夜空繼續說道,那張側臉忽然和Ribbon吃飼料時的側臉重疊在一起。
「雲雀,總有一天,我會從妳面前消失不見。我做過許多壞事,說不定會被擋在天堂的門外吧,但總而言之,我遲早會離開這個世界。」
「這……」
我希望她不要突然說出這種話。無論到什麼時候,我都想一直跟阿堇待在一起——明明想這麼告訴她,我的喉嚨卻堵住了,發不出聲音。我此刻的心情或許經由空氣,傳遞到了身旁的阿堇心裡。
「畢竟我已經是個老奶奶了呀。但是雲雀,妳不用擔心,我還不會從妳眼前消失不見,因為我對這孩子還有責任呀。」
阿堇挺直了背脊,堅定地說道。
「我是不可能活得比雲雀妳更久了,這是自然的道理,我們沒辦法改變。可是我想,我的靈魂肯定會一直陪在妳身邊的。儘管妳看不見,但我一定會在。我希望妳隨時都能記起這件事,所以才想將這孩子取名叫『Ribbon』。」
說到這裡,阿堇才終於重新將臉轉向我。
「靈魂?」
我問。我當然聽過這個詞,但不太確定它具體的意思。
「靈魂是我們最重要的東西。一旦玷汙了靈魂,我們就會失去一切。」
「和心靈不一樣嗎?」
「這是很好的問題,雲雀。靈魂和心靈不一樣哦。」
阿堇立刻答道,又以確信不疑的表情補充:
「靈魂被心靈保護著,而心靈又被身體保護著。」
我在腦中想像了一下。靈魂被心靈保護,而心靈又被身體保護,意思也就是說……
「就像草莓大福一樣嗎?!」
我靈光一閃,這麼說道。
「沒錯,妳說得沒錯。」
阿堇驀地睜大眼睛,那兩潭美麗的湖水彷彿被陽光照耀似的閃閃發亮。
「如果說外層的麻糬是身體,那麼裡面的豆沙餡就是心靈,而位於豆沙餡中心的草莓,沒錯,就是靈魂了。雲雀,妳覺得草莓大福裡最重要的是什麼東西?」
「草莓!」
我自信滿滿地回答。草莓大福裡面要是沒有了草莓,就變成普通的大福了。
「沒錯。接下來我要說的話很重要哦。」
阿堇那雙閃亮湖面般的眼睛,目不轉睛地凝視著我。
「我的靈魂,和雲雀妳的靈魂,永遠都被緞帶牽繫在一起。」
Ribbon將我和阿堇的靈魂綁在一塊,一條透明的、看不見的緞帶,將我們彼此相連。想到這點,我的胸口就湧上一種說不清的感覺,好像在大海裡面尿尿的時候一樣,有一股哀傷又溫暖的東西擴散開來。
「Ribbon。」
我緩緩發出聲音叫牠。Ribbon一臉乖巧沉穩的表情,不經意看向我,好像在說:嗨,叫我嗎?
多美、多好的名字啊。
我不禁覺得,越是呼喚這個名字,我和阿堇之間的羈絆便會變得更加穩固。這麼一想,我對Ribbon的愛就像片巨大的新葉一樣,嘩地抽芽舒展開來。
Ribbon剛出生時的體重不到五公克,到了出生第四天就長到了二位數,出生一週時將近三十公克,到了第十天,牠的體重就突破五十公克了,長成了出生時的十倍重。最近的Ribbon食欲旺盛,一次吃下的飼料量也多了不少。剛開始牠只能喝泡得稀稀的飼料湯,後來牠的飼料湯越來越濃稠,現在吃的已經像粥了。按照阿堇的說法,再過不久,牠就能吃下粟米之類的固態食物,到了那時候,我也能幫忙餵食了。
老實說,牠外表引人不適的程度大約在出生後一週左右達到顛峰。牠長得像凸眼金魚,脖子像長頸妖怪那麼長,而且又細得好像隨時會折斷,一點也不可愛。沒有羽毛的鳥毫無防備又弱不禁風,看起來只像異形而已。
我開始覺得牠有那麼一點可愛,是在牠出生之後第十一天,牠終於睜開眼睛的時候。早上我正準備去上學,卻被阿堇叫住。仔細一看,窩在帽子底部的Ribbon,眼睛微微睜開了一條縫。在這之前,牠的雙眼一直被半透明薄膜般的東西完全覆蓋,但現在,那層薄膜像鈕釦洞那樣開了一點縫隙,像羊羹一樣又黑又清澈的眼睛露了出來。牠還沒完全睜眼,所以表情看起來一直都好像剛睡醒一樣。
「Ribbon,這個可愛的女生就是雲雀喲。」
阿堇把我介紹給Ribbon認識。為了讓牠看清楚我的臉,我朝牠湊得很近,牠細微的呼吸噴上我的臉頰,有點癢癢的。
「Ribbon,我是雲雀,你好呀。」
我也跟Ribbon做了自我介紹。
Ribbon身體上開始長出了蓬鬆的胎毛,但頭頂上還是一根毛也沒有,光禿禿的。牠的臉看起來還是個外星人,但與昨天之前相比,長得已經越來越像鳥了。
「太好了,阿堇。」
我這麼說完,便匆匆忙忙地衝出玄關,以免遲到。
「我出門了——!」
「祝妳有美好的一天!」
遠遠傳來阿堇的聲音,這是個寒風刺骨的早晨。
放學回家一看,Ribbon明顯比之前長得更大了。阿堇也許是漸漸習慣了育兒工作,再次展開了Ribbon出生之後一直擱置的歌唱課程。Ribbon本來除了吃東西以外的時間都在睡覺,不過到了最近,牠清醒的時間也越來越多了。
在牠微微睜開眼睛之後三天,也就是出生之後第二週,Ribbon完全睜開了眼睛。原本彎曲成不自然角度的翅膀骨上,也長出了看似羽毛的東西,像粗針一樣刺刺的羽毛覆滿了牠的全身。到了這時候,牠看起來終於像隻小鳥了,對Ribbon的親近感也源源不絕地湧上我的心頭。當我注意到的時候,Ribbon光禿禿的頭頂上就已經長出了一撮翹毛,像武士的髮髻。
我將Ribbon放在手掌心上,幫阿堇一起餵食。從手掌中央,我能切實感受到Ribbon生命的重量。
「Ribbon該不會是一隻棕耳鵯吧?」
我下定決心,這麼問阿堇:
「因為,妳看牠這裡……」
我用大拇指比了比Ribbon的耳朵一帶。鳥類的耳朵位於眼睛斜下方,有個像牙籤戳出來的小孔就是了。Ribbon在耳朵這附近,長著帶有淡淡橘色的毛。
「不知道呢。」
阿堇含糊其詞。
在我的手掌支撐之下,Ribbon正在一心一意地吃著阿堇湯匙裡的粟米。牠的身體周遭長了一圈蓬鬆的胎毛,好像穿上了表演服的芭蕾舞伶。
「我們遲早會知道答案的。」
阿堇將湯匙遞向Ribbon的嘴喙,語調平穩地這麼說。
「難得有這個機會,不如保留答案,當作到時候的驚喜吧?」
Ribbon專心致志地吃著飼料,不只是嘴喙,連鼻子周圍都沾上了好多粟米。我直到最近才知道,這種粟米原來不是普通的小米,它叫做蛋黃粟,是由小米去殼之後,表面再沾上蛋黃製成。所以加熱之後,它會隱約散發出一股雞蛋獨有的氣味。
為了再早一分鐘、一秒鐘見到Ribbon,我每天放學都跑步回家。我運動神經不好,尤其跑馬拉松和賽跑的時候總是跑全班最後一名,跑步回家對我來說可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為了抄近路,我穿過平常不走的空地,像野貓那樣鑽過鐵絲網往前狂奔。好不容易抵達玄關,我會好好調整過呼吸,再靜靜打開玄關門,走進屋內。一踏進門,總會聽到阿堇唱的搖籃曲迎接我回家。
Ribbon的出生為祖孫倆帶來無比的喜悅,也像一條無形的緞帶,緊連著彼此守護的心意。從孵蛋到展翅,阿堇與雲雀無微不至地照顧Ribbon,看似平凡溫馨的日常,是否真能夠一直歲月靜好下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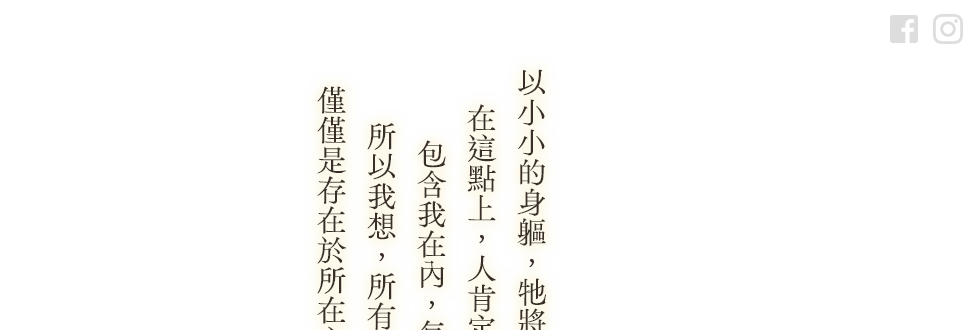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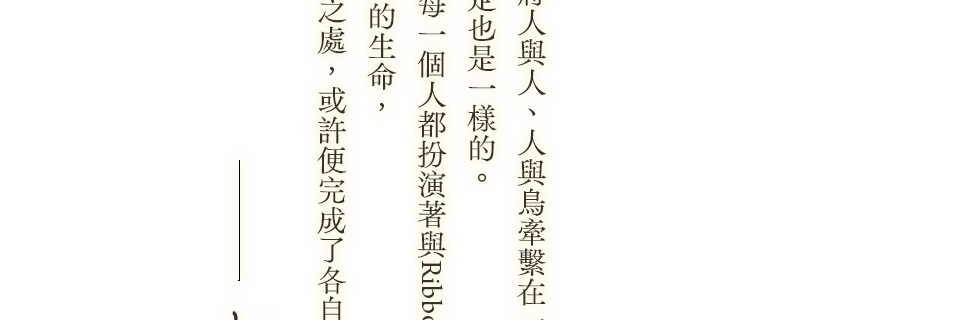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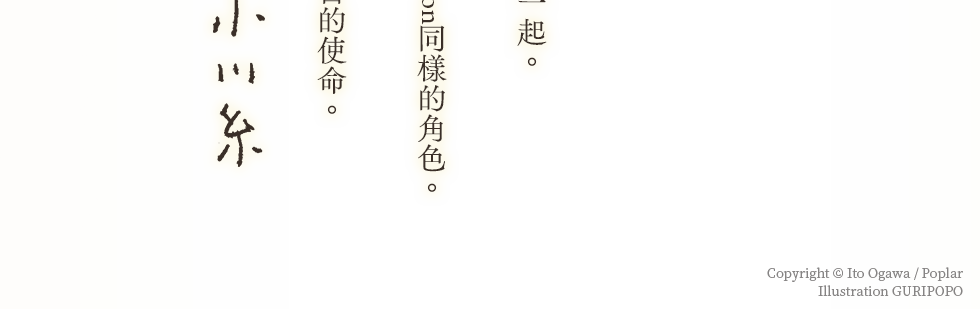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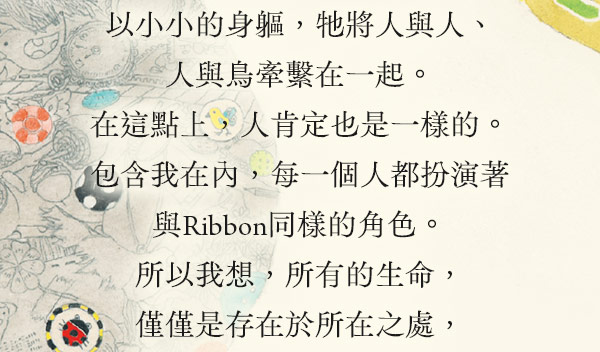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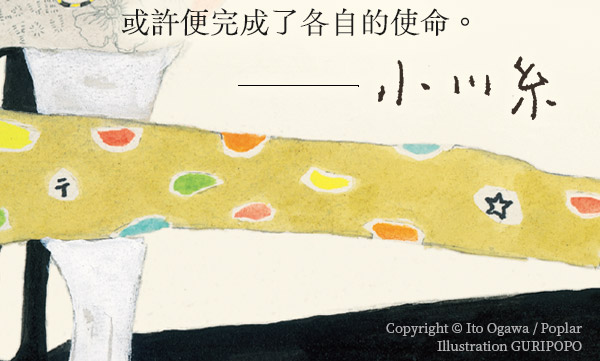








© Cedric Diradour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