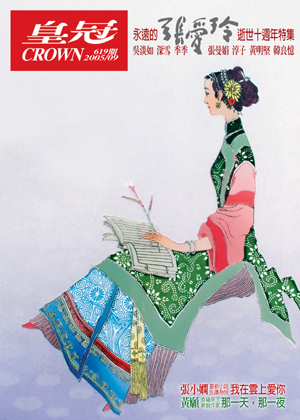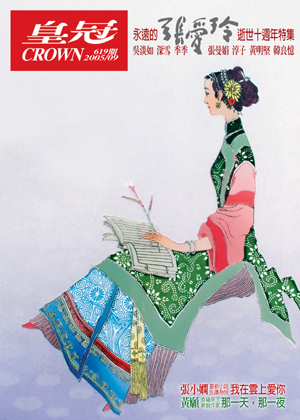特別企畫‧永遠的張愛玲小白珠子和蛤蟆酥
我呢,只想談談小時候看了她的書以後,嘗試跟著這位民國女子吃吃看、喝喝看的一點瑣事……
說實在的,我談不上是張愛玲迷,雖然我也跟同輩許多『前』文藝青年一樣,在生命中某段時光,特別愛讀她的作品,邊讀還會邊驚嘆:居然有人聰慧至此,對人世與愛情看得冷然剔透至此,文筆卻又如此從容而鮮麗,可是我對她始終也止於欣賞喜愛而己,並沒有到『癡迷』的地步。
至於張著中的飲食意像與譬喻,那是可以寫一本厚厚的論文的,像這樣有學問的事,還是留給文學家或學者去做,我呢,只想談談小時候看了她的書以後,嘗試跟著這位民國女子吃吃看、喝喝看的一點瑣事。
真的是小時候喔,當時我還在唸小學六年級,因為早讀一年的關係,十一歲還沒滿,卻已是個酗文字的文藝少女,不,文藝兒童。不管什麼書,只要裡頭印了有密密麻麻的字,拾起便看。看不懂的,像什麼尼采哲學之類的,看不到半頁就擺在一邊,再找別的;看得懂的、好看的,小說也好,散文也好,就手不釋卷,鄰居玩伴在紗窗外叫我去跳橡皮筋也不理。
有一天,在床頭櫃上發現媽媽看完以後順手擱下的《流言》。張愛玲這名字我是聽過的,媽媽是《皇冠》的長期訂戶,我從三年級起就是忠實的小讀者,自然知道張愛玲是皇冠旗下的大作家,只不過不知怎的,之前竟然沒看過張愛玲的作品。我翻開書,第一篇看到是〈童言無忌〉,光篇名就引起我的興趣,我還是兒童嘛。
張愛玲從用錢、賺錢這件事講起,然後說到『穿』。老實講,她講的那些多少是『大人』的事,我並不完全心領神會,卻已被流利至極又有風格的文字吸引,緊接著,她談起『吃』,說自己『一直喜歡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時候設法先把碗邊的小白珠子吞下去』,看到這兒,我竟不自覺嚥了口水,並起身打開冰箱,看裡頭可還有紙盒裝福樂鮮奶。有的話,我要熱來喝,我想喝喝看牛奶的『小白珠子』是不是真的特別好喝。
冷藏櫃裡沒有鮮奶的影子,不過家裡常備有克寧奶粉,我因為嫌奶粉泡出來的牛奶有股怪味,也不香,平時是不大肯喝的,這會兒實在是太好奇了,頭一回自動自發學著幫忙家務的陶媽媽泡牛奶的樣子,泡起牛奶來了。奶粉罐裡附有塑膠圓匙,我舀了滿滿兩匙,加了小半碗冷開水攪勻,到沒有疙瘩塊塊了,這才對上熱水,再攪拌幾下。
為了讓牛奶多起泡泡,我用四根筷子一起用力攪,果然攪出一小圈小白珠子,貼著碗壁。我小心翼翼半喝半吸溫溫的牛奶,設法先吞泡沬,可那泡沬顯然不夠多,或者太細太小,我根本嚐不出有什麼特別,還是我不愛喝的奶粉加水該有的味道嘛。(長大以後發覺,這種物質極細微處的樂趣,大概得比較世故卻仍有點天真的人才能明白,當時我到底還是半大不小的孩子,天真是有的,世故卻不足,怎麼會懂?)
我試著喝了半飯碗牛奶,就不肯再勉強自己,毫不吝惜地倒進水槽,回過頭去看文章,張愛玲又說:『我和老年人一樣的愛吃甜的爛的。一切脆薄爽口的,如醃萊、醬蘿蔔、蛤螟酥,都不喜歡,瓜子也不會嗑,細緻些的菜如魚蝦完全不會吃,是一個最安分的『肉食者』。
沒出息的我又吞口水了,因為我也愛吃甜的爛的,而且連張愛玲不愛的醃菜、醬蘿蔔也喜歡,還是個吃魚高手,最嗜食刺多又小的紅燒鯽魚,有鯽魚上桌,我就不吃白飯,索性將魚當飯,一人吃上一整條。(不過,我也不會嗑瓜子,尤其是特別容易碎的玫瑰瓜子,到現在還不會。)
只是,這蛤蟆酥是什麼玩意?真的也『脆薄爽口』,好不好吃呢?我把這些問題藏在心底,當天晚上爸爸回家後,就問,爸爸是江蘇人,住過上海,應該會知道吧。
『就是種餅啊,綠綠的,顏色像蛤蟆。』爸爸果然知道,『那東西乾乾的,沒什麼吃頭。』
可是我還是好奇的很,以後只要跟爸媽上『采芝齋』、『老天祿』之類的江浙點心店,就要左轉轉右轉轉,看看有沒有蛤蟆酥可買,可是我始終沒找著,也始終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樣的點心。一直到很多年以後,讀到張愛玲較晚期寫作的〈談吃與畫餅充飢〉,裡頭終於較詳細的提到了蛤蟆酥,『那是一種半空心的脆餅,微甜,差不多有巴掌大,狀近肥短的梯形,上面芝麻撒在苔綠底子上,綠陰陰的正是一隻青蛙的印象派畫像。那綠絨倒就是海藻粉。想必總是沿海省分的土產,也沒包裝,拿了來裝在空餅乾筒裡。』傳奇才女的形容是比爽朗不拘小節的爸爸仔細生動,我彷彿可以想像蛤蟆酥的模樣,甚至它脆酥的滋味——儘管我還是沒見過、沒吃過,因此也就不知道到底有沒『吃頭』。
其實,就在這吃吃看或吃不到的過程中,我早該明白,自己雖然一直以為文學是偉大的藝術,大學時主修的也是西洋文學,可是兒時的我在看了張愛玲以後,佩服歸佩服,卻沒有『見賢思齊』,從此發奮練筆寫作,反而熱中學著人家吃吃喝喝,這不已預示著,我終究會了解到自己畢竟不是當純文學作家的料,並且在三十歲以後總算接受現實,轉而寫起似乎更適情適性的飲食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