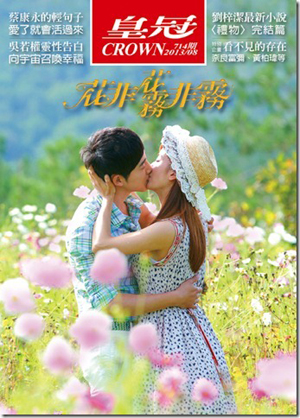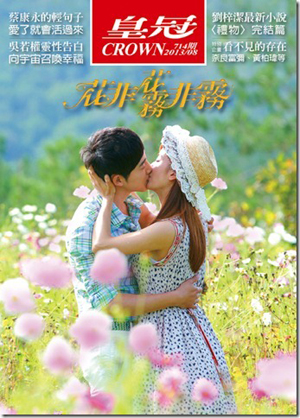【推薦小說】美好的痠痛:十年十問
1、這十篇小說的戲劇張力十足,但同時又「真實」得不可思議。妳如何蒐集這些故事題材?在寫就這十篇小說時,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比如情節難以發展、寫到無法控制自己的情感……等。
我很少在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下去「構思」一篇小說。幾乎都是在現實生活中,不經意地被某個事物或「戲劇化」經驗擊中,我會有種「咚!」的感覺:就是這個!這個可以發展成小說。但這個現實經驗,其實就只是像大富翁遊戲的第一次骰子,它幫我起了一個頭或給我一個人物,接下來的每一步,進進退退,機會命運,就是開了word檔之後的事了,也就是說,變成「作者和小說」之間的事,與現實不太相關了。
如〈日曆〉是大學時編刊物去印刷廠,看到裡面那些排版小姐,想到恐怖的、僵滯的年輕生命;〈失明〉是我當時因為千度近視,常常受針眼、結膜炎、角膜刮傷等等眼疾所苦;〈親愛的小孩〉則是三十歲過後,自己與周圍朋友都來到面臨「想生、不想生、如何生、想生的生不出來、不想生的意外懷孕」的人生階段。
若說讀來「真實」,我想是無論劇情如何跌宕,我一直都希望把情緒與情感逼到最真,它就像是一條繩索,必須緊抓不放,虛構的人物與故事才能飛簷走壁。這也是常常是寫作過程最難的部分,有時覺得這繩子有點虛假、有點危險,我和小說中這些男女就停在懸崖上,定住不動,一停半個月或幾年都有。大概這也是寫得慢的原因。
2、從〈失憶與失蹤〉到〈禮物〉中間隔了整整十二年,這十二年之間,妳如何看待寫作這件事?這十篇作品在妳的寫作生涯裡有沒有什麼特別重要的意義?
比較把寫作當回事,應該是從十年前〈失明〉得到小說新人獎開始。但即使拿到這張「文壇入場券」,我還是沒有乖乖入座,跑去做了編輯、文案、記者等文字工作。七年前,〈父後七日〉散文得獎,接著改編電影賣座得獎等等,一連串「顯著」的事,我就變成寫「散文」和「劇本」的作者了。一直到去年《短篇小說》雜誌在萬眾矚目下創刊,我應邀交稿一篇,〈親愛的小孩〉因此被看見了,很多出版人和讀者跟我說:「哇,原來妳也會寫小說。」(笑)這是滿有趣又無奈的現象:一個作者如何被認定,不是因為他寫了什麼,而是他被看見了什麼,以及如何被看見。
但的確是因為《父後七日》,我才開始跟寫作「玩真的」。之前幾年我都還不認為自己真的「能寫」、「愛寫」,它給了我許多信心與定力。
3、在妳的散文作品裡,讀者常常感受到小說的戲劇感。在妳的這部小說作品之中,也時時流露出散文樸實真摯的情感。對妳來說,寫散文和寫小說各自代表什麼呢?
寫散文是「再造已知」,比較像整理收納一個事件或狀態,像是規劃好的旅行,途中當然也會有驚喜,會有意外,會有小確幸。寫小說就如前面所說,像是帶著自己虛構出來的人物攀岩登峰,最後一起到達未曾想像的地方。
但兩者對我來說,不可稍有閃失的,都是「腔調」,也就是說故事的方式。我想腔調就會決定情感。
4、在《父後七日》裡,妳挑起了生命裡又輕又重而我們時常忘卻的悲傷,並告訴我們「請收拾好您的情緒,我們即將降落」。在《親愛的小孩》裡也時常觸及「悲傷」這個生命困境,但這裡的悲傷好像不只是一個事件,而比較接近一個常態,幾乎像是構成生命的一種元素。對妳來說,悲傷是什麼?妳希望透過故事裡悲傷的人來表達什麼?
與其用「悲傷」來說,不如來談談造成悲傷的原因吧。這十篇小說裡,有失去、分離、背叛、被欺騙、得不到所愛……或根本就只是迷惘騷亂、搞不定自己,而形成的大片悲傷。
我很喜歡的一部電影《戀戀風暴》裡,西恩潘飾演一個非常搞不定自己的人,不只無法控制情緒,還有暴力傾向,天天鬧事。最後他被關在監獄裡時,流著淚對來探監的妻子說:「我們人為什麼不可以一出生就很老了?越活越年輕、越來越有活力、越來越純真,然後最後在母親的子宮裡死去。」
既然成長、生老病死都是不可逆的必經過程,那麼途中必然會遇到各種傷害。我們無法一生下來就是身經百戰、世故圓熟的人,所以必定跌跌撞撞、吃虧學乖或學不乖。唯有等到塵埃落定,回頭一看,「唉,都過去了。」才有點雲淡風輕,有點成長。但下一次,它又來了。
我覺得這些傷害,並不完全是大到住院開刀那種。有時就像日積月累的肌肉僵硬或筋膜沾粘,我們偶爾去按摩或作些紓緩運動時,會說:「對!就是這個痠痛的感覺!」會發出美好的哀號,希望按摩師不要停(笑)。但只要我們每天使用身體,這些壓力或緊繃就會存在。我想我是用小說,點出或喚起這些必然存在的美好的痠痛吧。
5、在妳的作品中,「旅行」常常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旅行看起來像是流浪與漂移,也像是整理與重生。可否從《親愛的小孩》裡的這些故事來談談「旅行」,旅行之於主角的意義,之於妳寫作的意義。
我很喜歡在旅行中觀察人。因為一個區域的特性,會群聚某一種特定的人,我會抓取他們「想當然耳」的普遍性,再幫他們加上獨特性。如〈親愛的小孩〉的主角,的確有些是我去峇里島,從獨行女子身上採一點樣本,慢慢形塑出來,想當然耳,她們是來靈修、來度假、來希望可以遇到《享受吧,一個人的旅人》裡面的大帥哥,但有沒有可能她們之中有一人是很想生小孩的呢?我會這樣開始想。〈禮物〉則是我在洛杉磯華人區,看到有些來待產的華人孕婦,想當然耳,她們是為了美國籍。但也許裡面有更戲劇化的故事。
當然不可能看到一個樣本就決定了,都是一點點、一點點採樣而來。
旅行是一個移動、漂浮的狀態,充滿碰撞與機遇;十篇小說裡,很多處理到騷亂不定、躁動不安的生命狀態,所以很自然地加入旅行的部分。
旅行對我寫作的幫助,不只是在取材。而是,寫小說就像是進入一陌生之地;那麼,若能經常把自己丟到陌生地方,我想應該是很好的訓練。
6、《親愛的小孩》裡絕大部分的故事都以女性做為主要敘事口吻,這些女人擁有各自的特質和性格,妳如何塑造她們?如何讓她們走進故事裡?或者,如何讓她們發展成自己的故事?
我借用、但稍微改一下〈馬修與克萊兒〉裡面的話來說。小說裡的這些女性角色,應該都是「如果我是男的,我一定會喜歡上的那種女人。」(笑)
她們並非完美,各自有吸引人的地方,也都有性格上的弱點。每次寫到中間,我都會覺得好像已經跟她是很要好很要好的朋友,可是把她塑造完成之後,就必須告訴她:「嘿,我要離開了。」這才是寫小說最精采的開始。比如說〈禮物〉,下筆時,我以為大概也是寫個八千到一萬字,用「禮物」來講男女之間的品味與權力關係。但李君娟的形象越來越明顯之後,是故事跟隨著她發展了。等到寫到最後一個字,變成她在告訴我:「嘿,我要離開了。」
小說寫完之後的疲憊與後座力,我想有時是來自這裡──與心愛的人物告別。
對了,其實每位女主角都有各自的「主題曲」,甚至「片尾曲」。這些歌曲與音樂對我形塑人物與鋪陳情節非常有幫助。希望有機會可以分享給讀者聽聽。
7、假設現在有一個難搞的男人和難搞的女人,妳會推薦他們看《親愛
的小孩》裡的哪一個故事?
我想應該就看〈搞不定〉吧。可以比較看看誰比較難搞。
8、我們都相信有很多人看這本書會哭著笑、笑著哭,妳想對這本書的讀者說什麼?
曾有朋友告訴我:妳的小說太「好看」,會讓人以為妳的作品除此之外就沒有價值了。我知道他所謂的「好看」既是褒也是貶。褒的是,就是好看。貶的是,容易看,淺薄通俗。
但當然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希望讀者看到的東西。所以希望讀者在好哭好笑好看之外,還能多看出一些什麼。每個人的答案應該都不太一樣。
9、小說相較散文,應該更容易改編。這十篇小說,有改編成電影的計畫嗎?
不能每次都一魚兩吃啦。(笑)
但的確〈親愛的小孩〉有個同名劇本在進行。不過人物、情節與小說並不完全相同,比較像「現代男女求子記」,是個都會喜劇。
10、寫完兩本散文、集結了一本短篇小說集之後,接下來妳計畫寫什麼?
有一個日治時代家族故事,已經開頭很多年,一直沒寫完。我覺得是我之前的人情世故還不足以關照,每隔一段時間,我就會拿出來寫寫看,我有沒有能力帶著這些大正昭和時代的鄉紳和婦女,再往上攀爬一點。有些題材與情感,我相信絕對需要年紀與歷練才有能力處理,只靠自以為敏銳的天線與小聰明是撐不起來的。但我想這次應該不用再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