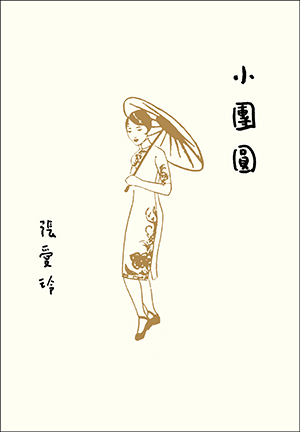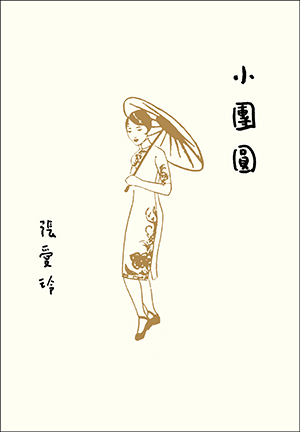內容試閱
一
大考的早晨,那慘淡的心情大概只有軍隊作戰前的黎明可以比擬,像《斯巴達克斯》裏奴隸起義的叛軍在晨霧中遙望羅馬大軍擺陣,所有的戰爭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為完全是等待。
九莉快三十歲的時候在筆記簿上寫道:「雨聲潺潺,像住在溪邊。寧願天天下雨,以為你是因為下雨不來。」
過三十歲生日那天,夜裏在床上看見洋台上的月光,水泥闌干像倒塌了的石碑橫臥在那裏,浴在晚唐的藍色的月光中。一千多年前的月色,但是在她三十年已經太多了,墓碑一樣沉重的壓在心上。
但是她常想著,老了至少有一樣好處,用不著考試了。不過仍舊一直做夢夢見大考,總是噩夢。
鬧鐘都已經鬧過了。抽水馬桶遠遠近近隆隆作聲。比比與同班生隔著板壁,在枕上一問一答,互相口試,發問的聲音很自然,但是一輪到自己回答,馬上變成單薄悲哀的小嗓子,逐一報出骨頭的名字,慘不忍聞。比比去年留級。
九莉洗了臉回到自己的小房間裏,剛才忘了關檯燈,乙字式小檯燈在窗台上,乳黃色球形玻璃罩還亮著,映在清晨灰藍色的海面上,不知怎麼有一種妖異的感覺。她像給針扎了一下,立刻去捻滅了燈。她母親是個學校迷,她們那時代是有中年婦女上小學的。把此地的章程研究了個透,宿舍只有檯燈自備,特為給她在先施公司三塊錢買了一隻,寧可冒打碎的危險,裝在箱子裏帶了來。歐戰出洋去不成,只好改到香港,港幣三對一,九莉也覺得這錢花得不值得。其實白花的也已經花了,最是一年補課,由牛津劍橋倫敦三家聯合招考的監考人自己教,當然貴得嚇死人。
「我先下去了,」她推開西部片酒排式半截百葉門,向比比說。
「你昨天什麼時候睡的?」
「我睡得很早。」至少頭腦清醒些。
比比在睡袋裏掏摸著。她家裏在香港住過,知道是亞熱帶氣候,但還是寄了個睡袋來,因為她母親怕她睡夢中把被窩掀掉了,受涼。她從睡袋裏取出一盞燈來,還點得明晃晃的。
「你在被窩裏看書?」九莉不懂,這裏的宿舍又沒有熄燈令。
「不是,昨天晚上冷。」當熱水袋用。「嬤嬤要跳腳了,」她笑著說,捻滅了燈,仍舊倒扣在床頭鐵闌干上。「你預備好了?」
九莉搖頭道:「我連筆記都不全。」
「你是真話還是不過這麼說?」
「真的。」她看見比比臉上恐懼的微笑,立刻輕飄的說:「及格大概總及格的。」
但是比比知道她不是及格的事。
「我先下去了。」
她拿著鋼筆墨水瓶筆記簿下樓。在這橡膠大王子女進的學校裏,只有她沒有自來水筆,總是一瓶墨水帶來帶去,非常觸目。
管理宿舍的修女們在做彌撒,會客室裏隔出半間經堂,在樓梯上就聽得見喃喃的齊聲唸拉丁文,使人心裏一陣平靜,像一汪淺水,水滑如油,浮在嘔吐前翻攪的心頭,封住了,反而更想吐。修女們的濃可可茶燉好了等著,小廚房門口發出濃烈的香味。她加快腳步,跑下水門汀小樓梯。食堂在地下室。
今天人這麼多,一進去先自心驚。幾張仿中世紀僧寺粉紅假大理石長桌,黑壓壓的差不多都坐滿了。本地學生可以走讀,但是有些小姐們還是住宿舍,環境清靜,宜於讀書。家裏太熱鬧,每人有五六個母親,都是一字並肩,姐妹相稱,香港的大商家都是這樣。女兒住讀也仍舊三天兩天接回去,不光是週末。但是今天全都來了,一個個花枝招展,人聲嘈雜。安竹斯先生說的:「幾個廣東女孩子比幾十個北方學生嘈音更大。」
九莉像給針扎了一下。
「死囉!死囉!」賽梨坐在椅子上一顛一顛,齊肩的鬈髮也跟著一蹦一跳,縛著最新型的金色闊條紋塑膠束髮帶,身穿淡粉紅薄呢旗袍,上面印著天藍色小狗與降落傘。她個子並不小,胸部很發達,但是稚氣可掬。「今天死定了!依麗莎白你怎麼樣?我是等著來命了!」
「死囉死囉」嚷成一片。兩個檳榔嶼華僑一年生也皺著眉跟著喊「死囉!死囉!」一個捻著胸前掛的小金十字架,捻得團團轉,一個急得兩手亂洒,但是總不及本港女孩子叫得實大聲洪,而又毫無誠意,不會使人誤會她們是真不得了。
「噯,愛瑪,講點一八四八給我聽,他們說安竹斯喜歡問一八四八,」賽梨說。
九莉又給針刺了一下。
地下室其實是底層。天氣潮濕,山上房子石砌的地基特高,等於每一幢都站在一座假山上。就連這樣,底層還是不住人,作汽車間。車間裝修了一下,闢作食堂,排門大開,正對著海面。九莉把墨水瓶等等擱在一張空桌子上,揀了個面海的座位坐下。飽餐戰飯,至少有力氣寫考卷──每人發一本藍色簿面薄練習簿,她總要再去領兩本,手不停揮寫滿三本,小指骨節上都磨破了。考英文她可以整本的背《失樂園》,背書誰也背不過中國人。但是外國人不提倡背書,要背要有個藉口,舉得出理由來。要逼著教授給從來沒給過的分數,叫他不給實在過意不去。
但是今天卷子上寫些什麼?
死囚吃了最後一餐。綁赴刑場總趕上大晴天,看熱鬧的特別多。
婀墜一面吃,一面彎著腰看腿上壓著的一本大書。她是上海人,但是此地只有英文與廣東話是通用的語言,大陸來的也都避免當眾說國語或上海話,彷彿有什麼瞞人的話,沒禮貌。九莉只知道她姓孫,中文名字不知道。
她一抬頭看見九莉,便道:「比比呢?」
「我下來的時候大概就快起來了。」
「今天我們誰也不等,」婀墜厲聲說,俏麗的三角臉上一雙弔梢眼,兩鬢高弔,梳得虛籠籠的。
「車佬來了沒有?」有人問。
茹璧匆匆走了進來,略一躊躇,才坐到這邊桌上。大家都知道她是避免與劍妮一桌。這兩個內地轉學來的不交談。九莉也只知道她們的英文名字。茹璧頭髮剪得很短,面如滿月,白裏透紅,戴著金絲眼鏡,胖大身材,經常一件二藍布旗袍。劍妮是西北人,梳著兩隻辮子,端秀的鵝蛋臉,蒼黃的皮膚使人想起風沙撲面,也是一身二藍布袍,但是來了幾個月之後,買了一件紅白椒鹽點子二藍呢大衣,在戶內也穿著,吃飯也不脫,自己諷刺的微笑著說:「穿著這件大衣就像維多利亞大學的學生,不穿這件大衣就不像維多利亞大學的學生。」不久,大衣上也發出深濃的蒜味,掛在衣上都聞得見,來源非常神秘。修女們做的雖然是法國鄉下菜,顧到多數人的避忌,並不擱蒜。劍妮也從來不自己買東西吃。
她雖然省儉,自己訂了份報紙,宿舍裏只有英文《南華晨報》。茹璧也訂了份報,每天放學回來都急於看報。劍妮有時候看得拍桌子,跳起來腳蹬在椅子上,一拍膝蓋大聲笑嘆,也不知道是丟了還是收復了什麼地方,聽地名彷彿打到湖南了。她那動作聲口倒像有些老先生們。她常說她父親要她到這安靜的環境裏用心念書,也許是受她父親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