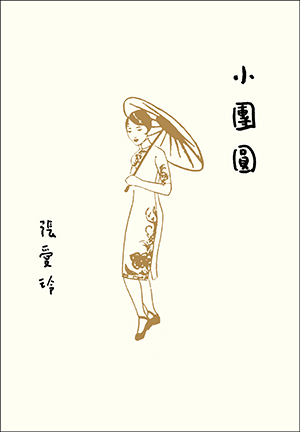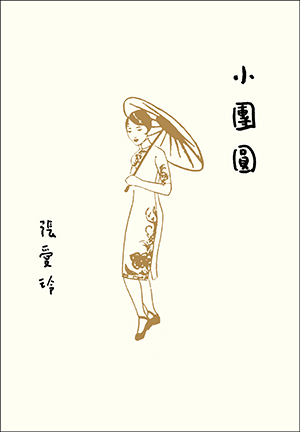內容試閱
有一天散了學,九莉與比比懶得上樓去,在食堂裏等著開飯。廣東修女特瑞絲支著燙衣板在燙衣服。比比將花布茶壺棉套子戴在頭上,權充拿破崙式軍帽,手指著特瑞絲,唱吉爾柏作詞,瑟利文作曲的歌劇:「大的小賤人,且慢妄想聯姻。」("Refrain, audacious tart, your suit from pressing.")原文雙關,不許她燙衣服,正磨著她上樓去點浴缸上的煤氣爐子燒水。特瑞絲趕著她叫「阿比比,阿比比,」──此外只有修道院從孤兒院派來打雜的女孩子瑪麗,她叫她「阿瑪麗」──嘁嘁喳喳低聲托比比代問茹璧婀墜可要她洗燙,她賺兩個私房錢,用來買聖像畫片,買衣料給小型聖母像做斗篷。她細高個子,臉黃黃的,戴著黑邊眼鏡。
比比告訴九莉她收集了許多畫片。
「她快樂,」比比用衛護的口吻說。「她知道一切都有人照應,自己不用心。進修道院不容易,要先付一筆嫁妝,她們算是嫁給耶穌了。」
她催比比當場代問茹璧,但是終於上樓去向亨利嬤嬤要鑰匙燒洗澡水。比比跟著也上去了。
九莉在看小說,無意中眼光掠過劍妮的報紙,她就笑著分了張給她,推了過來。
九莉有點不好意思,像誇口似的笑道:「我不看報,看報只看電影廣告。」
劍妮微笑著沒作聲。
寂靜中只聽見樓上用法文銳聲喊「特瑞絲嬤嬤」。食堂很大,燈光昏黃,餐桌上堆滿了報紙。劍妮摺疊著,拿錯了一張,看了看,忽道:「這是漢奸報,」抓著就撕。
茹璧站了起來,隔著張桌子把沉重的雙臂伸過來,二藍大褂袖口齊肘彎,衣服雖然寬大,看得出胸部鼓蓬蓬的。一張報兩人扯來扯去,不過茹璧究竟慢了一步,已經嗤嗤一撕兩半。九莉也慢了一步,就坐在旁邊,事情發生得太快,一時不吸收,連說的話都是說過了一會之後才聽出來,就像閃電後隔了一個拍子才聽見雷聲。
「不許你誣蔑和平運動!」茹璧略有點嘶啞的男性化的喉嚨,她聽著非常詫異。國語不錯,但是聽得出是外省人。大概她平時不大開口,而且多數人說外文的時候都聲音特別低。
「漢奸報!都是胡說八道!」
「是我的報,你敢撕!」
劍妮柳眉倒豎,對摺再撕,厚些,一時撕不動,被茹璧扯了一半去。劍妮還在撕剩下的一半,茹璧像要動手打人,略一躊躇,三把兩把,把一份報紙擄起來,抱著就走。
九莉把這一幕告訴了比比,由比比傳了出去,不久婀墜又得到了消息,說茹璧是汪精衛的姪女,大家方才恍然。在香港,汪精衛的姪女遠不及何東爵士的姪女重要,後者校中就有兩個。但是婀墜是上海人,觀點又不同些。茹璧常到她房裏去玩。有一天九莉走過婀墜房門口,看見茹璧在她床上與賽梨扭打。茹璧有點男孩子氣,喜歡角力。
這些板壁隔出來的小房間「一明兩暗」,婀墜住著個暗間,因此經常起兩扇半截門,敞亮透氣些。九莉深夜走過,總看見婀墜在攻書,一隻手托著一隻骷髏,她像足球員球不離手,嘴裏念念有詞,身穿寶藍緞子棉浴衣,披著頭髮,燈影裏,背後站著一具骨骼標本,活像個女巫。
劍妮有個同鄉常來看她,穿西裝,偏於黑瘦矮小,戴著黑框眼鏡,面容使人一看就馬上需要望到別處去,彷彿為了禮貌,就像是不作興多看殘廢的人。劍妮說是她父親的朋友。有一次他去後,亨利嬤嬤打趣,問「劍妮的魏先生走了?」劍妮在樓梯上回頭一笑,道:「人家魏先生結了婚的,嬤嬤!」
亨利嬤嬤仍舊稱他為「劍妮的魏先生」。此外只有個「婀墜的李先生」,婀墜與一個同班生等於訂了婚。
劍妮到魏家去住了幾星期,暫時走讀。她說明魏先生的父母都在香港,老夫婦倆都非常喜歡她,做家鄉菜給她吃,慣得她不得了。他們媳婦不知道是沒出來還是回去了。
此後隔些時就接去住,劍妮在宿舍裏人緣不錯,也沒有人說什麼。一住一個月,有點不好意思,說「家鄉菜吃胖了。」
比比只說:「同鄉對於她很重要。」西北固然是遠,言外之意也是小地方的人。
九莉笑道:「她完全像張恨水小說裏的人,打辮子,藍布旗袍……」
比比在中國生長的,國產片與地方戲也看得很多,因也點頭一笑。
張恨水小說的女主角住到魏家去卻有點不妥,那魏先生又長得那樣,恐怕有陰謀。嬤嬤們也不知道作何感想?亨利嬤嬤仍舊照常取笑「劍妮的魏先生」。香港人對北方人本來視同化外,又不是她們的教民,管不了那麼許多,況且他們又是世交。而且住在外面,究竟替宿舍省了幾文膳食費,與三天兩天回家的本地女孩子一樣受歡迎。只有九莉,連暑假都不回去,省下一筆旅費。去年路克嬤嬤就跟她說,宿舍不能為她一個人開著,可以帶她回修道院,在修道院小學教兩課英文,供膳宿。當然也是因為她分數打破紀錄,但仍舊是個大情面。
還沒搬到修道院去,有天下午亨利嬤嬤在樓下喊:「九莉!有客來找你。」
亨利嬤嬤陪著在食堂外倚著鐵闌干談話,原來是她母親。九莉笑著上前低聲叫了聲二嬸。幸而亨利嬤嬤聽不懂,不然更覺得他們這些人古怪。她因為伯父沒有女兒,口頭上算是過繼給大房,所以叫二叔二嬸,從小覺得瀟洒大方,連她弟弟背後也跟著叫二叔二嬸,她又跟著他稱伯父母為大爺大媽,不叫爸爸媽媽。
亨利嬤嬤知道她父母離了婚的,但是天主教不承認離婚,所以不稱盛太太,也不稱卞小姐,沒有稱呼。
午後兩三點鐘的陽光裏,她母親看上去有點憔悴了,九莉吃了一驚。也許是改了髮型的緣故,雲鬢嵯峨,後面朝裏捲著,顯瘦。大概因為到她學校宿舍裏來,穿得樸素點,湖綠布襯衫,白帆布喇叭管長。她在這裏是苦學生。
亨利嬤嬤也是彷彿淡淡的。從前她母親到她學校裏來,她總是得意非凡。連教務長密斯程──綽號「汽車」,是象形,方墩墩身材,沒頸項,鐵青著臉,厚眼鏡炯炯的像一對車燈──都也開了笑臉,沒話找話說,取笑九莉丟三拉四,捏著喉嚨學她說「我忘了。」她父親只來過一次,還是在劉氏女學的時候。因為沒進過學校,她母親先把她送到這家熟人開的,母女三個,此外只請了一個老先生與一個陸先生。那天正上體操課,就在校園裏,七大八小十來個女生,陸先生也不換衣服,只在黃柳條布夾袍上套根黑絲,繫著口哨掛在胸前,剪髮齊肩,稀疏的前劉海,清秀的窄長臉,嬌小身材,一手握著哨子,原地踏步,尖溜溜叫著「幾夾右夾,幾夾右夾。」上海人說話快,「左右左右」改稱「左腳右腳,左腳右腳。」九莉的父親頭戴英國人在熱帶慣戴的白色太陽盔,六角金絲眼鏡,高個子,淺灰直羅長衫飄飄然,勾著頭笑嘻嘻站在一邊參觀,站得太近了一點,有點不好意思。下了課陸先生也沒過來應酬兩句。九莉回去,他幾次在舖上問長問短,含笑打聽陸先生結了婚沒有。
她母親到她學校裏來總是和三姑一塊來,三姑雖然不美,也時髦出風頭。比比不覺得九莉的母親漂亮,不過九莉也從來沒聽見她說過任何人漂亮。「像你母親這典型的在香港很多,」她說。
的確她母親在香港普通得多,因為像廣東人雜種人。亨利嬤嬤就是所謂「澳門人」,中葡混血,漆黑的大眼睛,長睫毛,走路慢吞吞的,已經中年以後發福了。由於種族歧視,在宿舍裏只坐第三把交椅。她領路進去參觀,暑假中食堂空落落的,顯得小了許多。九莉非常惋惜一個人都沒有,沒看見她母親。
「上去看看,」亨利嬤嬤說,但是並沒有一同上樓,大概是讓她們單獨談話。
九莉沒問哪天到的。總有好兩天了,問,就像是說早沒通知她。
「我跟項八小姐她們一塊來的,」蕊秋說。「也是在牌桌上講起來,說一塊去吧。南西他們也要走。項八小姐是來玩玩的。都說一塊走──好了!我說好吧!」無可奈何的笑著。
九莉沒問到哪裏去,香港當然是路過。項八小姐也許不過是到香港來玩玩。南西夫婦不知道是不是到重慶去。許多人都要走。但是上海還沒有成為孤島之前,蕊秋已經在鬧著「困在這裏一動也不能動。」九莉自己也是她泥足的原因之一,現在好容易走成了,歐戰,叫她到哪裏去呢?
事實是,問了也未見得告訴她,因為後來看上去同來的人也未見得都知道蕊秋的目的地,告訴了她怕她無意中說出來。
在樓上,蕊秋只在房門口望了望,便道:「好了,我還要到別處去,想著順便來看看你們宿舍。」
九莉也沒問起三姑。
從食堂出來,亨利嬤嬤也送了出來。瀝青小道開始坡斜了,通往下面的環山馬路。兩旁乳黃水泥闌干,太陽把藍磁花盆裏的紅花晒成小黑拳頭,又把海面晒褪了色,白蒼蒼的像汗濕了的舊藍夏布。
「好了,那你明天來吧,你會乘公共汽車?」蕊秋用英文向九莉說。
亨利嬤嬤忽然想起來問:「你住在哪裏?」
蕊秋略頓了頓道:「淺水灣飯店。」
「噯,那地方很好,」亨利嬤嬤漫應著。
兩人都聲色不動,九莉在旁邊卻奇窘,知道那是香港最貴的旅館,她倒會裝窮,佔修道院的便宜,白住一夏天。
三人繼續往下走。
「你怎麼來的?」亨利嬤嬤搭訕著說。
「朋友的車子送我來的,」蕊秋說得很快,聲音又輕,眼睛望到別處去,是撇過一邊不提的口吻。
亨利嬤嬤一聽,就站住了腳,沒再往下送。
九莉怕跟亨利嬤嬤一塊上去,明知她絕對不會對她說什麼,但是自己多送幾步,似乎也是應當的,因此繼續跟著走。但是再往下走,就看得見馬路了。車子停在這邊看不見,但是對街有輛小汽車。當然也許是對門那家的。她也站住了。
應當就這樣微笑站在這裏,等到她母親的背影消失為止。──倒像是等著看汽車裏是什麼人代開車門,如果是對街這一輛的話。立刻返身上去,又怕趕上亨利嬤嬤。她怔了怔之後,轉身上去,又怕亨利嬤嬤看見她走得特別慢,存心躲她。
還好,亨利嬤嬤已經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