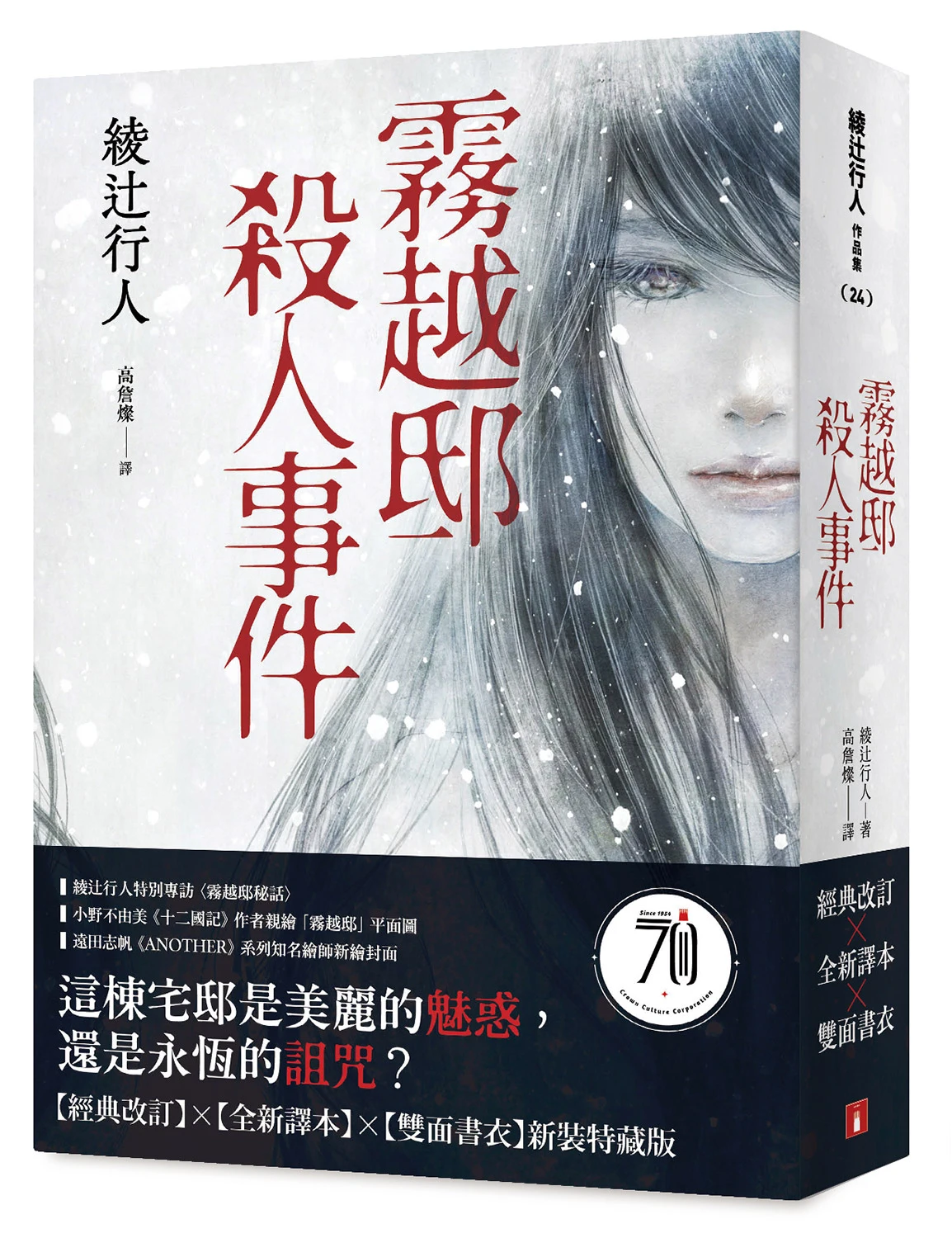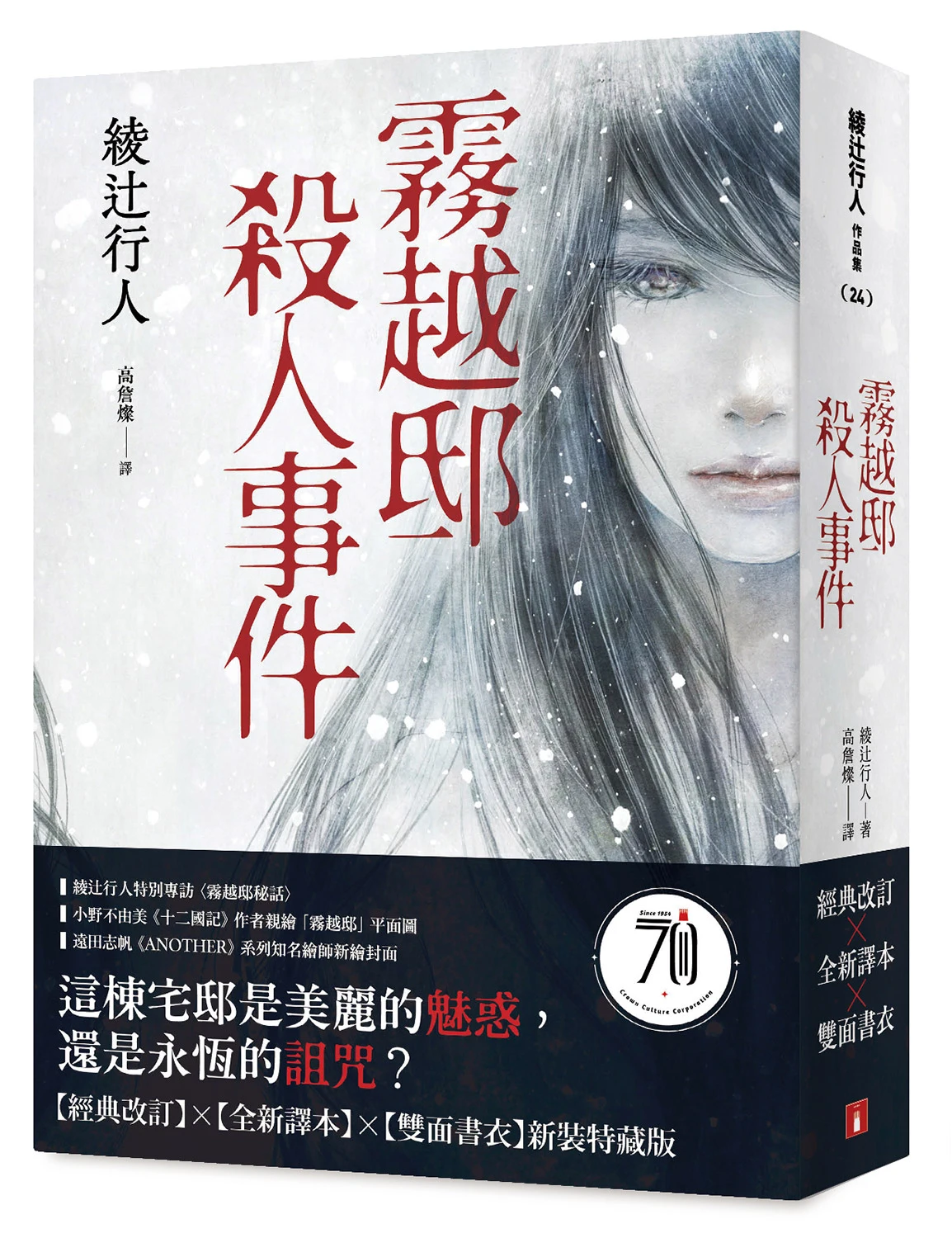內容試閱
第一幕 劇團「暗色天幕」
1
「哦,來了一整個團體的同伴。」
甫一走進房內,便傳來一個像馬鳴般高亢的聲音,我們皆大感困惑,就此停步。
聲音的主人就坐在一進門裝設在左手邊正中央牆上的壁爐前,是一位戴著銀色圓框眼鏡,個頭矮小,年近半百的男子。壁爐內燒的是真正的火焰,散發紅光,他就坐在壁爐前的凳子上,雙手擺在火上取暖,身子沒動,只轉動他粗短的脖子,衝我們一笑。
他身上穿著像是手工編織的白色厚毛衣,年約五十五歲左右,不,應該已年近六十了吧。雖已童山濯濯,但從鼻子下方到嘴巴、下巴一帶,卻覆滿了蓬鬆的白鬍鬚,形成強烈對比。
咦,這男人就是宅邸的主人嗎?
我一時這麼認為,不過其他人似乎也是同樣的心思。
「請問……」
率先踏進房內的槍中秋清,以請教的口吻開口說道,結果男子笑容滿面地說道:
「不不不。」
他抬起單手,大動作地直搖手。
「剛才我不是提到同伴嗎?我也是在這場暴風雪下前來借住躲雪的人。」
聽到他這麼說,眾人不由得露出放心的表情,我也不例外。緊張感化解後,凍僵的身體才漸漸對房內的暖氣有反應,一下子熱了起來。
「您好……啊。」
是緊跟在我身後,最後一位走進的蘆野深月發出的聲音。我轉頭一看,發現她手扔握在敞開的那扇門的門把上,納悶地望向走廊。
「怎麼了嗎?」
經我詢問後,深月一邊輕撫她濡濕的烏黑長髮,一邊偏著頭應道:
「為我們帶路的人不見了。」
原來如此,帶我們到二樓這個房間的男人,已不見人影。我什麼也沒說,就只是微微聳了聳冷得僵硬的肩膀。
「那個人感覺怪陰森的。」深月說。
「確實是個態度冷淡的男人。」
「不光這樣,感覺他好像一直盯著我的臉上下打量。」
那是因為妳長得漂亮啊—我想這麼說,但急忙打住。
因為我可不想要在這種情況下說出這句話,就此成了無關緊要的一句玩笑話,而被人遺忘,此時我的臉上一定露出了很生硬的表情。
其他人都爭先恐後地擠向壁爐前伸手烤火,我一邊在嘴邊摩擦著失去感覺的雙手,一邊催促深月趕緊跟大家一起過去。
以淡綠色的大理石打造的壁爐上方,以厚實的櫸木裝設了一排裝飾層架,兩端擺放長長的銀燭臺,燭臺中間擺上鮮豔的彩繪陶壺以及以縝密的螺鈿裝飾的小盒子。我對此沒什麼了解,但每個看起來都像是歷史悠久,價格不菲。
這些物品後方的牆壁掛著一面橢圓形的大鏡子,映照出我們在壁爐前擠在一起的模樣,我們每個人都一臉茫然,不發一語地面向爐火。
待身體漸漸暖和後,我重新環視室內。
這是一座寬敞的歐式房間,若以榻榻米來計算,大概有三十張榻榻米那麼大吧。我在東京(雖然這麼說,但也不是在二十三區)租的兩房一廳的房子,都遠比不上這個房間來得寬敞。天花板也很高,足足有三公尺以上。
從設有壁爐的那面牆對面,一直從房間中央,霸氣地設置了豪華的布面沙發組,好幾個裝飾層架,填滿了鋪白色壁紙的牆壁。地板上鋪設了漂亮的波斯地毯,配色是以紅為底色,以暗綠當主色,上頭加入唐草圖案的編織。
但當中最吸睛的,是前方左手邊(若從進門處來看,則是在正前方)的牆壁。那面牆幾乎整面都是玻璃,只有離地約一公尺的褐色裙板部分不是玻璃,它以上一直到天花板全是玻璃。
緊緊地嵌在黑色的細木格子裡,邊長約三十公分的正方形圖案玻璃,那泛青的色澤,可能也因為周遭光線的因素,感覺猶如置身深海,深邃地浮現出從天花板垂吊而下的枝形吊燈的形體。
「哎呀,真是太驚人了。」
在凳子上移向一旁,為我們挪出空位的那名先到的男子,柔和地瞇起他圓眼鏡底下的眼睛,向我們搭話。
「突然下起這樣的大雪,真教人吃不消,你們是來旅行的嗎?」
「嗯,可以這麼說。」
槍中摘下因蒸汽而起霧的金色細框眼鏡應道。
「那您呢?呃,您是當地人嗎?」
「是啊,我好歹也算是位醫生,敝姓忍冬。」
「冷冬?」
「對,忍耐度過寒冬的忍冬。」
很特別的姓氏,說到「忍冬」,是日文「吸葛」的漢名,是每到梅雨季就會綻放淡紅色可愛小花的一種花草。
「忍冬醫生是吧,這樣啊。」
槍中一副了然於胸的表情點了點頭,接著視線落向腳下,改以愉快的表情重新打量對方。
「嗯,這可真是有趣的巧合呢。」
「這話怎麼說?」
「就是這塊地毯啊。」
「啥?」老醫生為之一愣,順著槍中再度望向腳下的視線望去。
「這地毯怎樣嗎?」
「您不知道嗎?」
接著槍中望向在一旁聽他們對話的我,向我問道:
「鈴藤,你知道嗎?」
我不發一語搖了搖頭。
「是這塊波斯地毯的圖案,你仔細看,和所謂的唐草圖案大不相同對吧。整體偏大,而且每一根草都獨立,莖的部分畫得特別長,加以強調,葉子則特別少。」
經他這麼一說,看起來確實與阿拉伯的唐草圖案不太一樣,而且也感受不到什麼異國的風格,倒不如說它隱隱散發著一股日本味。
「這是以吸葛畫成的圖案,人稱忍冬唐草圖案。」
「哦,這麼說來……」
「也可簡稱為忍冬圖案,若追溯它的起源,我記得是古希臘的棕櫚圖案吧。這是經由波斯、印度,傳到中國和日本,之後便得到這樣的稱呼。」
老醫生發出「哦」的一聲讚嘆,槍中轉身對他說道:
「您不覺得這是有趣的巧合嗎?在這第一次見面的場合下,地上鋪的地毯,它上頭圖案的名字,竟與第一次見面的人擁有的姓氏相同。忍冬是個很罕見的姓氏,說起來,打從我們走進這個房間的那一刻起,就給了我們提示。」
「原來是這麼回事。」忍冬醫師的那張圓臉眉開眼笑,布滿皺紋。「您可真是博學呢,我這個人對自己工作外的事一概不知。哎呀,連有忍冬圖案這種東西都不知道。」
「忍冬醫生是到這戶人家來看診的嗎?」
「不,我是到其他地方去看診,回來時遇上大雪,覺得這情況不太對勁,急忙跑來這裡投靠。」
「真是明智之舉,我們是差點凍死路旁。」
槍中瘦削的臉龐浮現笑意,在外衣的內側口袋掏找。
「抱歉,這麼晚才介紹,敝姓槍中。」
他從錢包裡取出一張因沾濕而縐巴巴的名片,遞給對方。這時,還留在他袖口上的雪花脫落,撒落一地。
「槍中……這名字念作『AKIKIYO』是嗎?」
「『清』念作『SAYA』。所以是『AKISAYA(秋清)』。」
「這樣啊。哦~您是導演?這麼說來,是電視劇的導演嗎?」
「不,我只是個小小劇團的導演。」
「劇團,真不簡單呢。」
老醫師就像一個發現什麼稀奇玩具的小孩般,雙眼炯炯生輝。
「我們叫『暗色天幕』,是在東京演出的一個小劇團。」
「是所謂的前衛劇團吧,其他人也都是劇團裡的成員嗎?」
「是的。」
槍中頷首。
「這位是鈴藤稜一。」
他指著我說道。
「他是我大學的學弟,立志當一位作家,雖然不是劇團的成員,但我常會請他幫忙寫劇本。其他六人都是我們劇團裡的演員。」
「東京劇團的人全跑來這裡,有什麼目的呢?總不會是要到這種鄉下地方舉辦地方公演吧?」
「我很遺憾,我們的身分還沒辦法舉辦地方公演。」
「這麼說來,是為了集訓之類的吧?」
「這個嘛,與其說集訓,不如說是一場小型的員工旅行吧。」
「那又怎麼會闖進這樣的深山裡呢?」
忍冬醫師一直維持他那充滿福態的笑臉,直爽地提出各種問題。而槍中也順著他的提問,開始說明我們來到這座宅邸的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