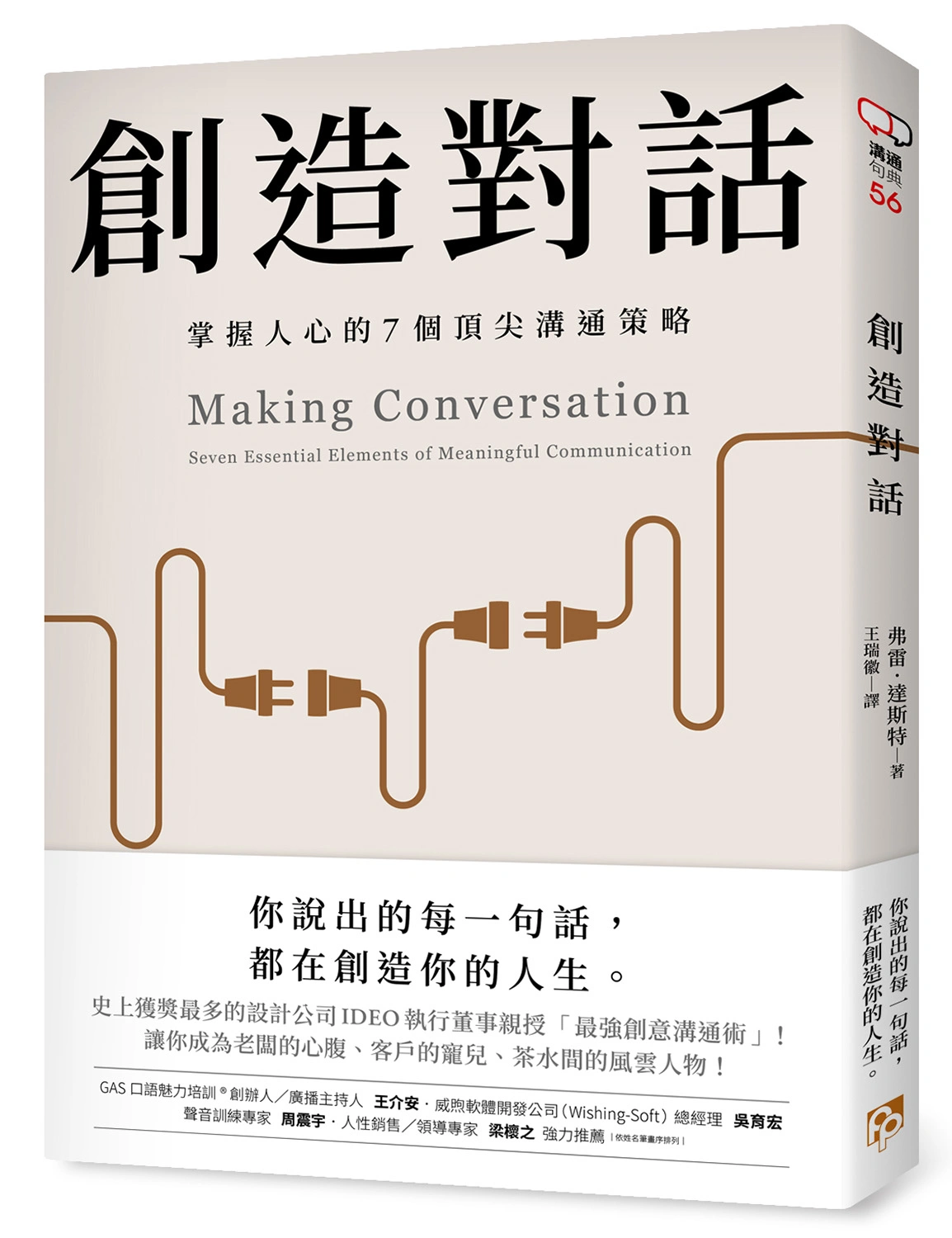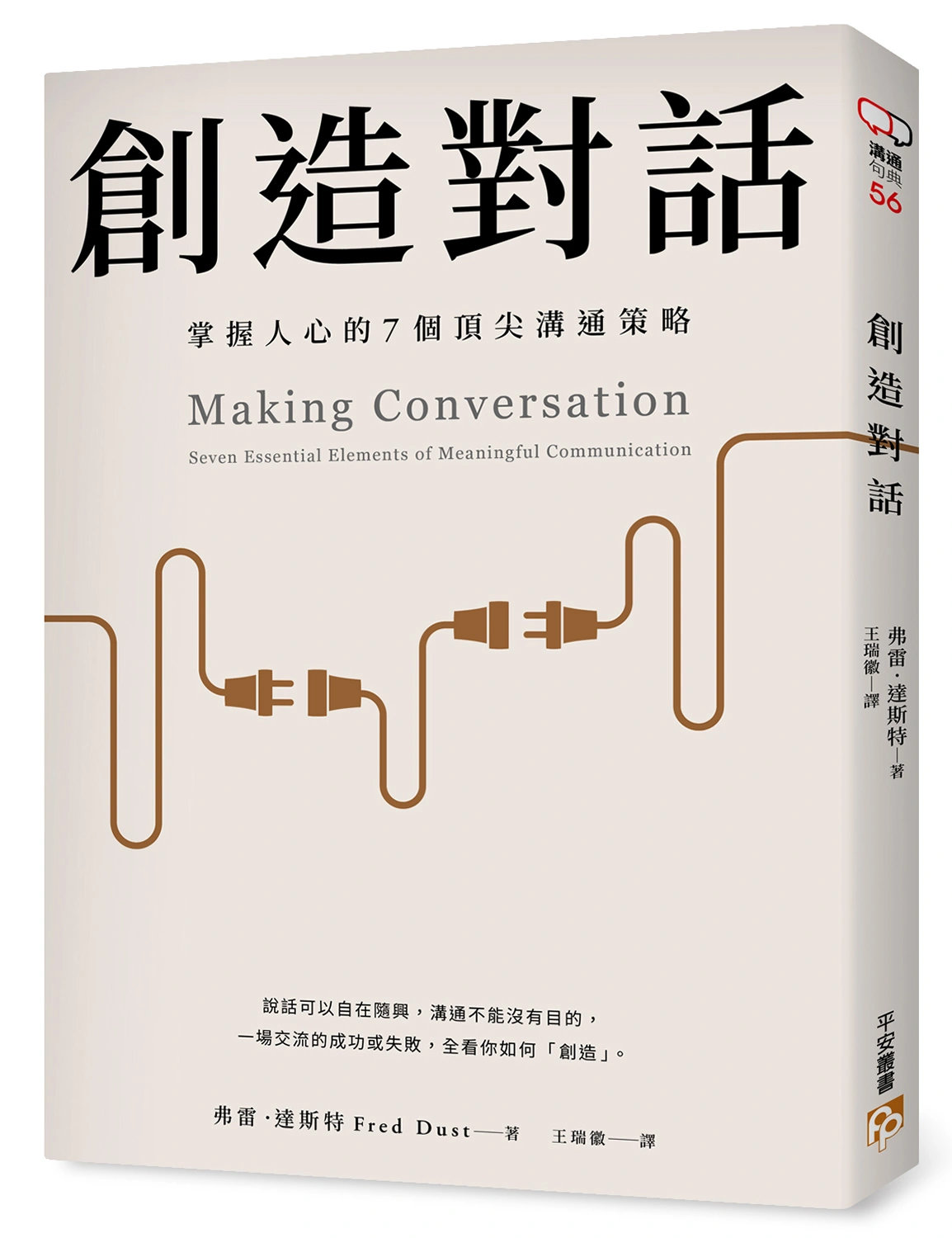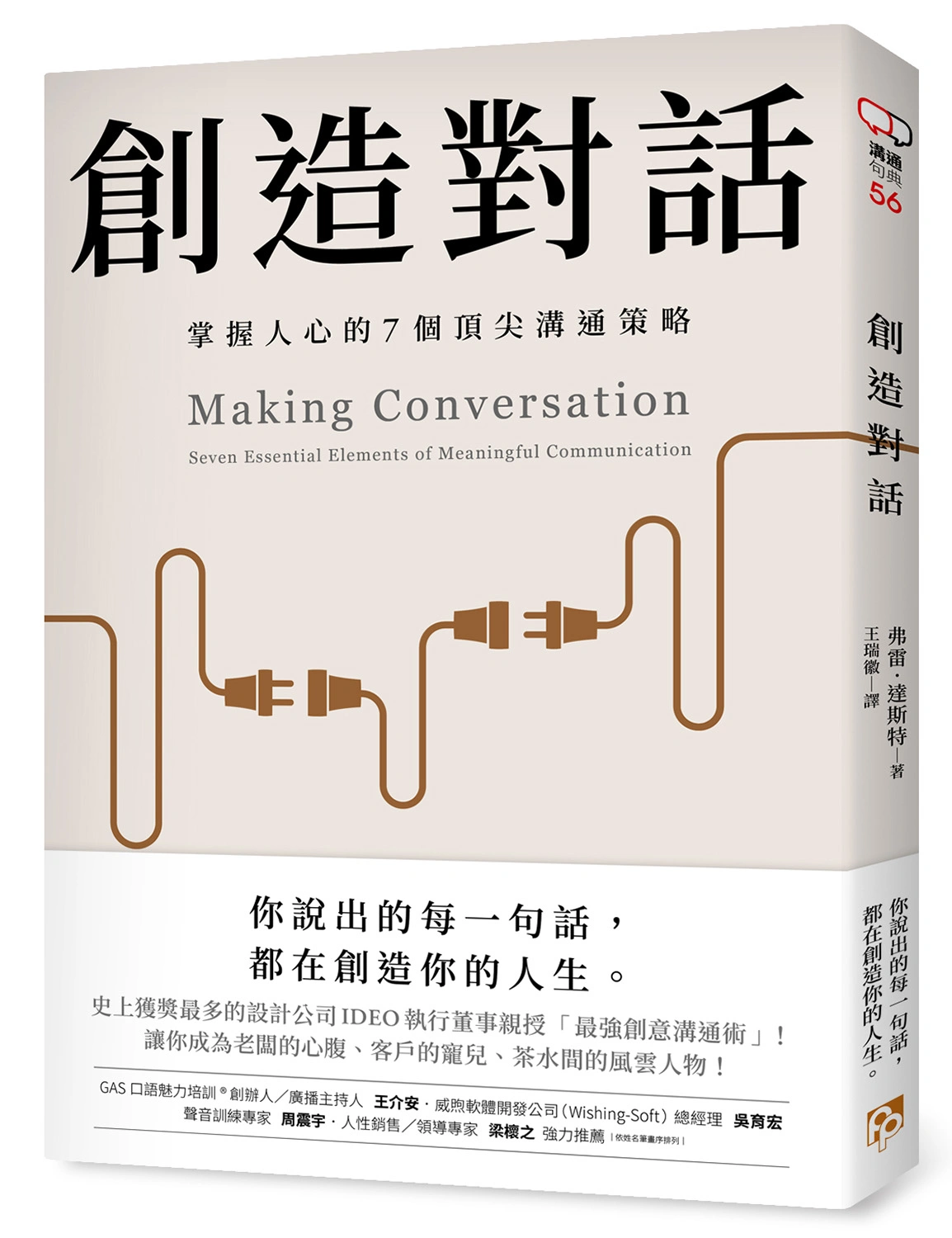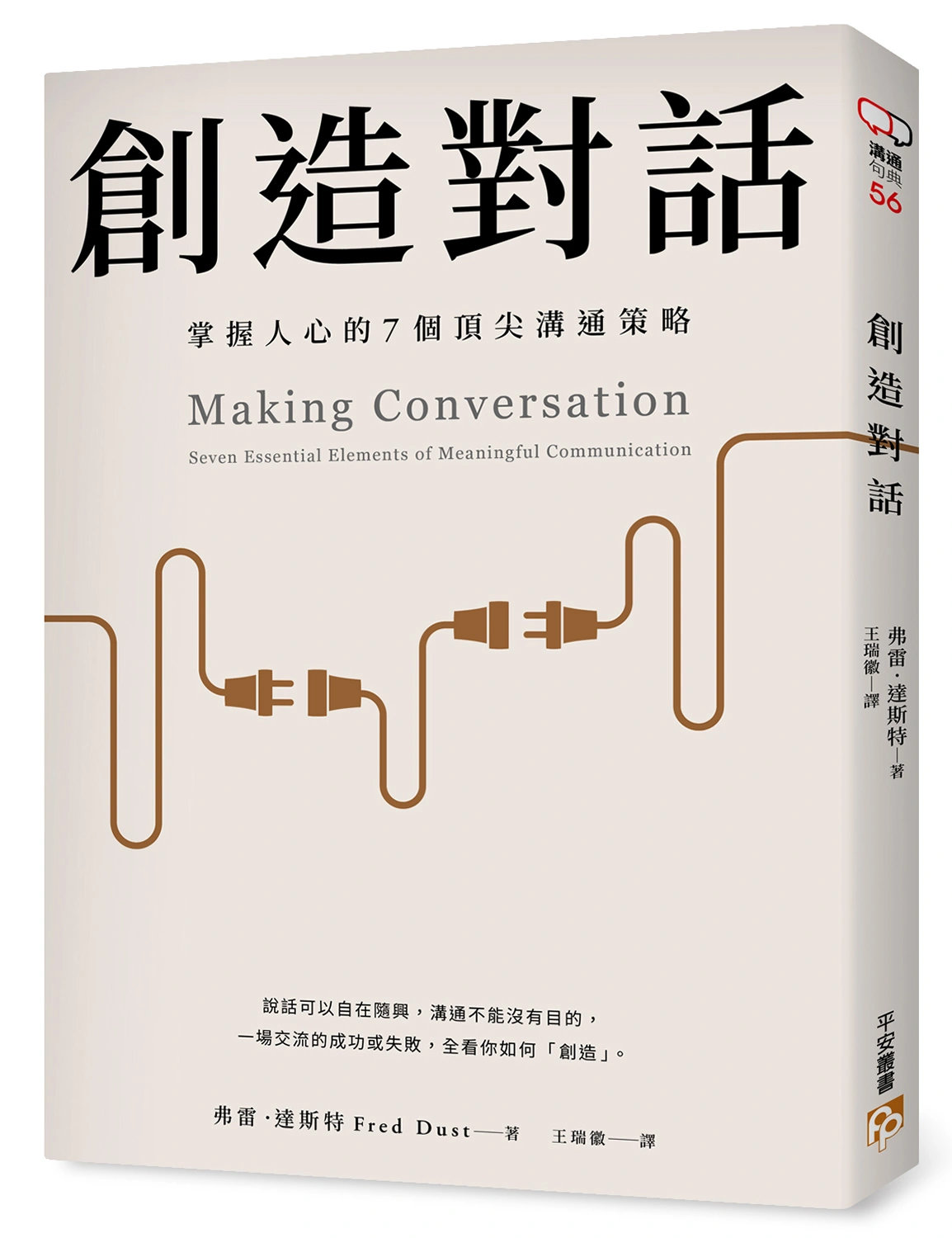內容試閱
我在二○○○年加入IDEO,並建立了IDEO的建築實踐。IDEO公司的設計文化原本就具有高度合作的性質,要將合作過程擴展到我們設計的服務對象並不難。
我親自致力於分解建築語言,使得整個過程和原則更加簡明,讓我們的客戶真正成為協同設計者。我們讓護理師設計病患的房間。我們搭建全尺寸的概念性教室模型,和教師們在其中閒聊走動,在過程中改變他們的想法。那是一種構建式、建設性對話的設計,是我在亞歷山大的設計中所看到的東西的演化物。
但是在我們進行這工作的當中,發生了十分有趣的事。
許多學校、非營利組織、慈善團體和政府單位找上我們,想知道我們是否能解?更大、更根本的問題。這些都是剛萌生的挑戰,但我意識到這正是我真正想做的那類工作。而且,毫不奇怪,我發現自己又回到起點,基本上做的是我在大學和畢業後一直在做的事:把人們聚在一起,運用創意做出改變。而就像ACT UP或者邊境藝術集團的許多企劃,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從正確的對話開始的。
這對我影響重大,因為我們開始建立一種業務,致力於集結一些高度多樣化的組織,以便共同解?像是收入不平等、槍枝暴力和醫療保健之類的更大規模、更根本的社會問題。
這類企劃意謂著將非營利組織或基金會、營利組織或私人公司,以及政府這三組人馬聚集一堂,進行「三方」(tri-sectoral)對話。當然,這種對談肯定是困難重重,三方參與的理由也往往相當分歧。隨之而來的是更細微的問題。有時欠缺共同語言,有時則是對談話該如何進行,甚至事情的進展速度持有不同看法。早在這項工作開始時我便發現,當我們把不同的利益關係方、團體、政治或文化實體聚集在一起,期待做出改變時,我們手上的工具還不夠理想。
我的一個重大轉捩點發生在二○一○年初。當時我在希臘,剛在一場充滿政府官員和大筆資金的集會上做了得罪人的發言。我正要離開房間,一群穿黑套裝的人把我團團圍住,將我逼進了後面屋角。在短暫但極為焦慮的瞬間,我被困在了原地。突然間,希臘總理喬治.巴本德里歐(George Papandreou)出現在這群安全人員當中。他不但沒有憤怒的言語或驅趕的意思,還邀請我和他一起晚餐。
當天稍晚,我發現自己坐在雅典海岸的一間空酒館裡,面前只有總理、他的特別探員和他的妻子,迷人的地中海第一夫人艾達。他的手機響個不停,來電的是正在尋求庇護的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畢竟,當時正值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運動的期間。總理低頭看著桌上的手機,說:「有時候,只要能讓政府慢下來,就能避開危機。」
當時感覺很奇怪,甚至有些天真。但如今回想起來,我了解到,刻意地設計較慢的對話,也許確實能讓我們解?許多重大問題。說來簡單,但並非基本。這是第一次,但絕不是我最後一次從這位總理那裡獲得關於對話的驚人洞見,他是一個骨子裡深植著雅典式民主的男人。接下來幾年,隨著希臘面臨經濟危機的衝擊,以及之後的幾年裡,我和喬治有過多次關於對話的對話。
喬治在非常嫻熟於私下交流,看出阻礙或改進互動的前因後果。他告訴我,兩個世界領導人可能會在談判桌上鬧僵,但如果我們並肩站在海中,水深達腰際,遙望著地平線,我們或許能找到另一種和諧。他渴望有一種授權雅典計程車司機協助激勵公民對話的計畫。「他們是真正的對話仲裁者。」在街頭,他這麼對我說。
我的那些和喬治之間關於談話的談話讓我清楚了解一件事:想要重新設計我們的社會結構,我們必須反過來重新設計它的核心作業工具——對話本身。
因此,我們必須開始認真研究該如何重新設計對話。問題顯而易見:我們該如何加快建立共同語言的過程?我們如何能讓人公開談論他們各自的目標?而如果我們能讓人達成協議,你如何能確定協議會帶來行動?儘管問題十分淺顯,答案卻需要下功夫精心設計。
二○一六年,我們成功利用新的對話模式來解?設計問題,這些問題從和美國民眾以及剛成立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合作,一直到和安第斯山脈的非營利組織和農民合作不等。我和衛生部長就健康、焦慮和壓力等問題進行了各種新的對話,並探討了透過在許多希臘村鎮的廣場上進行對話,來減輕希臘金融危機壓力的方式。我和亞斯本研究院的菁英以及布魯克林區的槍枝暴力受害者展開新的對話模式。
這些模式的範圍和預期影響各不相同:有的是關於思考傾聽藝術的新方法的一系列短期動態課程,有的則是為了讓數百人探索新的點子和理論,並且立時獲得一群人的支持。這些形式打破了對話慣例,有著新且更嚴格的規則,它們結合了動作或道具,在建構中包含了編舞藝術和技能。所有這些新的談話方式,我們都將在接下來的章節中逐一探討。
我們不斷進步。我們不斷創造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