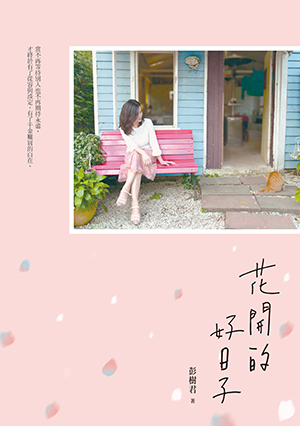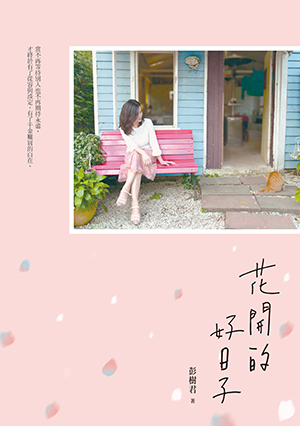內容試閱
一瞬之光
這個傍晚,我外出散步,看見非常美麗的天空。
是那種被稱為莫內藍的顏色,也就是法國印象派畫家莫內晚年在接受白內障手術之後,看見了一般人看不見的紫外線,所畫出的藍色睡蓮那種藍。
莫內藍,此刻映入我眼中的天空藍,是黃昏最後的微光,這種不屬於人間的藍色,據說可以直抵人心最幽深之處。
我停下腳步,虔敬地仰起臉,把整座天空看進眼中,收入心底。再過一會兒,這微光就要淹沒在漸深的黑夜之中。這樣的一瞬之光接近一種天啟。身旁不斷有人來來去去,然而沒有人抬頭看向天空,因為他們專注於掌中狹小的視窗,忽略了頭頂之上,那個巨大美麗的藍色視窗。在這樣的當下,彷彿只有我看見了某種神祕的指引,就像一個Just for me的祕密。
在這一瞬間,生命中無數的一瞬一起重現,也一起幻滅。
也是在這一瞬間,我想起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在我年紀很輕的時候,我曾經無法在黃昏的天空下行走,因為我害怕看見一日的餘光消失,害怕進入夜色之中。當那樣的光直抵我內心最幽深之處時,總是讓我無法承受。所以我習慣在黃昏時待在室內,並且拉上厚重的窗簾,假裝外面的世界並不存在。
後來有人告訴我,那是「黃昏憂鬱症」,是對於一日將盡的惆悵與失落。
但此刻,我獨自凝視著那同樣是莫內藍的天空,沉浸在它無邊遼闊的寧靜美麗之中,心中卻是充滿喜悅與恩寵。為什麼我的心境如此不同?
或許過去那不是憂鬱,而是對於美在瞬間消逝的不捨與留戀,所以寧可不要看見,因為沒有得到就沒有失去。然而在經歷了人生種種,好的壞的,歡愉的悲傷的,光明的黑暗的,在這一切的發生之後,我已經明白,無常是人生的本質,就像一瞬之光的天空。
生命是無數的一瞬,是一個片刻連著一個片刻,不知什麼時候,我已學會放手讓那些片刻過去,不再留戀也不再回想,不再因為害怕失去而不敢擁有,也不再因為已經失去而憾恨。於是如今我不但能安然地在黃昏的天空下行走,還能駐足欣賞那即將消失的微光,這或許表示我心中對於未知的恐懼已得到了療癒。
在一日將盡的此刻瞥見這一瞬之光,就像在長長的人生裡,無數擦肩而過的機緣中,一次驚鴻一瞥的偶遇與回眸。雖然每一個一瞬終將逝去也正在逝去,或是已經逝去,但我知道,只要我心甘情願地放這一瞬走,這一瞬我就得到了自由。
現在的自己
一個朋友約我看戲。散場之後,我們一起去喝長島冰茶,然後為了把酒醒一醒,沿著深夜的街道慢慢散步。
無人的台北街頭有一種繁華落盡的靜謐氣氛,很適合我們中年微涼的心境。我和朋友認識的時候還很年輕,年輕到人生簡直不算真正開始,後來各自經歷了命運的曲折起伏,有過各種悲歡離合,足夠各寫一部可歌可泣的長篇小說。如今,那些曾經讓我們以為過不去的傷心事終成往昔,再回首時已經皆付笑談中了。
朋友問我,如果時光可以倒流,還願意回到年輕的自己嗎?我說,不,好不容易才走到現在呢,回去做什麼?把走過的路再走一遍嗎?豈不前功盡棄。
年輕的自己擁有大把的光陰和無限的可能,卻也擁有太多的不安與不定,說得好聽是青春飛揚,但同等的意思就是心緒浮躁。那時太容易喜歡別人,也太容易對人失望,太容易相信別人,也太容易因人受傷。那時還不懂得如何與自己好好相
處,常常要拿枝微末節來和自己過不去。那時與人相處也總是驚惶而敏感,擔心犯錯,也果然犯了許多錯,並且付出了不少代價。
現在的自己依然會犯錯,但有了年紀的優勢就是知道怎麼與自己和解,就算還是會低落,也知道如何從另一個角度解讀得失。比起從前,現在有待面對與解決的難題更多,但看待世情不再非黑即白,已經懂得如何去欣賞人性中的砂礫與人生中的灰色地帶。
我並不懷念年輕的自己,但我接受所有走過的道路,不管那其中有多少錯誤和傷痛,因為是它們成就了現在的自己。那些錯不像臉書上的貼文,寫壞了可以刪除或隱藏,它們是切切實實地發生了,也造成了必然的損傷,但人生本來就不完美,而現在有彈性接受這樣的不完美,知道那就是真實的人生。只要有這樣一個小小的體悟,所有的坎坷就值得了。
生命像一列火車轟隆隆駛過,揚起煙塵,再漸漸沉寂下落,曾經渴望的都得到了,其中有些已失去,另一些也不再那麼重要,所有的狂喜與狂悲宛如一場夢境,過了也醒了。現在的自己不再年輕,卻總算有了一張心平氣和、在任何狀況下都可以微笑的臉。
「所以,比起年輕時的我,我更喜歡現在的自己。」我說。
朋友笑了。「我也是。」他說。
當不再等待別人也不再期待永遠,才終於有了從容與淡定,有了千金難買的自在。我和朋友都同意,那是比起青春美貌更好的東西。
見面
以前想念一個朋友,我們給他打電話,現在想念一個朋友,我們追蹤他的臉書。但還是有些朋友選擇在雲端之外,過著與臉書絕緣的生活,例如Jonson。
Jonson一週有三天在花蓮教書,而我在報社的工作最早也要十點才能下班,兩人的時間要能湊得上並不容易,僅管如此,我們還是每隔一陣子就相約見面,在深夜的小酒館或居酒屋裡,搭配蟹肉煎餅或干貝串燒,以彼此的近況做為下酒的材料,也只有這樣我才能了解他最新的動態,畢竟他不用臉書。
在臉書統治全世界的今天,能安然做臉書王國的化外之民,頗有一種獨釣寒江雪的孤冷,也像堅持自己用捲紙捲菸草一樣,幾乎可說是一種個人風格了吧。
我自己加入臉書的時間也算晚的,若不是因為喜歡大衛芬奇的《社群網戰》,所以才心生好奇,想研究看看臉書究竟是怎麼回事,說不定現在也沒有臉書帳號。因為我總覺得,臉書這種最初只是幾個大學男生在男生宿舍裡惡搞出來的發明,彷彿有著某種一不小心就可能失控的危險。臉書是一張效益弘大的公眾布告欄,傳遞與交換訊息的速度既快又廣,卻也因此而容易招惹是非,更容易失去個人隱私,所以與它維持安全距離是必要的,私事不能說,心事也不能說,說了十之八九要後悔。
不能告訴臉書的私事與心事,只能告訴值得信賴的朋友了。
但縱使有三千個臉書朋友,真能聽你傾吐心中塊壘的又有幾人呢?
真正的感情,還是得在真實的生活中才能感受。就算與某個朋友在臉書上互動得再熱絡,中間還是隔著終端機的海洋,感覺其實並不那麼精準。畢竟如果沒有近距離地感受到他的氣息、碰觸到他的肢體、看得到他的表情,又怎能聽得到他心裡真正的聲音?
所以,當我因想念某個朋友而去看他的臉書動態時,總不禁要思索,這些輕描淡寫的文字背後還有哪些隱藏的訊息?他快樂嗎?最近好嗎?如果可以的話,還是約出來見見吧。
就像紙本書很難被電子書取代一樣,見面這件事,還是很重要的,情感這種東西,也終究不是在電腦、手機或iPad的兩端想像出來的。人與人之間的氣味、溫度與擁抱,face to face的表情、眼神與微笑,再先進的3C產品也無法製造。見面的當下,那外在的環境與內在的心境所交織而成的感覺與氣氛,後來都會成為偶爾
掠過心頭的回憶,那樣進入心裡的畫面,永遠無法被任何電子產品所取代。
收集三千個臉書帳號,不如有一個可以一起談心的朋友。所以,哪天約他見見面,一起去散散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