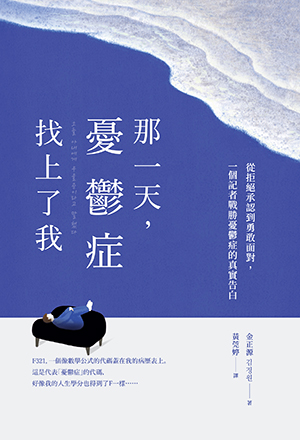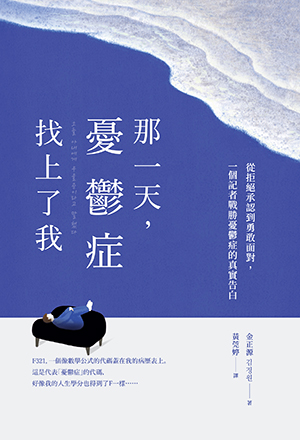內容試閱
精神科的藥
「我開抗憂鬱劑和抗不安劑給你,先服用一陣子看看。」
就診的第一天,我本來抱著僥倖的心態,打算接受心理諮商就好,不吃藥。不過醫生以溫柔卻不失堅定的態度開藥給我,沒人愛吃藥,再說,更沒人會愛吃「精神科的藥」吧。
「接受藥物治療之後,等狀態好起來,我們就正式開始心理諮商,你現在這種狀態,就算做了諮商也沒有多大效果。」
醫生把人的身體、心理和想法三者之間的關係畫在白紙上,認真說明了好一陣子。
「我……要吃多久的藥?」
「抗憂鬱劑起碼要吃六個月以上,抗不安劑視情況而定,會慢慢地減輕藥量。」
醫生對數百名、數千名患者都說過一樣的話,就像是一個教書教了幾十年,把書本背得滾瓜爛熟的老師一樣,一口氣解釋了為什麼不能一次大幅減藥的原因。這是由於如果藥吃到一半,病情有了好轉就馬上大幅減藥,有可能會復發,他也不忘告訴我藥物的副作用。
「抗憂鬱劑和抗不安劑不一樣,不會立刻見效,至少要吃兩三個禮拜才行。下次我會稍微增加藥量。」
血清素、受體、額葉、賀爾蒙、交感神經等各種陌生字眼在診間漫天飛舞,我彷彿隔天要參加大學入學考試,正在聽考前猜題補教名師講座的學生般專注。聽是聽了,卻一知半解,我只確定了一件事:那就是未來一年,我都得乖乖吃藥。
結束看診的我走出診間等候,沒過多久,護士就叫了我的名字,給了我處方箋。在我詢問領藥藥局位置的同時,護士不正面回答卻說了句:「請拍照。」「拍照?」護士看出我的疑惑,好心解釋是要我拍下處方箋。我掏出手機拍下處方箋後,護士就把它拿走了。幾分鐘後她走回來,手上拿著一包鼓鼓的藥袋,然後把藥袋給我,順口叮囑著:「早、中、晚三次服用,一天吃三次,不是一定的,但飯後吃會比較好。」
我好奇地問:「為什麼我不用去藥局拿藥?藥是醫院直接開給我的嗎?」答案就在我的處方箋上,那個被蓋上去的F開頭精神科代碼。原來醫院考慮到精神科患者去藥局可能會覺得不自在,所以由醫院直接開立精神科的藥。明明是考慮到患者的立場,我卻覺得不舒服,暗想:「原來是擔心我直接去藥局,會被別人知道我是精神科患者啊。」我翻出剛剛拍的處方箋照片,上頭的藥名從三個字到十個字不一,有顆粒也有膠囊。看到處方箋和藥袋,我總算有了真實感。
「我真的變成精神科患者了。」
拿完藥走出醫院的我雙腳瞬間發軟。我靠在走廊牆上,稍微喘了口氣,實在沒力氣搭公車回家,於是叫了計程車。在車上,我兩手緊抓藥袋,打給了妻子。
「老婆,醫生說我是憂鬱症。」
從此我和憂鬱症展開了非自願同居生活。
她的眼淚
她沉默著。一聽到我確診憂鬱症的消息,我本以為她多少會有一些反應,誰知道她一言不發地回房間了……真叫我傷心。被獨自留在客廳的我如同行屍走肉般拿起遙控器,打開電視,從一號頻道轉到六百號頻道,有藝人造訪美食餐廳的節目,也有海外旅遊節目,還有和寵物度過快樂時光的節目。總之,和平的電視世界宛如在嘲笑我的不幸。
不知不覺過了午夜,我關電視回房,看見妻子睡在女兒旁邊,不,是看起來睡著了。我一躺下,她立刻起身走出房間。客廳很快地傳來了電視的嘈雜聲,不久之後,電視聲中夾雜了啜泣聲。我知道,是她在哭泣,「我該不該去客廳?」煩惱的我最後選擇繼續躺在床上,因為我不知道出去能說什麼,萬一說錯話,事情會變得更糟糕吧。後來我聽妻子說,她那時氣的是我竟然想作出極端選擇,並不是因為我得了憂鬱症。
妻子帶著紅腫的雙眼和我一起吃早餐。自始至終沉默的她,就連我要去上班了,也沒開口叮嚀我出門小心安全。那一天,我心不在焉,滿腦子都在盤算告訴公司我得憂鬱症的時機點,最後我索性請了半天假,提早下班。
趁女兒去學校,我和妻子臨時在家裡召開了「憂鬱症緊急對策會議」。因為讓女兒知道我得憂鬱症沒什麼好處,商量過後,我們決定隱瞞女兒這件事。在會議過程中,妻子的眼裡噙滿淚水,她的問題如暴雨襲捲而至,像是我要看多久的病?吃藥會不會吃上癮?公司那邊打算怎麼處理?問題攻勢好不容易告一段落後,她提出了新意見:
「要不要去別家醫院看看?也許是誤診。就算是憂鬱症,應該會有醫生選擇諮商治療,不採用藥物治療的吧?」
我說服強烈排斥用藥的妻子,既然已經看了醫生,就要相信醫生。
「再去幾次醫院,如果有問題或是不同意醫生的作法,到時候我們再來考慮,好嗎?」
雖說天生性格使然,我不愛改變已經作好的決定,不過我反對妻子的建議另有原因─換了醫生,我又要重講一次我的情況,而且是在素昧平生的醫生面前。這讓我很反感。第一次告訴醫生我的情況時,內心湧起一股悲慘的感覺,該說感覺像是明明沒犯罪卻像被抓到把柄,帶到刑警面前嗎?總之,對於再經歷一次相同的事,我敬謝不敏。
妻子露出不滿的神情,勉強妥協,暫時維持現階段的治療方式,「先這樣做吧,不過如果你覺得哪裡不對勁,一定要去別家醫院。狀況變差或是吃藥不舒服,一定要馬上告訴我,知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