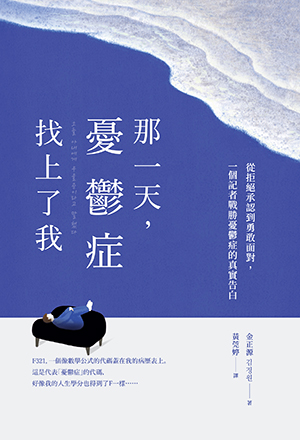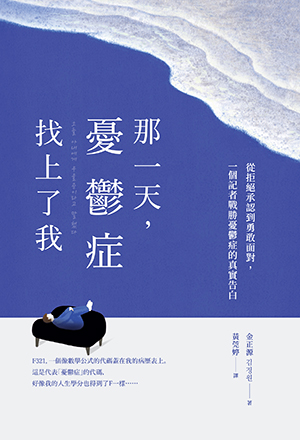內容試閱
太太登場
憂鬱症緊急會議兩週後,妻子猝不及防地宣布:
「無論如何,我要去見那位醫生才行。」
「為什麼?」
「太太去見丈夫的主治醫生,是天經地義的事,和醫生打聲招呼我才能放心。」
「喔……那我先跟醫生說一聲。」
我感到很難為情,有必要帶她去醫院嗎?其實妻子違背了我們的協議,她向親朋好友打聽到一位大家推薦的「名醫」,瞞著我去預約掛號。我以「上次已經說好,先觀察看診情況再說」試圖反說服妻子,妻子卻再出奇招,說要親自見我的主治醫生。
「您太太說要過來嗎?家人會帶給治療很大的幫助,下次看診的時候請她一起過來吧。」聽完我的說明,主治醫生爽快地答應。
去見主治醫生的一個禮拜前,妻子就像在準備面試的高三應屆考生,忙著把想問的問題整理在筆記本上,陣仗之大,活像要採訪哪位偉大的名人似的。手冊上的內容五花八門,甚至有好幾個(主要和夫妻房事相關的)問題,真的是荒謬到不行!我請她刪去那些問題,妻子沒回答我,只露出令人費解的表情。回診當日,我和太太手牽手到了醫院,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很幸運。跟著先生去醫院絕對不是會讓太太愉快的事情,更不用說,去的還是「身心精神科」。不知道和我一起去醫院的妻子,腦海中在想些什麼呢?
妻子一進到醫院,神情變得安心許多,「比我想得更清爽俐落。」坐在門診候診區,妻子四處打量,細心觀察醫院的每個角落,眼神之銳利,宛如一名搜索犯罪現場的刑警,不能輕易放過任何小線索。護士喊了我的名字,我以在學校闖了禍,不得不請爸媽到校的孩子的心情,把太太迎進診間。不知道妻子是不是因為太過緊張,以至於不敢直視醫生的雙眼。她的眼神固定在問題手冊上,用略上揚的語氣進入提問環節。
「為什麼一直增加抗憂鬱劑劑量?」
「要吃多久的藥?」
「我先生現在比以前更常發呆,這樣子沒關係嗎?」
「能完全康復嗎?預計的治療時間是多久?」
「為什麼他會得憂鬱症?」
連珠炮的問題讓人不禁聯想到大企業面試的緊張場合。除了事前和我約定好的問題之外,妻子還是沒放過十九禁問題。醫生並沒有因為「夫人」的提問而驚慌失措,從頭到尾保持微笑,仔細說明我的症狀及家人們的協助對策。這次的看診時間比前幾次長很多,要不是護士告知下一位病人已經到了,好像會持續一整天。
在結束看診的回家路上,妻子意味深長地說:「那位醫生……還不錯,我會取消別家醫院的預約。可是啊,醫生的聲音超級平,聽久了好睏啊,一直用『Do Re Mi』的『Mi』音在說話,精神科醫生都是這樣的嗎?」
從那天起,主治醫生多了一個「咪咪(Mi Mi)醫生」的綽號。
咪咪醫生
「您太太怎麼說?」
咪咪醫生微笑問道。上次咪咪醫生不慌不忙地應對突然登場的妻子,用特有的低沉嗓音看診。咪咪醫生擁有不會過於低沉也不會讓人感到輕浮的音色。如果國家有規定精神科醫生的聲音高低,我想咪咪醫生的聲音非常合格。
精神科醫生的聲音和醫學劇裡常見的醫生有很大的差異。如果是需要進手術室嚴陣以待、要求助手送上手術刀的醫生,比起聲音,這種醫生的「開刀技術」和「膽量」才是左右手術結果的主要原因。假如碰上緊急情形,比如說患者突然噴血、或是血壓驟降、又或者是心臟脈搏變慢,醫生要保持冷靜繼續手術才有望拯救患者的生命。而精神科醫生的手術刀就是他們的聲音。除了藥物治療之外,在和患者諮商的過程中,精神科醫生會通過聲音傳遞同理心,使諮商順利進行。精神科醫生是用話語撫慰因他人帶刺的話而受傷的患者靈魂。
當然,我並不是說富有魅力的聲音是成為優秀精神科醫生的必要條件。我也不會憑聲音決定主治醫生的人選。第一次決定去精神科,上網尋找醫院時,找到的醫院多如過江之鯽,我超級茫然,究竟該去哪一家好?所以我制定了一套自己的標準。
首先,第一個標準是性別。我希望我的醫生是位男性。我絕無性別歧視之意,這就跟女性偏好女婦產科醫生一樣。其次,我把年輕的醫生排除在候選名單之外,我畢竟是四十多歲的人,希望醫生能和我年紀相仿或是比我年長。無論如何,年紀差不多的醫生應該更能理解我的處境。
最後,過濾掉常上電視或是一聽名字就知道是誰的名人醫生。因為我每次在電視上看到那些醫生和律師,都很懷疑他們到底什麼時候有空看他們的患者或委託人。我相信有些人時間管理做得好,忙歸忙,還是有一心多用的餘力,不過,既然是挑選治療心理疾病的精神科醫生,我希望醫生能全心全意地關注我。點進醫院官網或部落格,看了一些醫生的簡歷之後,我的心中大致有底。
另外,便利性也是我考慮的因素之一。我主要尋找離家或離公司近的醫院,我怕距離醫院太遠,一想到要花大把時間奔波,就會打退堂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