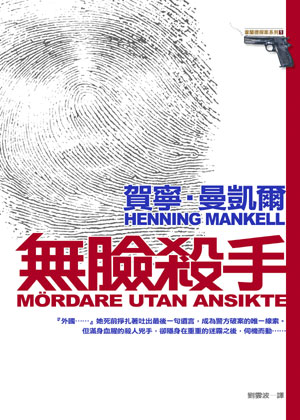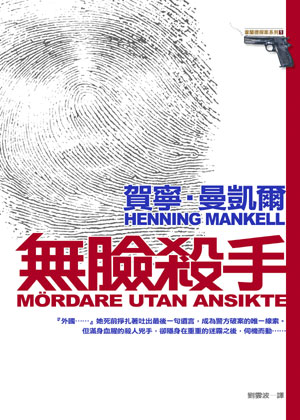內容試閱
警車在通往卡岱湖的一條岔路上等著他。冰凍的沙礫被輪胎軋得嘎吱嘎吱響。韋蘭德跟在警車後面,駛過通往圖納魯的岔道以後繼續往陡峭的山坡上爬,最後到達萊納爾。汽車晃晃悠悠地開上一條比農耕車小徑強不了多少的狹窄、骯髒的小路,走了一公里之後,終於到達現場。他們看到兩個相連的農場、兩所刷成白色的農場住宅,還有兩個被精心照料過的花園。
一個老人趕緊向他們走來。韋蘭德一看見那個老人,就意識到的確有不愉快的事情在等著他處理。老人眼中的恐懼可不是想像出來的。
『我把門砸開了,』老人狂躁不安地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我把門砸開了,因為我得進去看看。不過她很快也會死的。』
他們從砸破的門進去,一股刺鼻的老人氣味撲面而來。壁紙是老式的。為了能在昏暗的光線裡看見東西,韋蘭德不得不瞇起眼睛。
『這裡出了什麼事?』他問。
『就在這兒。』老人回答。
接著,他哭了起來。三位警察面面相覷。韋蘭德用腳將門踹開。事情比他想像的還要糟糕,而且糟糕得多。後來他總是說,類似的案件他見得多了,但那是他所見過最慘的現場。
那對老夫婦的房間浸泡在血泊中,血甚至濺到天花板的吊燈上。老頭橫臥在床,上身沒有穿衣服,下半身的長衛生褲被扯了下來。面部損壞得無法辨認,似乎有人想要割下他的鼻子。他的雙手被反綁在背後,左大腿被砍碎,血紅的皮肉裡露出白森森的骨頭。
『哦,真他媽的。』韋蘭德聽見諾倫在他身後咕噥,感到一陣噁心。
『叫救護車。』韋蘭德說。他強忍著沒有嘔吐。『動作快一點。』
然後他們俯身察看老太太的傷勢。她被捆在一把椅子上,半臥在地板上,捆她的人還在她瘦削細長的脖子上勒了一條繩子。她還有微弱的呼吸。韋蘭德叫彼得斯找一把刀來。他們割斷深深勒進她手腕和脖子裡的細繩子,輕輕把她放在地板上。韋蘭德抱住她的頭放在自己的腿上。
他看看彼得斯,知道他們都在想著同一個問題:是誰殘忍到下如此毒手?竟然要用繩子勒死一個無助的老太太!
『去外面等,』韋蘭德對在走廊上抽泣的老人說:『去外面等著,不要碰任何東西。』
他覺得自己的聲音聽起來簡直就像是吼叫。我吼叫是因為我害怕,他想。我們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啊!過了將近二十分鐘救護車才到。老太太的呼吸越來越不規律,韋蘭德開始擔心救護車來得太遲了。他認識那位救護車司機,他叫安東森。
『嗨,』韋蘭德說:『他死了,但那老太太還活著。想辦法讓她活下去。』
『出了什麼事?』安東森問。
『但願她能告訴我們,如果她能活下來的話。現在快走吧!』
救護車在沙礫路上消失時,韋蘭德和彼得斯已經從屋子裡出來了。諾倫正用手帕擦臉。天漸漸亮了,韋蘭德看看錶,七點二十八分。
『這簡直是個屠宰場。』彼得斯說。
『有過之而無不及,』韋蘭德答道:『給局裡打電話,要求組一個各類人員齊全的專案小組。叫諾倫封鎖現場。』
風增強了,韋蘭德弓起背朝自己的汽車走去。事實上,他應該留下來幫現場勘察技術人員的忙,但他都快凍僵了,而且覺得噁心,所以若不是絕對必要,他不想再多待下去。再說,他看見雷柏格開著隊裡的車來了。這表示,技術人員得勘察完犯罪現場的每一吋土地之後才能回去。再有一、兩年就要退休的雷柏格可是一位滿腔熱忱的警察,別看他表面斯斯文文,慢吞吞的,他只要一來,保證能把犯罪現場查得一清二楚。
雷柏格有風濕病,拄著手杖。此刻他正一拐一拐地穿過院子向韋蘭德走來。
『不好看,』雷柏格說:『裡面像個屠宰場似的。』
『這話可不是你第一個說。』韋蘭德說。
雷柏格表情嚴肅。『有什麼線索嗎?』
韋蘭德搖搖頭。
『一點沒有嗎?』雷柏格的聲音裡含有某些請求的成分。
『鄰居們既沒聽見什麼,也沒看見什麼。我認為這是個普通的搶劫案。』
『這樣瘋狂的暴行你還說普通?』
雷柏格很不高興,韋蘭德後悔自己措辭不當。『我是說,沒錯啦,昨天夜裡有一些特別殘忍的傢伙光顧過這裡。他們是那種專靠洗劫孤寡老人們居住的偏僻農場過日子的強盜。』
『我們得抓住這些傢伙,』雷柏格說:『免得他們捲土重來。』
『說得對,』韋蘭德說:『無論如何都得抓住這些傢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