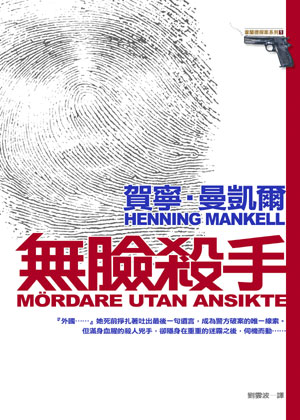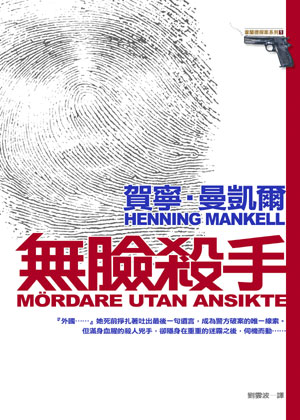內容試閱
韋蘭德駕車在萊納爾來回開了好幾趟。各家屋裡都有燈光,外面卻連個人影也沒有。他們知道了這件事會怎麼想呢?他自問。
他感到很不安。發現老婦人脖子上的繩套使他大為震驚,其殘忍程度令人不可思議。誰會做這種事呢?為什麼不拿斧頭朝她頭上一劈,當場了結呢?為什麼要折磨她呢?他開車穿過小鎮的時候,腦子裡在計畫偵辦方案。開到通往布蘭塔的交叉口,他把車停下來,因為冷而打開了暖氣,然後一動不動地在車裡坐著,兩眼凝視著地平線。
這起案件又得由他主導偵辦,這一點他很清楚,其他人都沒有這個可能。他接替雷柏格成了禹斯塔的刑事偵探。儘管他才四十二歲,局裡沒有人比他經驗豐富。
許多偵查工作都是例行公事:犯罪現場勘察、詢問萊納爾的居民以及強盜可能逃竄路線的附近居民。有誰發現了什麼可疑情況?有什麼反常的事情?這些問題已經在他的腦海裡響起。但韋蘭德憑經驗知道,農場搶劫案常常是很難破的。他唯一的希望就是那位老婦人能活下來。她目睹了所發生的一切,她知道情況。但假如她死了,這個雙重命案將會十分棘手。
他感到很難。在正常情況下,越是難破的案件越能激起他更大的熱情與活力。鑒於熱情與活力是所有警察工作的先決條件,他一直想像著自己是一個好警察。然而現在他卻感到沒有自信,感到自己很累。
他強迫自己把車子換到一檔。開了幾公尺遠,他又停了下來。剛才他彷彿突然意識到了在那個冰凍的冬天早晨看到的情況。
襲擊一對無助老夫婦毫無價值,而且又是如此殘忍,這究竟是為什麼?想到此,他不寒而慄。
這裡發生了原本不該發生的事。他望向車外,呼嘯的狂風猛烈地撞擊著車門。我得開始了,他想。這話很像是雷柏格說的。
『無論是誰幹的,我們都必須抓住他。』
他逕自將車開到禹斯塔的那家醫院,乘電梯來到加護病房。一進走廊,他就看見那個年輕實習警察馬丁森坐在病房外面的椅子上。韋蘭德有點惱火。難道局裡真沒有別的人了,非要派這麼個沒經驗的年輕實習警察來醫院嗎?他為什麼要坐在門外?他為什麼不坐在床邊,隨時捕捉被殘害的老太太最微弱的聲音呢?
『嗨,』韋蘭德說:『情況怎麼樣?』
『她仍在昏迷,』馬丁森回答說:『醫生似乎沒抱多大希望。』
『你為什麼坐在外面?為什麼不坐在病房裡?』
『他們說有什麼情況會告訴我的。』
韋蘭德注意到,馬丁森開始對自己失去了信心。
我說話很像一個壞脾氣的老師,韋蘭德想。他小心翼翼地推開門往裡面看。這個『候死室』裡有各種各樣的機器,牆上的一根根軟管一起一伏,好像是一群透明的軟體蟲。他推開門的時候,一位護士正站在那裡看記錄表。
『你不能進來。』她嚴厲地說。
『我是警官,』韋蘭德怯弱地回答說:『我只是想知道她怎麼樣了。』
『跟你說過了,請你在外面等。』護士說。
韋蘭德還沒來得及回答,一位醫生匆匆走進來。他覺得那位醫生看起來年輕得令人吃驚。
『我們不希望這裡有任何未經允許的人進來。』年輕醫生看到韋蘭德後說。
『我這就走,不過我只想瞭解一下她現在的情況。我叫韋蘭德,是警官。這是一樁命案,』他補充說,不知道這樣說能不能扭轉情勢,『是我負責調查這件案子。她情況怎麼樣?』
『她居然還活著,真是令人驚訝,』醫生說著,朝韋蘭德點點頭,要他到床邊來,『我們無法告訴你她所受內傷的程度。首先我們得看她是否能活過來。但她的氣管受到了嚴重創傷,好像有人要勒死她。』
『正是如此。』韋蘭德看著被單和軟管下面露出的那張消瘦的臉說。
『像她這種情況早就該死掉了。』醫生說。
『我希望她能活下來,』韋蘭德說:『她是我們現有的唯一證人。』
『我們希望所有的病人都能活下來。』醫生板著面孔說。他在觀察一個監視器,上面的綠色曲線連續波動著。
在醫生一再堅持無可奉告以後,韋蘭德離開了病房。傷勢的後續發展難以斷定,瑪麗亞洛夫格林可能會在昏迷中死去。這種事沒人敢打包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