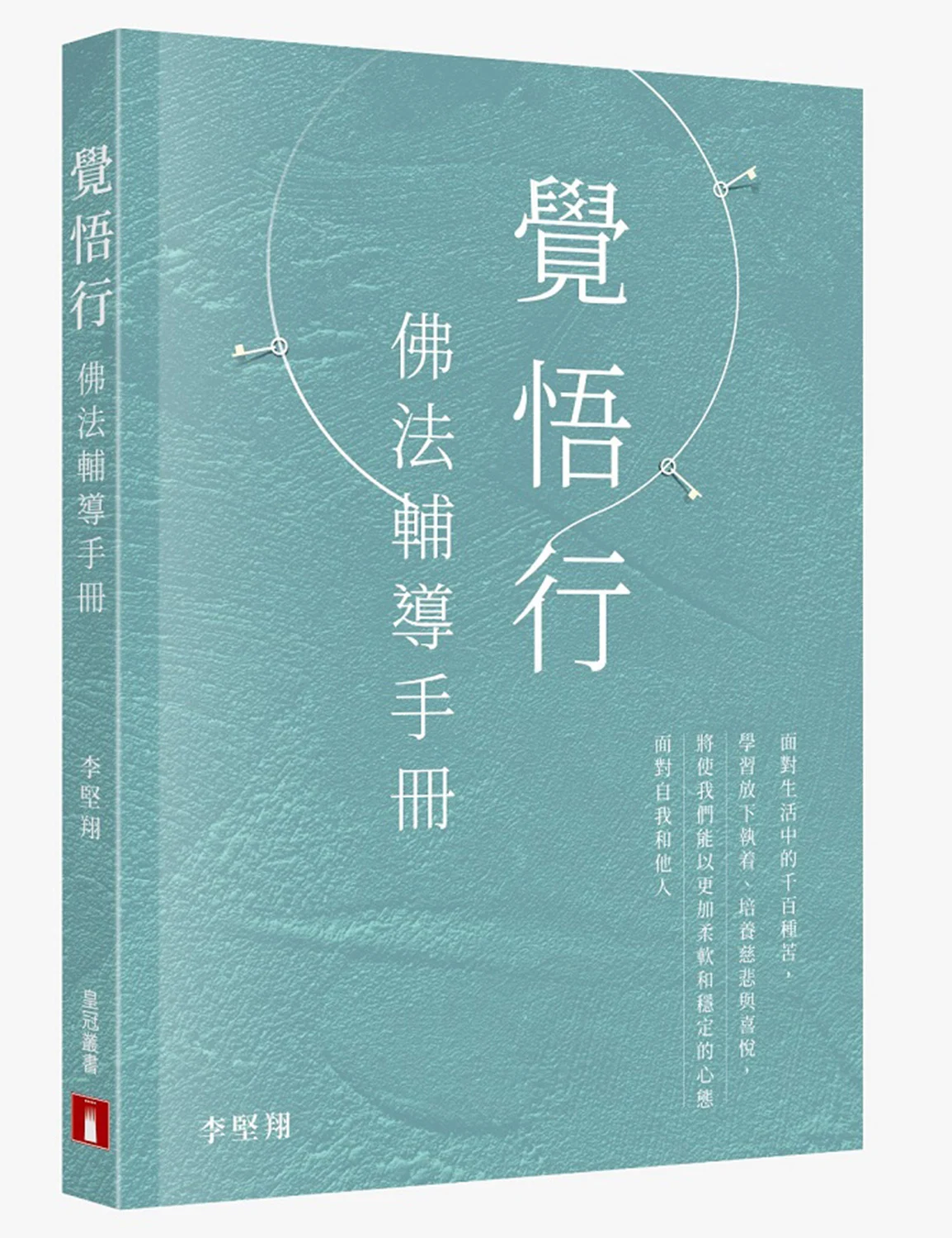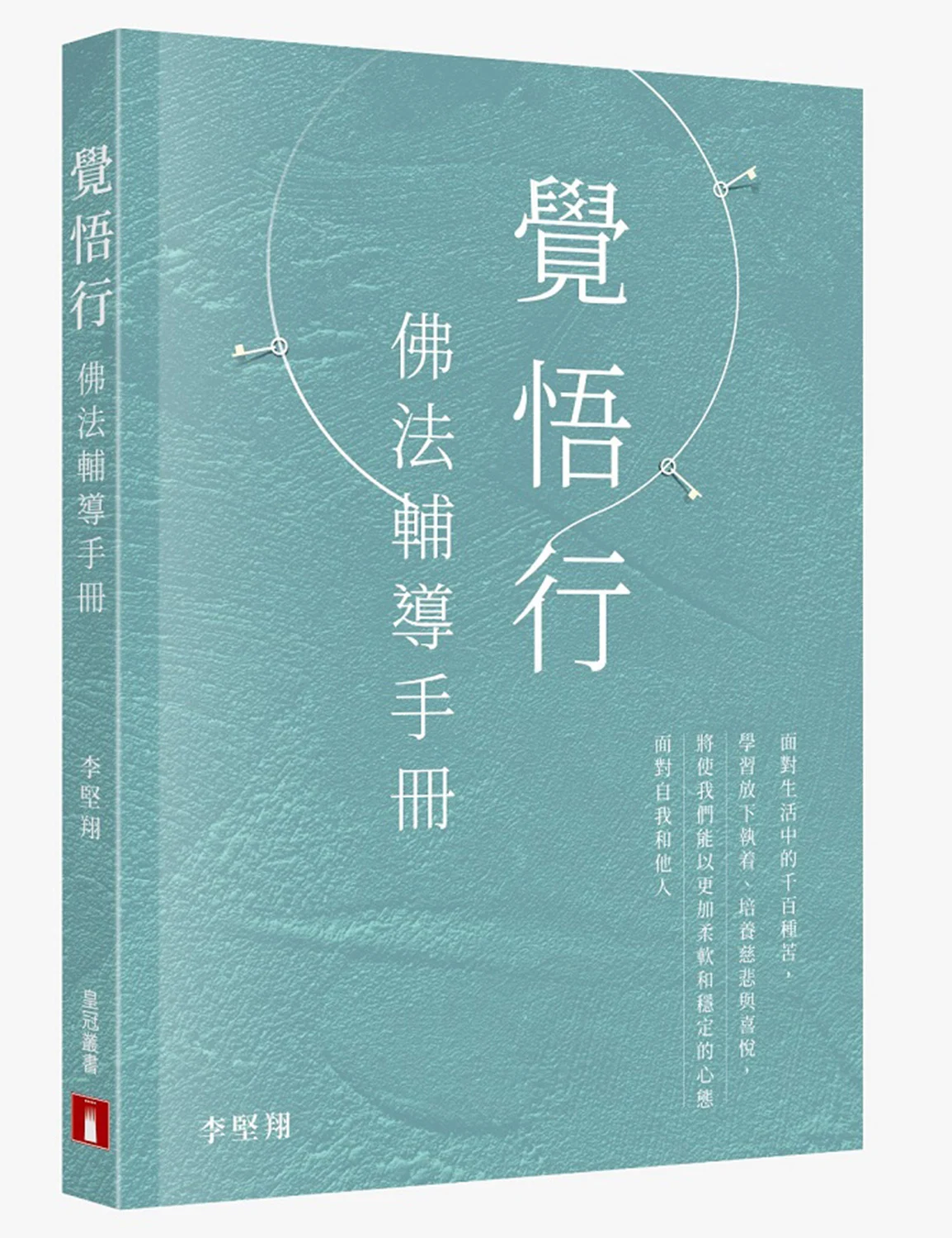內容試閱
再講簡單一點,相信「真實存在的我」和相信婚姻差不多:鑽石恆久遠,一顆永流傳,送一顆鑽石便令人相信愛是永恆,永垂不朽,超生越死,婚姻可以受控,而且非常快樂。理性上,我們都知道人生無常,但感情上,我們卻沉醉於自己營造的概念,說服自己永恆的存在。這正是一般人面對恐懼和孤獨的方法,也是餵養「我執」的日常。
以下是「我」如何形成的一個臨床例子:
34歲的Jolie成長於一個上層社會家庭,父親是一位商人,母親則是家庭主婦。在她的童年時期,父母的關係開始惡化,她目睹了他們之間的激烈爭吵和偶爾的肢體衝突。在她大約七歲時,母親突然帶她去一個地方,撞見父親正與他人出軌。
母親指着父親說:「看看你爸爸,這就是他傷害我們的方式。我要你永遠記住這一點。」
儘管事件後父母並未離婚,但父親逐漸與她的生活疏離,而母親則成為主要照顧者。然而,母親對Jolie常常過於苛刻和批評,因小錯誤而懲罰她。例如,當Jolie無法正確演奏鋼琴曲時,母親會打她,並強迫她在十分鐘內從學校回家。母親甚至會把Jolie鎖在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裏完成作業,並限制她穿着女性化的衣服。儘管父親情緒不穩定,常對她大喊大叫並責怪她,Jolie卻對父親產生了更強烈的情感聯繫。然而,父親的持續不忠讓她感到深深的失望。
她反思道:「看我媽媽這樣子,我能理解我父親為甚麼會出軌。但我見過他的情婦,她是一位體面和善良的女士。因此我不明白為甚麼父親還要找新的情婦。這讓我覺得他不僅背叛了我母親和他的情婦,也一次又一次地背叛了我。」
後來,Jolie出國留學,主修心理學。她努力工作以建立堅實的專業背景,在工作上努力展現出自己能力優秀和負責任的形象,同時在婚姻和家庭治療這一領域獲得了多項資格認證。然而,她經常批評同事:「今天我們的外出活動延遲了,就是因為你遲到影響大家。」或者「你有甚麼理據說你擅長寫論文?真可笑。」在她的專業和個人生活中,Jolie傾向於隱藏自己的錯誤,有時甚至會撒謊以保護自我形象。生活上,她遭受着嚴重的焦慮、過度擔憂和長期失眠的困擾。
第一層虛構的我執:Jolie在一個動盪的家庭環境中成長,父母之間的衝突和父親的出軌,使她形成一個複雜的自我概念,使她感到自己是不被需要的、脆弱的、可以被傷害的,甚至是有問題的(以解釋母親為何虐待她和父親為何離開她)。她特別恐懼被遺棄和背叛的感覺,強烈傾向自我批評,並抱持「我不夠好」的信念。
第二層虛構的我執:假設Jolie執着於「我」是不被需要的、有問題的這一自我概念,她內心的不適感加上對父母之間怨恨的感知,使她對自己充滿了憎恨與厭惡。為了和這種嗔心(dosa)角力,Jolie追求心理學的職業,努力展現自己是能幹和負責任的人,這可能也表明她渴望得到認可和接納,認為只要自己足夠優秀,就能抵擋內心的不安感和對被遺棄的恐懼。
她傾向於說謊或隱瞞錯誤以保護自我形象,並習慣性地批評他人,這可能是對她過去批評的內化所形成的一種防禦方式。同時,她通過貶低他人來提升自己,試圖說服自己相信「我」是優越的。然而,這種虛構的優越感既昂貴又脆弱,因為這種「我」很容易因拒絕和失敗而動搖,令她始終感到被看破的恐懼和被遺棄的焦慮。
認知過程:當Jolie察覺到任何拒絕、挑戰或失敗的跡象時,她會引發被遺棄和身心危險的強烈恐懼。這些情緒使她的內心充滿疑慮與批評,她習慣性地認同這些想法並相信它們是真實的,因為這些想法對她來說是熟悉的,與她的過去經歷產生共鳴。因此,嗔心佔據主導地位,迅速進入防禦模式,她選擇說謊、隱藏或攻擊,以保護她那第一層虛構的自我觀念。
空:實際上,只要Jolie放下這些認知過程,甚麼都不存在。
很多令人痛苦的人,也有着痛苦的故事。了解一個人背後的動機、因緣,可以幫助我們增加同理心,甚至慈悲心。
面對因「我執」而生的苦,我們可以怎麼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