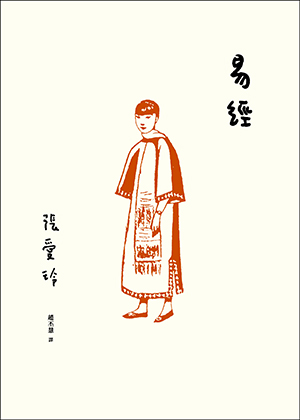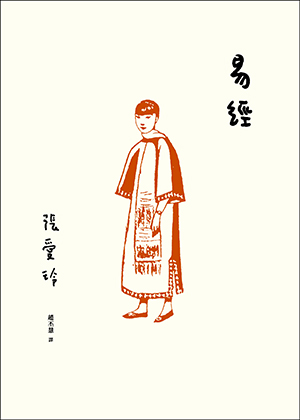內容試閱
一
琵琶沒見過千葉菜。她母親是在法國喜歡上的,回國之後偶爾在西摩路市場買個一次,上海就只這個市場有得賣。她會自己下廚,再把它放在面前。美麗的女人坐看著最喜歡的仙人掌屬植物,一瓣一瓣摘下來,往嘴裏送,略吮一下,再放到盤邊上。
「千葉菜得這麼吃。」她跟琵琶說,唸成「啊提修」。她自管自吃著,正色若有所思,大眼睛低垂著,臉頰上的凹陷更顯眼,抿著嘴,一口口嚙著。有巴黎的味道,可是她回不去了。
琵琶別開了臉。太有興趣怕人覺得她想嘗嘗。姑姑半笑不笑的說:「那玩意有什麼好?」她在歐洲也吃過千葉菜。
「嗐,就是好。」露只簡單一句,意在言外。
三個人組成了異樣的一家子。楊小姐、沈小姐、小沈小姐,來來去去的老媽子一來就告訴要這麼稱呼。她們都是伺候洋人的老媽子,聰明伶俐,在工廠做過工或是在舞廳陪過舞,見過世面,見怪不怪了。就算犯糊塗,也是擱在心裏。楊小姐漂亮,沈小姐戴眼鏡、身材好。不,她們倆不是親戚,兩人笑道,透著點神秘。小沈小姐比兩人都高,拙手拙腳的,跟老媽子一樣像是新來的。後來才從開電梯的那打聽到是楊小姐的女兒。楊小姐離婚了。沈小姐在洋行做事,不常在家。三人裏楊小姐最難伺候,所以老媽子都待不久。露和珊瑚寧可凡事自己來,而不依賴親戚們薦的老媽子。東方人不尊重別人的私生活,兩人的親戚也都愛管閒事。露和琵琶的父親離婚之後,照樣與小姑同住,姑嫂二人總像在比誰反抗家裏多些。
「她們倆是情人。」露的弟弟國柱笑道:「所以珊瑚小姐才老不嫁。」
遠在巴黎的時候,露就堅持要琵琶的父親履行寫在離婚協議書上的承諾,送琵琶到英國念書,反倒引發了危機。琵琶不得不逃家去投奔母親。
「看著吧,琵琶也不會嫁人。」國柱道:「也不知是怎麼回事,誰只要跟咱們的楊小姐沾上了邊,誰就不想嫁人。」
聽人家講她們倆租這一層樓面所付的房租足夠租下一整棟屋子,可是家事卻自己動手做。為什麼?還不是怕傭人嘴敞。
琵琶倒不懂她們怎能在租界中心住得起更大更好的公寓,而且還距離日軍佔領區最遠。她倒是知道母親回國完全是因為負不起國外的生活,而她就這麼跑來依附母親,更是讓她捉襟見肘。補課的費用貴得嚇人。而姑姑自從和大爺打官司輸了,不得不找差事,也變得更拮据。但是看母親裝潢房子仍舊是那麼的刺激。每次珊瑚在辦公室裏絆住了,不能趕早回來幫忙裝潢,露就生氣。
「我一個人做牛做馬。」她向幫不上忙的琵琶埋怨。「是啊,都丟給我。她的差事就那麼要緊。巴結得那樣,也不過就賺個五十塊一個月,還不到她欠的千分之一呢。」
她在房裏來來回回踱方步,地上到處是布料、電線、彫花木板、玻璃片、她的埃及壁燈、油漆桶、還有那張小地毯,是她訂做的,仿的畢卡索的抽象畫。
「知道你姑姑為什麼欠我錢麼?她可沒借,」她把聲音低了低,「愛拿就拿了。我的錢交給她管,還不是為了幣值波動。就那麼一句話也不說,自個拿了。我全部的積蓄。哼,她這是要我的命!」
琵琶一臉驚駭,卻馬上整了整面容,心裏先暫停判斷。她喜歡姑姑。
「我有個朋友氣壞了。他說:『根本就是偷,就為這,能讓她坐牢。』」露瞇著眼,用英語模仿友人激憤的說話,天鵝般的長頸向前彎,不知怎地竟像條蛇。
「她為什麼會那樣呢?」琵琶問道。
「還不是為了你明哥哥啊。打算替他爸爸籌錢,這個洞卻越填越深。沒錯,愛上一個人就會千方百計想幫他,可也不能拿別人的錢去幫啊!」
姑姑與明哥哥的事雖然匪夷所思,琵琶還是馬上就信了。她想起姑姑講電話,聲音壓得既低又沙啞,幾乎像耳語,但是偶爾仍掩不住惱怒,原來就是與明哥哥講電話。原來這就是熱情的苦果。她還當他們是男女間柏拉圖式戀情最完美的典範呢。那晚陪他們坐在幽暗的洋台上她就是這麼說的。一句話說完,鴉雀無聲,當時她還納罕,所以直到現在仍記得。那年她十三歲。始終不想到姑姑可能會愛上一個算得上是姪子輩的人。再者,他們也不是會戀愛的那種人。即便是現在,她也沒想到去臆測在洋台的那晚他們是不是已經是情人了。她喜歡的人四周都是空白的一片,就像國畫裏的留白,她總把這種人際關係上的空白當作是再正常不過。
她母親在說:「我也不知道反覆跟她說過多少次,只要不越界,只管去戀愛,可是一旦發生了肉體關係,那就全完了。否則的話,就算最後傷心收場,將來有一天兩人再見,即使是事隔多年,也是回味無窮。可是要真有什麼,那就不一樣了。她偏不聽,現在落得個人財兩空,名聲也沒了,還虧得我幫她守口如瓶──何苦來,有時候想想真冤。我這是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我連你舅舅都沒說。他要知道了,他跟你舅母一定會對她不高興,到時候就鬧得滿城都知道了。我也從沒跟你表舅媽說,可是她一定早知道了。她討厭你姑姑,因為她把明哥哥當自己兒子一樣。她把這事都怪罪到你姑姑頭上──也難怪,誰叫你姑姑比你明哥哥大呢。要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你表舅媽根本就不願意跟她有牽扯。她每次可都是為了來看我才上咱們這個門的。」
「那何必還住一塊?」琵琶試探著嘟囔。
「當然是為了省錢。有個體面的住址好讓她在洋行裏抬得起頭來,好讓他們覺得請到了有身份地位的人。」
琵琶聽得一頭霧水。一個月就五十塊錢,還想請個名媛速記員?
「還有一個原因,我們兩個彼此支持了這麼多年,要是鬧翻了,還會讓親戚看笑話。」
「那姑姑會還錢麼?」
「她說幾棟房子賣了一定還,可現在房子全給凍結了。照上海現在的情勢,誰知道哪天才賣得掉。剛回來的時候還以為不用多久就可以回去了,誰知道會困在這裏。現在又添了你。你知道你父親怎麼說的嗎?『她那是自搬磚頭自壓腳。』就會說風涼話。我一意堅持要你繼續念書,因為你別的什麼也不行。每個朋友都勸我不要。有個還跟我說,」說到這,她改用英語複述,也是瞇著眼,拱著頸項,「『留著你的錢!你不要傻!』」
琵琶本身也對於花她母親的錢到英國念書一事心中不安,可是從別人口中聽到是在浪費母親的錢,那種感受又兩樣。
「別人不了解我為什麼執意要送你到英國不可。我可以讓你在這裏找事做,可是你不是上班的那塊料。有人說索性嫁掉她算了。我是可以──」
你可以?琵琶忿忿的想著。你不是一直教導我為自己著想,當個新女性嗎?
「可是我不喜歡相親。」露接著道:「相親的人心態不正常,你懂我的意思麼?那跟一般的情況下遇見別人不一樣,一般的情況可以看出他們真正的樣子來。」
這跟我有什麼關係?琵琶心裏想。那種吃晚餐、看電影半新不舊的相親模式也許對別人管用,對我可不中用。
「還有人說:萬一她還沒畢業就戀愛了呢?不錯,你很可能在英國遇見什麼人。年青的女孩子遇見的第一個男人總是,哎,好得不得了。」她極嫌惡的道。
「我才不會。」琵琶笑道。
露別開了臉。「嘴巴上說是不管用的。」
「我不會,我就是知道。」琵琶笑道:「再說,我覺得很不安,花那麼多的錢,我得全部賺回來。」
「錢倒沒什麼,我向來也沒把錢看得多重,雖然說我現在給錢害苦了。不像你姑姑,就連年青的時候──你絕對想不到,她會那麼渾渾噩噩、莽莽撞撞的,好像一點也不懂事。當初分家,她已經分到她那一份了,末後又多出了一包金葉子,說是留給女兒當嫁妝的。從前那時候女兒只有嫁妝,不能繼承家產。當然是不能拿雙份。有個長輩說既然這是做母親的特為留下來給女兒的,就該給女兒。又有人說她都分到家產了,金葉子就該分她親哥哥一半,她那個同父異母大哥就免了。你父親臉皮薄,說:『都給了她吧。』我當然無話可說。而你姑姑居然連句話也沒有,就拿了。她就是這樣的人。還不止這件事呢。有時候她在小事上出風頭,像是什麼花樣啦、設計啦、或是送什麼禮最得體的,大家都誇珊瑚小姐真聰明,其實根本就是我出的主意,她竟然也當之無愧似的,一句話也沒有。哎唷!你們沈家啊,真是大名鼎鼎啊──喝,沈家啊!每次我說不,你外婆就把不字丟我臉上。等嫁進沈家,沈家還有什麼?你父親的內衣領子都破了,床單髒兮兮的,枕頭套都有唾沫臭。你大媽當家,連洗衣服的肥皂都缺,而且床單差不多沒換過。那時你老阿媽照顧你,一句話也不敢說──嚇都嚇死了。我得自己拿出錢來買肥皂、買布做內衣。你姑姑那時候十五歲,很喜歡我,一天到晚跑來找我。你父親恨死了。就連我,我倒不是跟他一鼻孔出氣,可連我有時也覺得她煩。這對兄妹真是奇怪。都要怪你奶奶。自己足不出戶,兩個孩子也拘在家裏,只知道讓他們念書。念了一肚子書有什麼用處?到今天你父親只記得從前怎麼怎麼,跟個瘋子一樣,抽大,打嗎啡,你姑姑倒做了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