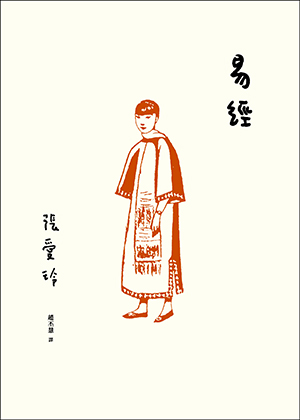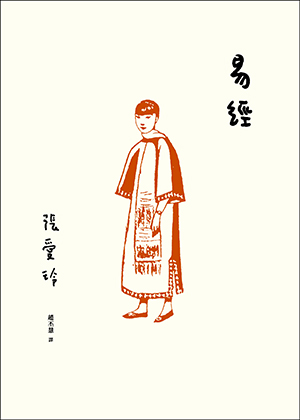內容試閱
這些年來壓抑住的嫌惡,以及為了做個賢妻與如母的長嫂所受的委屈,都在這時炸了,化為對瑣屑小事的怨恨。美德竟是如此的代價,琵琶也有點寒凜凜的。露仍踱來踱去,痛哭失聲,弄皺了臉皮,輕笑道:
「哎唷!做這種缺德事晚上怎麼還睡得安穩!要依我啊,良心上壓了這麼塊大石頭,就連死都不閉眼。」
琵琶仍然一言不發,沒辦法同情母親,因為她也同姑姑一樣被控有罪。她母親倒不見怪,認為是家族忠誠才讓女兒不願說長輩的不是。
「幫我拿著。」露把一片玻璃豎起來潤飾。
牢騷發完了。
半個鐘頭之後,珊瑚回家來,兩人一面閒聊一面做晚飯,空氣就同平常一樣。琵琶倒時時警惕,不肯對姑姑的態度上有什麼改常,以免讓姑姑察覺她知道了。做起來並不難,因為她對姑姑的感覺其實還是一樣。至於明哥哥呢,琵琶沒辦法將他看成是姑姑的情人,便也沒辦法將他看成是薄倖郎。他還是那個文靜矮小的大學生,每次與他同處一室,一站起來總會使他難堪,因為琵琶已經高他一個頭了。
可是這一向她極少和姑姑講話。姑姪兩人在露面前本就話少,琵琶更不好意思在母親不在附近的時候開口,彷彿是怕懼她。露回國之前姑姪兩人倒是談得挺多的。是姑姑帶著她一步步走入往事,儘管兩人都興趣缺缺。她是個孩子,對大人的事當然不會有多大的興趣。珊瑚也總是笑道:
「問我根本就問錯人了。我哪能記得別人的事?我從來都是聽過就忘了。」表示她不愛蜚短流長。少女時期她既不美又缺人愛慕,回顧過去因而少了戀戀不捨的感情。但就是那種平平淡淡的說法使故事更真實。就彷彿封鎖的四合院就在隔壁,死亡的太陽照黃了無人使用的房間,鬼魂在房間裏說話,白天四處遊蕩,日復一日就這麼過下去。琵琶打小就喜歡過去的事,老派得可笑,也叫人傷感,因為往事已矣,罩上了灰濛濛的安逸,讓人去鑽研。將來有一天會有架飛機飛到她窗邊接走她,她想像著自己跨過窗台,走入溫潤卻凋萎的陽光下,變成了一個老婦人,孱弱得手也抬不起來。但過去是安全的,即使它對過去的人很殘忍。
「哼!從前那個時候!」珊瑚經常這麼忿忿不平的說。不消說,過去的一切都是禁忌。
琵琶對於親戚關係也是懵懂得很。直到最近才知道她跟表舅媽與明哥哥是怎麼個親戚。表舅爺爺是外婆的姪子。明哥哥不是表舅媽的兒子,但是他卻管她叫媽。
「明哥哥的媽媽是誰呢?」有一天在珊瑚家遇見他,琵琶這才想到要問一聲。
「是個婢女,給燕姨太使喚的婢女。」珊瑚每句話說到末了就會不耐煩的偏過頭去,好似說得已經夠多了。一講起明來,她的聲音就變得低沉沙啞,真有些像哭過後的嗓音。「燕姨太發現了之後,痛打了她一頓。孩子一落地,她就把孩子奪走,把做媽的賣了。」
「表舅爺難道什麼也沒說?」
「他怕死她了。她可是他的心肝寶貝呢。」
「那明哥哥知道他母親現在在哪裏麼?」
「他怎麼可能知道?他還以為燕姨太是他親生母親呢。後來你表舅爺不要她了,明哥哥還哭著哀求他。表舅爺這才跟他說:『別傻了,她不是你媽。』終於告訴了他真相。以後明哥哥就恨死她了。每次她來,表舅媽還留她住,明哥哥氣得要死。」
「從哪兒來啊?」
「北平。表舅爺不肯讓她在上海住,要她搬到北邊去,否則就不給她月費。可是她老往上海跑,想來看他。他怎麼都不見。」
琵琶很能體會表舅爺不是輕易能見到的人。她自己就不曾見過他。
「可是你表舅媽是只要她來從不給她吃閉門羹。表舅媽說是過意不去。可也不犯著那麼客氣──留她住,房子那麼小,還一塊吃喝閒聊。現在燕姨太當然是百般巴結了,開口閉口都是『太太!太太!』從前啊,她哪裏把這個太太看在眼裏過。明哥哥可不理她。她倒纏著不放,少爺這個少爺那個的。表舅媽還責備他:再怎麼說,她小時候照顧過你。好像表舅媽不知道那女人是怎麼對付明哥哥的親生母親的。她就是這樣。雖然她把明哥哥當自己的兒子一樣,明哥哥實在沒辦法喜歡她。」
「燕姨太還是那麼美麼?」
「現在頭都禿了,戴著假頭髮殼子,捲得跟扇貝一樣。她才剛開始掉頭髮,表舅爺就躲著她了。」
「我怎麼從來沒在表舅媽家見過她?」
「應該見過。穿著黑旗袍,還是漂漂亮亮的。表舅爺出了事之後,她來過。」
出了事的意思是出了意外。琵琶沒在家聽說過,而珊瑚也只是說:
「他挪用公款坐牢了。」
琵琶聽人說過表舅是在船運局。有一兩次她聽見父親與姑姑提起他,語氣總是神神秘秘的,不敢張揚,半是畏懼半是不屑:
「最近見過雪漁嗎?」
「沒有,好久不見了。你呢?」
「也沒見過。唉,人家現在可發了。」榆溪竊笑道。「發了」是左右逢源的委婉說法,言下之意是與某個軍閥勾結。
「我聽說他在募什麼基金。手頭上多半還是緊。」
「國民黨政府的錢不夠他揮霍。」榆溪哈哈大笑道。
「哼,那個人啊!」珊瑚扮了個怪相。兄妹兩人露齒呼出顫巍巍的呼吸。
琵琶完全聽不出這番話的弦外之音。她並不知道羅氏一門不准入仕民國政府。羅家與親戚都靜坐家中,愛惜自家的名聲。大清朝瓦解了,大清朝就是國家。羅家男人過著退隱的生活,鎮日醇酒美人,不離舖,只要不忘亡國之痛,這一切就入情入理。自詡為愛國志士,其實在每一方面都趨於下流,可是不要緊。哀莫大於心死。琵琶一直都不明白她父親遊手好閒倒還有這麼一個冠冕堂皇的藉口。
她父親的一些親戚就耐不住寂寞。在北方沈六爺入了一名軍閥的內閣。沈八爺也起而效之。不過同樣的旗號只能打一次。北洋政府垮台之後,他們逃進了天津的外國租界,財是有了,政治名節卻毀了。南方的羅侯爺加入了南京政府。革命後二十年,他的名號依然響亮。當然這一場革命委實是多禮得很,小心翼翼保住滿洲人的皇宮。退位的皇上仍舊在他的小朝廷裏當他的皇上,吃的是民國供給的年金。報紙上提到前朝用的說法是遜清。如此的寬厚與混亂在南京政府成立後劃下了休止符。孫逸仙的革命有了真正的傳人。這一次真的兩樣了。然而南京政府一經底定,仍是戀戀於過去,捨不得斬斷與過去的聯繫。羅侯爺得了官位。報紙上刊登了他的照片。他的大名雪漁就如一幅畫。一篇長文報導了壟斷海岸船運的歷史,原是第一任侯爺的得意之作,報上還盛讚創始人的孫子獨具慧眼,克紹箕裘,接任海運局長。
而在虧空一案報上又提到了羅侯爺的祖父,這一次更是大篇幅報導,許多報紙還是頭條,讓羅氏一門極為不悅。
「老太爺又被拖下水了。」珊瑚道。
表舅媽同丈夫分居,只靠微薄的月費維生,完全不沾他的光。這時她去找侯爺的有錢伯父,雙膝跪地,叩頭如搗蒜。
「磕頭,明兒,」她向丈夫的兒子說:「求你曾伯伯救救你父親。給曾伯母磕頭。」
老夫妻拉她起來,溫言安慰她,暗示他們始終就不贊成入公職。福泰的表舅媽帶著明哥哥挨家挨戶磕遍了所有的親戚。明哥哥愛他的父親,可是他痛恨求情告幫,尤其是根本就不管用。所有人都袖手旁觀。
琵琶對旁人一無所知,也不覺得奇怪姑姑會一肩起搭救表舅爺的責任來。日子一天天過去,這件事卻越拖越久,她在報上看到虧空的款子是天文數字,後頭的零多到數不清。珊瑚對於未出口的問題早想好了答案,顯然也同許多的親戚說過:
「再怎麼說他也是奶奶最喜愛的外甥。」她指的是自己的母親。「她說唯有他還明理。我當然也喜歡他,跟他很談得來。」
「是麼?」琵琶驚訝的道。表舅爺根本是個隱形人。
「是啊。」珊瑚草草的說,撇過一邊不提的聲口。
琵琶很少聽到奶奶的事。露前一向喜歡提「你外婆」。有個故事說的是寡婦被圍困,說的就是外婆和幾個姨太太。可是提起奶奶來,露總是一聲不吭,只掛著淡淡的苦笑。琵琶現在知道母親為什麼不喜歡這位從未謀面的婆婆了。她在婚前就聽過太多她的事,婚後才發現上了當。
琵琶知道的祖父母是兩幅很不相襯的畫像,每逢節日就會懸掛在父親屋子的供桌上方。一幅是油畫,畫著一個端坐的男人,另一幅是女子的半身照片。她倒是挺喜歡這兩幅圖像的,很慶幸不是那種傳統的祖先畫像。祖父很福泰的一張臉,滿面紅光,眼睛下斜,端坐椅上,一腳向前,像就要站起來。祖母面容嚴峻,像菩薩,額上戴頭帶,頭帶正中央有顆珍珠。可是琵琶沒有真正想過祖父母,直到有一天她從父親的吸室裏抽了本書,帶到樓下讀。那是一本新歷史小說。
她弟弟進來了。
「祖父在裏頭。」他說,語氣是一貫的滿意自得。每次他有什麼消息告訴她,總是這種聲氣。
「什麼?在哪裏?」
「他的名字改了,我記不得是改成什麼,讀音差不多。」
「祖父叫什麼名字?」她微笑著問。
直呼父母或祖父母的名諱大不敬,可是為人子女仍是不能不知。有時候她好像是故意在吹噓自己的無知。只因為她可以去看珊瑚姑姑,又可以寫信給母親,她就認為自己是兩棲動物,屬於新舊兩個世界,而且屬於新世界要多些。他喃喃說沈玉枋。她年紀比他大。姐弟倆一塊在書裏尋找。
「陵少爺!」他們後母的老媽子在樓下喊。他得到吸室去。
「啊?」他高聲應了一聲,因為不慣大聲,聽上去鼻音很重。惱怒的問號像是在說「又怎麼了!」讓姐姐知道儘管挨打挨罵,他並不是溫順的乖孩子。他輕快的起身,藍褂子太大了,大步出了房間,自信只不過是去跑跑腿。
琵琶快速翻頁,心頭怦怦亂跳。誰是祖父?是引誘了船家女的大官還是與年青戲子同性戀愛的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