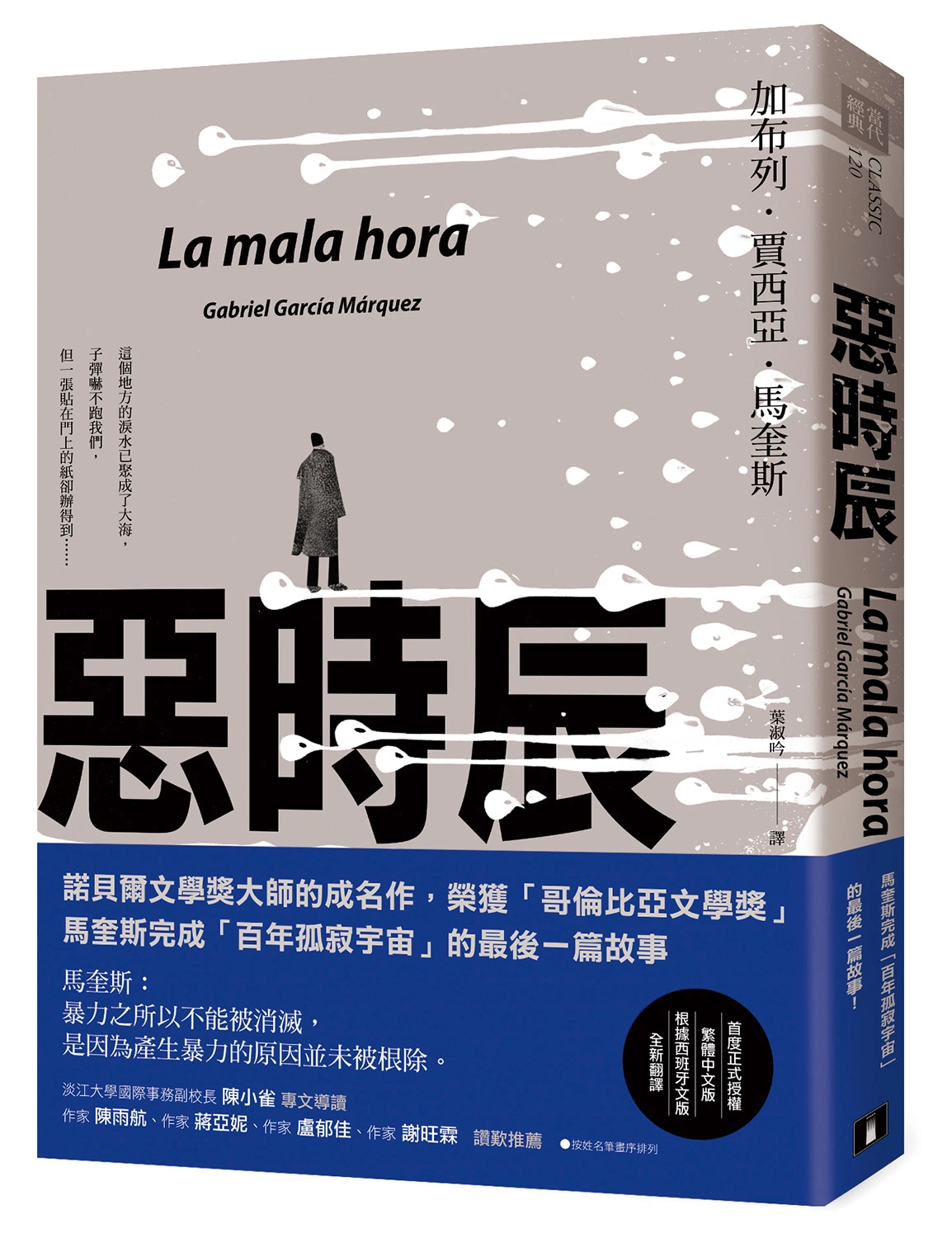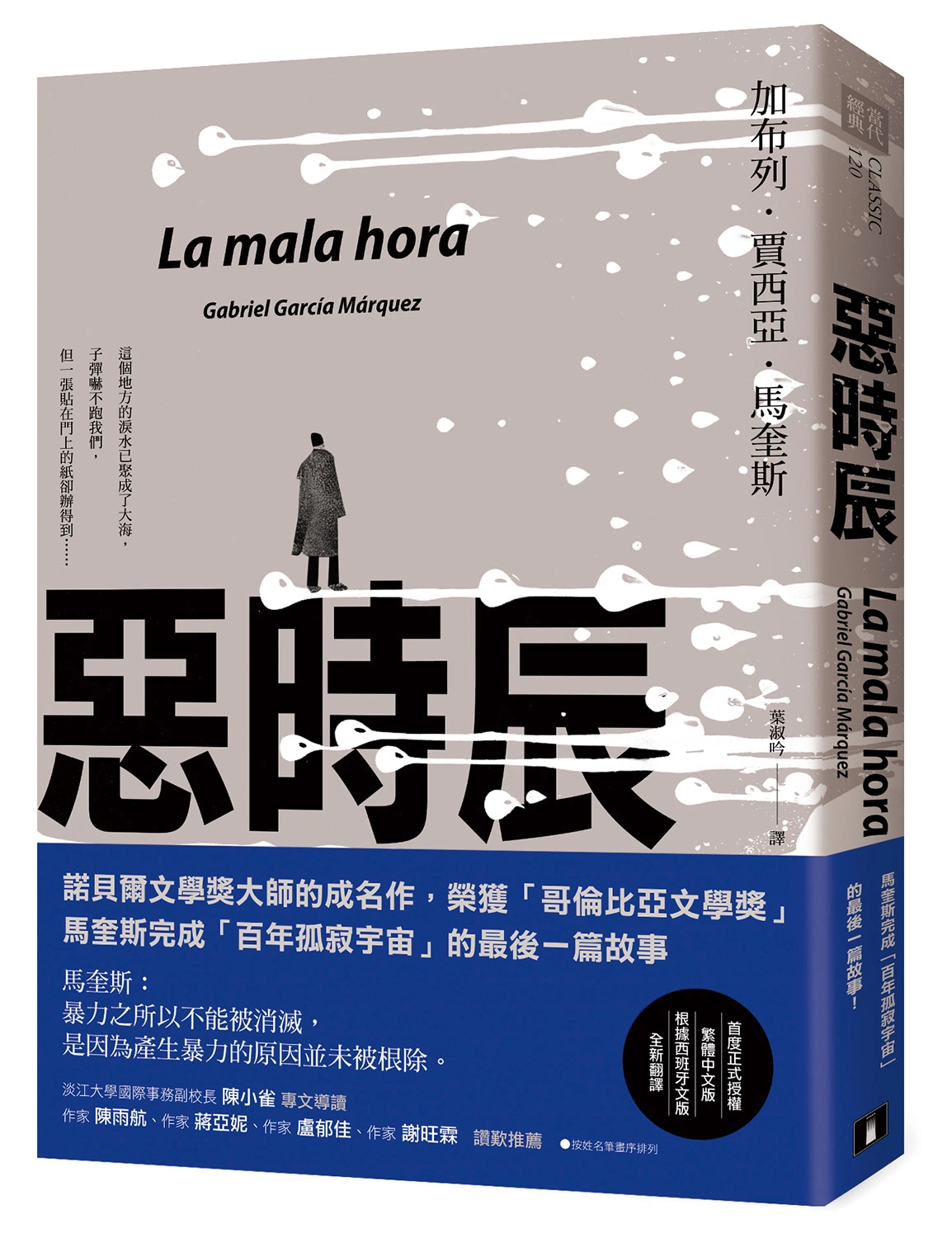內容試閱
安赫神父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起身。他舉起乾癟的手揉揉眼皮,掀開蚊帳,赤條條地坐起來,沉思了半晌,他需要這一點時間,感覺自己還活著,同時他回想月日,並對照聖人曆上的日子。「十月四日,禮拜三。」他心想;接著他喃喃自語:「亞西西的方濟各紀念日。」
他沒有梳洗,也沒有禱告,直接換好衣服。他人高馬大,性子急躁,外表和動作卻如溫吞的牛隻,神情肅穆而悲傷。他心不在焉,扣好教士袍的鈕釦,那動作彷彿正在檢查豎琴的琴弦,接著他拉開門栓,打開面向院子的門。他凝視雨中的晚香玉,想起了一首歌。
「我的眼淚啊,聚成了大海。」他嘆口氣。
從他的臥室,有一條直通教堂的內廊,廊上綴著一盆盆的花,鬆散搭蓋的磚牆上,已經看得到十月的青草從縫隙冒出。上教堂前,安赫神父先去廁所。他憋住氣,撒了一大泡尿,不想聞到總是嗆得他掉淚的阿摩尼亞熏天臭氣。之後他步向走廊,繼續回想歌詞:「那艘船載我航向你的夢。」他走到教堂的窄門前,聞到了晚香玉飄來的最後一縷芬芳。
教堂內氣味難聞。廳堂是長形的,也是鬆散的磚塊牆,只開一扇門,對著下面的廣場。安赫神父直接走到鐘樓下。他看著離頭頂超過一公尺高的鐘錘,想著上緊的發條還能走一個禮拜。他感覺到蚊子的攻擊,用力拍死後頸的一隻蚊子,手往發條繩上擦乾抹淨。接著他聽見上面精密的機械齒輪正在運轉,聲音低沉而微弱,時鐘敲響了五聲,宣告已經清晨五點。
他等到最後一聲結束。這時他雙手抓緊繩索,纏繞在手腕上,一鼓作氣敲響破爛的青銅鐘。他已經滿六十一歲。敲鐘對他的年紀來說太過吃力,但是他一向親自主持彌撒,而使力敲鐘能鼓舞他的士氣。
青銅鐘聲飄揚,蒂妮妲推開臨街大門,接著步向角落,前一晚她在這裡放置了捕鼠器。她看見了一場小小的血腥場面,開心之餘,又覺得噁心。
她打開第一個捕鼠器,用食指和拇指夾起老鼠尾巴,把牠丟進一個厚紙箱。這時安赫神父剛打開面向廣場的門。
「早安,神父。」蒂妮妲說。
神父沒理會她優美的男中音嗓音。在這個十月的黎明時分,放眼只見一片悲悽,廣場上空蕩蕩,扁桃樹在雨中沉睡,整座村莊靜悄悄,給他一種徬徨無依的感覺。適應雨聲之後,他聽見廣場的盡頭傳來帕斯特的豎笛聲,是那麼清晰而有一點不真實。到這一刻,他才回應她。
「帕斯特不是跟彈小夜曲的人在一起。」他說。
「不是。」蒂妮妲肯定地說。她拿著裝老鼠屍體的紙箱走過來。「跟彈吉他的人。」
「他們整整兩個小時都在演奏一首蠢歌。」神父說。「我的眼淚啊,聚成了大海。是這一首吧?」
「那是帕斯特的新歌。」她說。
神父佇立在門前不動,腦海掠過一幅想像。多年來,他每天都聽到兩個街區外的帕斯特吹奏豎笛,每到清晨五點,帕斯特就搬出凳子,靠在鴿舍的柱子旁練習。他是村裡最準時的時鐘:首先,是清晨五點的五聲鐘響,接著是第一聲彌撒開始的鐘聲,然後是帕斯特在他家院子的豎笛聲,一連串輕盈的樂符淨化了夾帶鴿子排泄物臭味的空氣。
「那首歌的旋律不錯。」神父回答。「但是歌詞很愚蠢。歌詞前後對調,意思都差不多。那個夢載我航向你的小船。」
他半轉過身,不禁為自己的發現露出微笑;他走向聖壇準備點燈。蒂妮妲跟在後面。她身穿白長袍,長袖口蓋住手腕,繫著平日聖會用的藍色絲質腰帶。她的兩邊眉毛相接,一雙眼是深邃的黑色。
「他們在附近逗留一整夜。」神父說。
「都是因為瑪格特.拉米瑞茲在。」蒂妮妲心不在焉地說,她搖了搖箱子,裡面發出老鼠屍體的碰撞聲。「可是昨晚發生了比小夜曲更精采的事。」
神父停下動作,那雙寧靜的藍眸盯著她看。
「什麼事?」
「黑函。」蒂妮妲說。然後她發出緊張的輕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