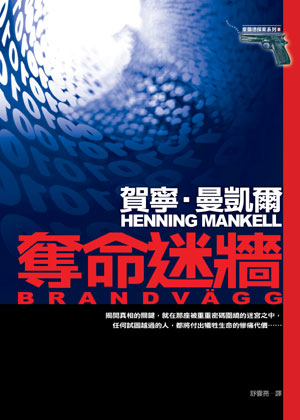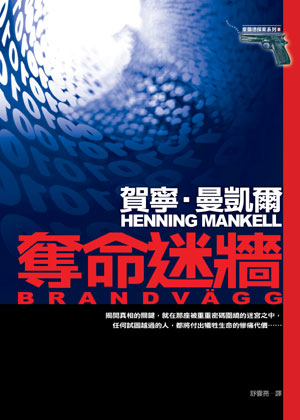內容試閱
2
一九九七年十月六日清晨,當庫特‧韋蘭德坐進停在禹斯塔市瑪利亞街上的車裡時,其實有點不太情願。這時剛過八點鐘。他駕車出城,心裡還在想自己到底為什麼會答應要去。他打從心底不喜歡參加葬禮,但現在卻正在前往葬禮的路上。因為時間還早,他決定不直接去馬爾默,而是走濱海公路先去斯瓦特和特雷勒堡。他往左邊的海面看了一眼,一艘渡輪正駛近港灣。他回想起這是自己在七年內所參加的第四次葬禮。第一次是經過長期的痛苦和折磨後,死於癌症的同事雷柏格。當時韋蘭德常去醫院探望他,而他則躺在病床上緩慢地步向死亡。雷柏格之死對韋蘭德來說是個巨大的打擊,因為正是雷柏格把他塑造成一個真正的警察。他教韋蘭德如何訊問,而且透過觀察他如何工作,韋蘭德也慢慢學到如何去分析犯罪現場中隱藏的線索。在與雷柏格一起工作之前,他只是個普通的警察;但在雷柏格死去多年以後,韋蘭德才發現,自己已經變成一個不只頑固、精力過人而且優秀的警探。每當他在進行一件不知如何著手調查的案子時,他仍會在腦中與雷柏格進行沉默的長談。
在沒有雷柏格的日子裡,他幾乎每天都還是
一開始,他甚至不知道她是誰。
然後他才想起她是斯特凡‧弗雷德曼的母親。幾秒鐘之後,三年前那件事的記憶和片段印象紛紛湧了上來。在那樁案子裡,那個男孩全身塗滿美洲印第安勇士的油彩,然後向逼瘋他姐姐和嚇壞他弟弟的人復仇。受害人之一是斯特凡自己的父親。想到最後那紛亂的場面,看到那男孩跪在姐姐的屍體旁哭泣時,韋蘭德不禁畏縮了一下。他只知道那男孩後來沒被送進監獄,而是一座看管嚴密的精神療養院,之後的事,他就一無所知了。(註1)
現在安妮特‧弗雷德曼來電說那男孩死了,是跳樓自殺。韋蘭德向她表達了誠摯的哀悼之意。他的感覺不是悲傷,也許是無助與絕望,但是他仍不明白她為什麼要打電話給他。他站在那兒,手上握著話筒,努力地回想她的面容。當年在他為了這名十四歲的男孩是否犯下這些駭人罪行而掙扎之時,曾經在她馬爾默市郊的家中見過她兩三次。她怕生緊張,總是畏畏縮縮,似乎擔心事情就要變糟。但在她的經驗中,事情往往真的就會變糟。韋蘭德記得自己還曾經懷疑她有酗酒或沉迷藥物的問題,不過他也不知道真相。他幾乎已經記不起她的臉孔,電話裡的聲音聽起來也變得全然陌生。
然後她說了自己打電話來的原因,她希望韋蘭德能參加葬禮。除了她自己和小兒子揚斯之外,沒有什麼人會來。畢竟他是曾經祝福他們平安的好人。
他答應會去參加。雖然話一出口就改變了心意,不過已經來不及了。
後來,他試著查出那男孩被關進精神病院後又發生了什麼事。在與斯特凡的其中一位醫生談過後,他得知,過去幾年裡,斯特凡幾乎完全陷入沉默,將自己與外界隔離。那男孩最後全身塗滿印地安勇士油彩,從樓上縱身躍下,落在醫院的水泥地面上。雖然從那紛亂的油彩和鮮血,很難看出深鎖其中的少年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不過卻相當程度地說明了形塑他性格的那個充斥暴力與冷漠的社會。
韋蘭德沿著道路緩緩行駛。今早,當他發覺褲子又變得合身時頗為驚訝,他的體重一定又減輕了。自從去年查出患有糖尿病,他就強迫自己改變飲食習慣,開始運動並減肥。但剛開始他太急了,每天都要站上浴室的體重計秤好幾次,最後他在狂怒中把體重計給扔了出去。
他的醫生仍然喋喋不休,堅持韋蘭德應該改變不健康的飲食習慣和完全不運動的狀態。醫生的嘮叨終究還是產生了效果,韋蘭德買了一套運動衣和一雙慢跑鞋,展開固定的健行。但是當同事馬丁森提議和他一起跑步時,韋蘭德拒絕了。因為他規劃了固定的健行路線,每次約一小時,從瑪利亞街開始,穿過桑德斯公園後再折返。他強迫自己每星期至少健行四次,還強迫自己避開最喜歡的幾家漢堡店。
就這樣,他的血糖指數降了下來,體重也減輕了。某天清晨,當他在鏡子前刮鬍子時,注意到雙頰又凹陷了。就好像脫去一層脂肪和不健康的皮膚後,又找回了自己原先的面孔。女兒琳達上次見到他時,也為這樣的改變而覺得高興,但在局裡,沒有人對他外表的變化做出任何評論。這似乎意味著我們對彼此視而不見,韋蘭德想道,我們一起工作,卻對彼此視而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