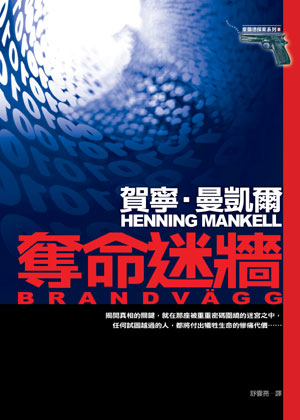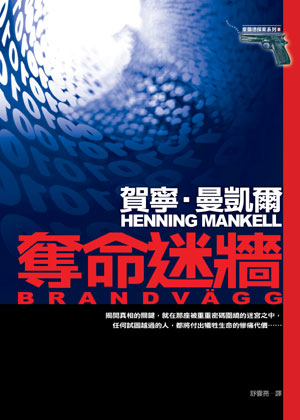內容試閱
在某個念頭驅使下,他踩下煞車,掉頭迴轉,他的時間還很充裕。他停好車走下來,外面沒有風,氣溫只比冰點高個幾度。他扣上外套的釦子,沿著沙丘間蜿蜒的小路走向海灘。海灘上雖然空盪盪的,但上頭有著人、狗和馬留下的痕跡。他望向海面,一群飛鳥正排成某種隊形飛往南方。
他還記得是在哪裡發現屍體的。那次艱難的調查過程把他引向了拉脫維亞,他在里加遇見了柏芭,她是個韋蘭德認識而且喜歡的拉脫維亞警官的遺孀。
然後他們開始見面。有很長一段時間,他以為這件事會有結果,柏芭會願意移居瑞典,他們甚至開始找起房子。但是,她忽然消失了,韋蘭德妒忌地認為她一定是遇上了別的男人,於是他甚至不事先通知就突然飛到里加,想給她個驚喜。但那裡沒有其他人,有的只是柏芭的疑慮,疑慮著是否要嫁給另一個警察,並放棄家鄉這收入不高但受人尊敬的翻譯工作。
事情就這樣結束了。
韋蘭德沿著海灘走著,發現從最後一次與柏芭談話以來已經過了一年。有時她仍會出現在夢中,但他從來沒能留住她。每當他走近或伸手觸摸她時,她就消失了。他自問,是否真的還想念她。現在他的妒意已經消失,想到她與別的男人在一起也不再覺得難過了。
我思念她的陪伴,他想著,我和柏芭在一起,只是為了逃避連自己都沒察覺的孤獨。
他回到車旁,又想著:我應該避開秋天寂寥的海灘,它們只會讓我覺得失落。
有一次,他從現實生活中逃開,躲到北方吉爾蘭的一個偏僻角落。當時他因為心情極度抑鬱而請了病假,並認為自己再也不會回禹斯塔當警察。那已經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但那種可怕的感覺仍然歷歷在目。這是他永遠不想再經歷一次的事,那種淒涼而波濤洶湧的景色似乎喚醒了他最深的恐懼。
他坐進車裡,繼續駛向馬爾默。他不知正要來臨的冬天會是什麼樣子,會下很多雪或是下雨下個不停?也不知道十一月要休的一週假期裡自己要做些什麼?他曾經跟琳達提過這次度假由他出錢,和她一起搭飛機去個溫暖的地方。可是她還在斯德哥爾摩上某種他不了解的課程,說她真的走不開。於是他努力思索是否能找到其他旅伴,卻想不到任何一個。他幾乎沒有朋友。斯騰‧維登也許會跟他一起去,他在禹斯塔郊外的農莊裡養馬,但韋蘭德不知道他是不是個好旅伴?維登經常喝酒,而韋蘭德正在努力戒酒。他也可以邀請父親的遺孀葛茹,但整整一個星期,他們要說些什麼?
沒有其他人。
他將在家裡度過假期,用那筆錢買輛新車。這輛開了很久的標緻,已經開始發出怪聲了。
剛過十點鐘,他駛進馬爾默的玫瑰園區外圍。葬禮定在十一點鐘舉行,那座教堂是棟現代化建築,附近有幾個男孩正對著水泥牆踢足球。一共有七個男孩,其中三個是黑人,另外三個看起來像是外國移民,最後一個有著一頭蓬亂的金髮,臉上滿是雀班。這些孩子正興高采烈地踢著球,笑聲此起彼落。有那麼一剎那,韋蘭德很想加入他們,但是他停在原地不動。有個男人從教堂裡走出來,點了支菸。韋蘭德從車裡鑽出來向他走去。
『斯特凡‧弗雷德曼的葬禮是在這裡舉行嗎?』他問道。
那人點點頭,『你是他親戚嗎?』
『不是。』
『我想不會有什麼人來參加葬禮,』那男人說,『你應該知道他做了什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