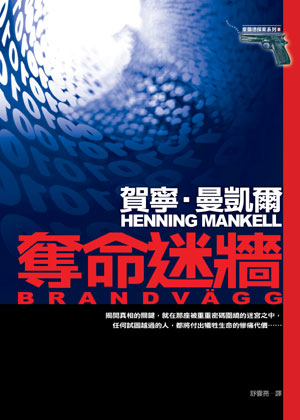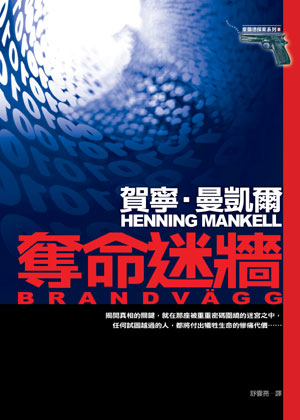內容試閱
他朝那些孩子走去,他們還在踢足球。
『你們知道這附近哪裡有花店?』他問道。
其中一個男孩指向遠方。
韋蘭德拿出錢包,抽出一張一百克朗的紙鈔。
『幫我跑去花店買些花,』他說,『要玫瑰花。快點回來。我會給你十克朗跑腿費。』
那男孩睜著一雙大眼看著他,但接下了錢。
『我是警察,』韋蘭德說,『很厲害的警察。如果你拿錢跑了,我會找到你的。』
男孩搖搖頭。
『你為什麼沒穿制服?』他以生硬的瑞典語問,『你看起來不像警察,不像厲害的警察。』
蘭德拿出警徽給他看。那男孩看了一會兒,便點點頭撒腿出發了。其他孩子則繼續踢球。
他很可能不會回來了,韋蘭德陰鬱地想,從很久前,我們的國民就已經不再尊重警察了。
但那孩子帶著玫瑰花回來了。韋蘭德給了他二十克朗,十克朗是跑腿費,另外十克朗是當作回來的報酬。過了一會兒,一輛計程車駛過來停下,斯特凡的母親下了車。她變老了,瘦得像是生了場大病。一個七歲左右的小男孩站在她身邊,他長得很像他哥哥,睜著一雙充滿恐懼的大眼。從那時起到現在,他仍然生活在驚恐之中。韋蘭德走過去招呼他們。
『就只有我們和牧師。』她說。
他們走進教堂。牧師是個年輕人,正坐在棺材旁看報。韋蘭德發覺安妮特‧弗雷德曼突然抓住他的手臂。
他明白了。
牧師站起身來,把報紙放在一邊。他們在棺木右邊坐了下來。她仍然挽著他的胳膊。
韋蘭德想,她先是失去了丈夫。畢雍‧弗雷德曼是個粗暴而讓人厭惡的男人,經常打她並讓孩子受驚,但他是她的丈夫和孩子的父親。後來,他被自己的兒子殺了。然後,她最大的孩子露易絲死了。現在,她來到這裡,埋葬她的兒子。她還剩下什麼?半條命嗎?
有人在他們身後走進教堂。安妮特‧弗雷德曼似乎沒有聽到,不然就是她正盡力自制,以至於無法去注意其他事情。有個與韋蘭德年紀相仿的女子正沿著走道走上前來。安妮特‧弗雷德曼終於抬起眼皮,對她點了點頭,那名女子在他們身後幾排坐了下來。
『她是醫生,』安妮特‧弗雷德曼說,『叫艾格妮‧麥斯特羅。揚斯狀況不太好的時候,她幫過我們。』
韋蘭德認得這個名字,但花了點時間才回想起來。在某天夜裡,透過斯德哥爾摩電台,他找到了當時身在蘭德梭外海一艘遊艇上的艾格妮‧麥斯特羅和她丈夫,是他們提供了斯特凡‧弗雷德曼那件案子裡最重要的線索。
韋蘭德聽到風琴聲,但沒看見彈風琴的人,原來是牧師按下了錄音機。
他納悶著為什麼沒聽見教堂鐘聲,葬禮不都是從教堂鐘聲開始的嗎?但這想法因為安妮特‧弗雷德曼再次抓緊他的手臂而被驅走了。他瞥了她身邊的男孩一眼,這年紀的孩子適合參加葬禮嗎?韋蘭德不這麼認為,但男孩看起來相當鎮定。
音樂聲消失了,牧師開始講話,他重申基督的話語:『把你們的小兄弟帶到我這裡來。』韋蘭德把注意力集中在棺木上的花圈,數著花朵好讓喉頭的腫脹不至於擴大。
儀式很短,然後他們走近棺木。安妮特‧弗雷德曼的呼吸粗重,彷彿她是正在最後衝刺的短跑選手。艾格妮‧麥斯特羅站在他們身後。韋蘭德轉向那個似乎不太耐煩的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