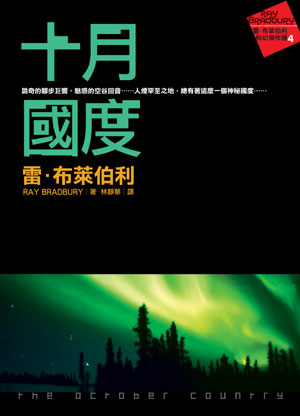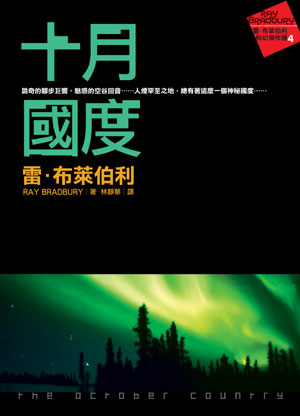內容試閱
這是個晴朗的春日午後,他們的車沿著寬闊的林蔭大道行駛。湛藍的天,豔麗的花朵,還有和煦的微風。大衛一直在說話,點了雪茄又繼續說。愛麗絲輕聲回答,神情略微輕鬆了些,但她沒有如母親般緊緊地、溺愛地抱著嬰兒,這使大衛的心微微發痛。她抱嬰兒的樣子好像在抱一個瓷器。
『噯,』他終於含笑說,『我們要給他取什麼名字?』
愛麗絲‧雷柏注視著從車窗外滑過那青翠蓊鬱的樹木。『先不要決定吧,我想等我們想出個特別的名字再說。不要對著他的臉噴煙。』她說話時不疾不徐,語氣也毫無變化,最後一句更是缺乏母愛,既無興趣也無惱怒,她只是平淡地從口中說出這句話。
他的丈夫有點不安,便將雪茄扔出窗外。『對不起。』他說。
嬰兒躺在母親的臂彎裡,陽光與樹影輪番投射在他臉上,他的藍眼睛睜得大大的,有如新開的藍色春花,他那粉紅濕潤的小嘴咿咿呀呀蠕動著。
愛麗絲迅速瞥一眼嬰兒,她的丈夫感覺她貼著他在發抖。『冷嗎?』他問。
『有點涼,還是把窗子搖起來吧,大衛。』
不僅僅是涼的問題。他將車窗緩緩搖起。
晚餐時間。
大衛把孩子從育嬰室抱出來,在他背後墊上許多枕頭,讓他以一個令他有點不知所措的角度坐在新買的高腳椅上。
愛麗絲望著她的刀叉。『他還沒大到可以坐高腳椅。』她說。
『讓他坐在這裡比較好玩。』大衛說,他的心情很好。『一切都順利極了,辦公室也一樣,訂單多到不行,一個不小心今年又要賺進一萬五了。嘿,妳留意一下小子好嗎?口水都滴到下巴上了!』他歪過去用他的餐巾擦嬰兒的嘴,從眼角瞥見愛麗絲連看都沒看一眼。他把嬰兒的口水擦乾淨。
『我猜這事一點也不好玩,』他說,又繼續吃他的晚餐,『可是一個作母親的多少總會對她自己的孩子有點興趣吧!』
愛麗絲揚起下巴,『別說這種話!不要在他面前說!如果你非說不可,待會兒再說。』
『待會兒?』他大聲說,『在面前、在背後,這有什麼差別?』說著,他立刻又平靜下來,帶點歉疚,『好吧,我知道了。』
飯罷,她由著他將嬰兒抱上樓。她沒有叫他抱;她只是隨他。
下樓之後,他發現她站在收音機旁,音樂響著,但她沒有在聽。她閉著眼睛,作沉思反省狀。他出現時她吃了一驚。
她忽然靠上去,緊緊貼著他,溫柔而快速,和以前一樣。她的唇緊貼著他的。他有點吃驚。嬰兒離開,上樓了,離開這個房間,她又可以呼吸,又活過來了。她自由了。她不停地輕聲叨絮著。
『謝謝你,謝謝你,親愛的,你還是一樣的你,可靠,如此可靠!』
她在育嬰室門口停了一下,有些猶豫,然後忽然抓住門把走進去。他看她小心翼翼接近搖籃,往下看,立刻像被打一巴掌似地楞了一下。『大衛!』
雷柏走到搖籃邊。
嬰兒的臉紅得發亮,而且臉上濕漉漉的、一頭汗水;他的粉紅小嘴一張一閤、一張一閤;一雙眼睛澄藍,兩隻手在空中揮動。
『喔,』大衛說,『他剛剛哭了。』
『是嗎?』愛麗絲‧雷柏抓住搖籃邊穩定自己,『我沒聽見。』
『門關著。』
『這是為什麼他的呼吸如此急促呢,為什麼他的臉這麼紅?』
『沒錯,可憐的小東西,一個人在黑暗中哭泣。他今晚可以睡在我們房間裡,免得他又哭了。』
『你會把他寵壞。』他妻子說。
當雷柏將搖籃推進他們臥房時,發現她在後面緊盯著他。他默默更衣後坐在床邊,這時他忽然抬頭,咒了一聲,彈一下手指。『該死!我忘了告訴妳,星期五我得飛一趟芝加哥。』
『喔,大衛。』她說不出話來。
『我已經把這趟行程推延兩個月,現在非去不可了。』
『我不敢一個人在家。』
『星期五以前我們會有一個新廚子,她會整天在這裡,我只去幾天。』
『我怕。我不知道怕什麼。如果我告訴你你絕不會相信。我想我瘋了。』
這時他已經上床了。她把臥房的燈熄了;他聽見她走到床邊,掀開被單鑽進去。他聞到溫暖的女人香緊挨著他。他說:『如果妳希望我再多等幾天,或許我可以——』
『你看。』她手指著說。
嬰兒清醒地躺在他的小床上,正用他那雙深邃銳利的藍眼睛直視著他。
燈又捻熄了,她緊挨著他顫抖。
『害怕自己生的孩子是件可怕的事,』她在他耳邊急促、憎惡地低聲說,『他想殺我!他躺在那裡聽我們說話,等著你離開,他好再設法殺我!不騙你!』她開始啜泣。
『好了,』他不斷安慰她,『不要說了,請妳不要再說了。』
她在黑暗中哭了很久。夜深了,她稍稍放鬆,但仍舊依偎著他發抖。她的呼吸漸漸緩和,溫暖而規律,她的身體蜷縮著睡了。
他也昏昏欲睡。
但就在他的眼皮漸漸沉重,身體逐漸沉入濃濃的睡意時,他忽然聽見一個微弱的怪聲,似乎房間內還有人醒著。
那是咂著濕潤的粉紅小嘴的聲音。
寶寶。
然後他——睡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