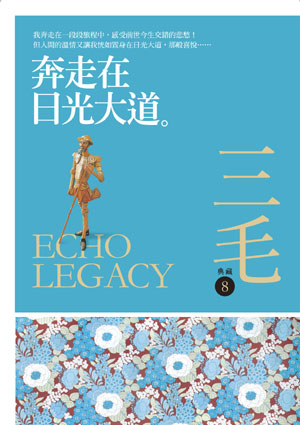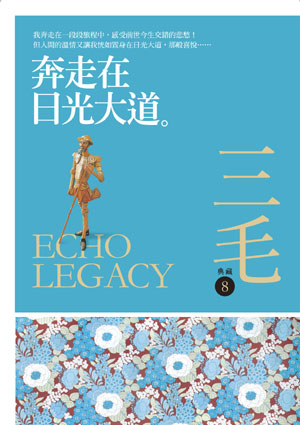內容試閱
不是為了這一夜,那麼前面的日子都不能引誘我寫什麼的,讓我寫下這一個有趣的夜晚,才去說說墨西哥的花船和街頭巷尾的所聞所見吧!
不帶米夏去參加任何晚上的應酬並沒有使我心裏不安。他必須明白自己的職責和身分,過分的寵他只有使他沿途一無所獲。
再說,有時候公私分明是有必要的,尤其是國籍不一樣的同事,行事為人便與對待自己的同胞有些出入了。
那一夜,蘇珊娜做了一天的菜,約根在家請客,要來十幾個客人,這些人大半是駐在墨西哥的外交官,而本地人,是不被邀請的。
約根沒有柔軟而彈性的胸懷。在階級上,他是可恨而令人瞧不起的迂腐。奇怪的是,那麼多年來,他愛的一直是一個與他性格全然不同的東方女孩子。這件事上怎麼又不矛盾,反而處處以此為他最大的驕傲呢?
再大的宴會,我的打扮也可能只是一襲白衣,這樣的裝扮誰也習慣了,好似沒有人覺得這份樸素是不當的行為。我自己,心思早已不在這些事上爭長短,倒也自然了。
當我在那個夜晚走進客廳時,已有四五位客人站著坐著喝酒了。他們不算陌生,幾個晚上的酒會,碰來碰去也不過是這幾張面孔罷了。
男客中只有米夏穿著一件淡藍的襯衫,在那群深色西裝的中年人裏面,他顯得那麼的天真、迷茫、興奮而又緊張。冷眼看著這個大孩子,心裏不知怎的有些抱歉,好似欺負了人一樣。雖然他自己滿歡喜這場宴會的樣子,我還是有些可憐他。
人來得很多,當莎賓娜走進來時,談話還是突然停頓了一會兒。
這個女人在五天內已見過三次了,她的身旁是那個斯文凝重給我印象極好的丈夫──文化參事。
她自己,一身銀灰的打扮,孔雀似的張開了全部的光華,內聚力極強的人,只是我怕看這個中年女人喝酒,每一次的宴會,酒後的莎賓娜總是瘋狂,今夜她的獵物又會是誰呢?
我們文雅的吃東西、喝酒、談話、聽音樂、講笑話,說說各國見聞。不能深入,因為沒有交情。為了對米夏的禮貌,大家儘可能用英文了。
這種聚會實在是無聊而枯燥的,一般時候的我,在一小時後一定離去。往往約根先送我回家,他再轉回去,然後午夜幾時回來便不知道了,我走了以後那種宴會如何收場也沒有問過。
那日因為是在約根自己家中,我無法離去。
其中一個我喜歡的朋友,突然講了一個吸血鬼在紐約吸不到人血的電影:那個城裏的人沒有血,鬼太餓了,只好去吃了一個漢堡。這使我又稍稍高興了一點,覺得這種談話還算活潑,也忍受了下去。
莎賓娜遠遠的埋在一組椅墊裏,她的頭半枕在別人先生的肩上,那位先生的太太拚命在吃東西。
一小群人在爭辯政治,我在小客廳裏講話,約根坐在我對面,神情嚴肅的對著我,好似要將我吃掉一樣的又恨又愛的凝視著。
夜濃了,酒更烈了,室內煙霧一片,男女的笑聲曖昧而釋放了,外衣脫去了,音樂更響了。而我,疲倦無聊得只想去睡覺。
那邊莎賓娜突然高叫起來,喝得差不多了:「我恨我的孩子,他們拿走了我的享受,我的青春,我的自由,還有我的身材,你看,你看──」
她身邊的那位男士刷一聲抽身站起來走開了。
「來嘛!來嘛!誰跟我來跳舞──」她大嚷著,張開了雙臂站在大廳裏,嘴唇半張著,眼睛迷迷濛濛,說不出是什麼欲望,那麼強烈的狂奔而出。
唉!我突然覺得,她是一隻饑餓的獸,在這墨西哥神秘的夜裏開始行獵了。
我心裏喜歡的幾對夫婦在這當兒很快而有禮的告辭了。分手時大家親頰道晚安,講吸血鬼故事給我聽的那個小鬍子悄悄拍拍我的臉,說:「好孩子,快樂些啊!不過是一場宴會罷了!」
送走了客人,我走回客廳去,在那個陰暗的大盆景邊,莎賓娜的雙臂緊緊纏住了一個淺藍襯衫的身影,他們背著人群,沒有聲息。
我慢慢經過他們,坐下來,拿起一支煙,正要找火,莎賓娜的先生啪一下給我湊過來點上了,我們在火光中交換了一個眼神,沒有說一句話。
燈光扭暗了,音樂停止了,沒有人再去顧它。梳妹妹頭、看似小女孩般的另一個女人抱住約根的頭,半哭半笑的說:「我的婚姻空虛,我失去了自己,好人,你安慰我嗎──」
那邊又有喃喃的聲音,在對男人說:「什麼叫快樂,你說,你說,什麼叫快樂──」
客廳的人突然少了,臥室的門一間一間關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