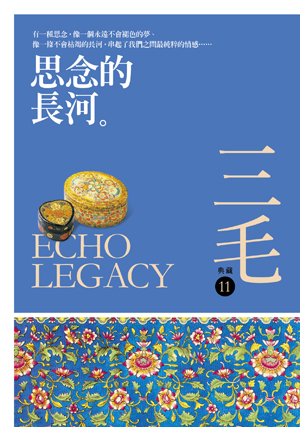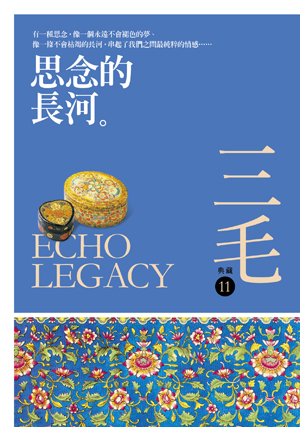內容試閱
撒哈拉之心。
曾經這麼想過,如果有一天,有一個女兒,她必要被稱為:撒哈拉‧阿非利加‧葛羅‧陳。SAHARA AFRICA QUERO CHEN。
這個名字,將是她的父親、母親和北非沙漠永恆的結合與紀念。
沙漠的居民一再的說──那些沉迷安樂生活,美味食物和喜歡跟女人們舒舒服服過日子的人,是不配去沙漠的。
雖然自己是一個女子,卻實實在在明白了這句話裏的含意。
也許,當年的遠赴撒哈拉,最初的動機,是為著它本身的詭秘、荒涼和原始。
這一份強烈的呼喚,在定居下來之後,慢慢化生為刻骨銘心的愛。願意將它視為自己選擇的土地,在那兒生養子女,安居樂業,一直到老死。
每一日的生活和挑戰,在那筆墨無以形容的荒原裏,燒出了一個全新的靈魂。在生與死的極限裏,為自己的存活,找出了真正的意義。
撒哈拉的孤寂,已是另一種層面的崇高。大自然的威力和不可測出的明日,亦是絕對的。
在那一片隨時可以喪失生命的險惡環境裏,如何用人的勇氣和智慧,面對那不能逃避的苦難──而且活得泰然,便是光榮和價值最好的詮釋了。
大自然是公平的,在那看似一無所有的荒原、烈日、酷寒、貧苦與焦渴裏,它回報給愛它的人,懂它的人──生的欣喜、悲傷、啟示、體驗和不屈服的韌性與耐力。
撒哈拉沙漠千變萬化,它的名字,原意叫做「空」。我說,它是永恆。
沙漠裏,最美的,是那永不絕滅的生命。
是一口又一口隱藏的水井,是一代又一代的來和去,是男女的愛戀與生育,是小羊小駱駝的出世,是風暴之後的重建家園。是節日,是狂歡,是年年月月日日沒有怨言的操作和理所當然的活下去。
沙漠的至美,更是那一棵棵手臂張向天空的枯樹。是一朵在乾地上掙扎著開盡生之喜悅的小紫花。是一隻孤鳥的哀鳴劃破長空。是夕陽西下時,化入一輪紅日中那個單騎的人。
也是它九條龍捲風將不出一聲的小羊抽上天地玄黃。也是它如夢如魅如妖如真如幻的海市蜃樓。是近六十度的酷熱凝固如岩漿。是如零度的寒冷刺骨如刀。
是神,是魔,是天堂,是地獄,是撒哈拉。
是沙堆裏挖掘出來的貝殼化石,是刻著原始壁畫的洞穴。是再沒有江河的斷崖深淵。是傳說了千年的迷鬼獫狺。是會流動的墳場,是埋下去數十年也不腐壞的屍身。是鬼眼睛和蠱術。是齋月,是膜拜。是地也老、天也荒。
沙漠的極美,是清晨曠野,牧羊女脆亮悠長的叱喝裏,被喚出來的朝陽和全新的一天。
沙漠是一個永不褪色的夢,風暴過去的時候,一樣萬里平沙,碧空如洗。它,仍然叫永恆。
撒哈拉啊!在你的懷抱裏,做過沒有鮮花的新娘,在你的穹蒼下,返璞歸真。
你以你的夥伴太陽,用世上一切的悲喜融化了一個婦人,又塑造了另一個靈魂,再刻盡了你的風貌,在一根根骨頭裏。
你的名字,在我的身上。
看起來,你已經只是地圖上的一幅土黃色的頁數。看起來,這一切都像一場遺忘。看起來,也不敢再提你。看起來,這不過是風塵裏的匆匆。
可是,心裏知道,已經中了那一句沙漠的咒語:「只要踏上這片土地的人,必然一再的想回來,別無他法。」
已是撒哈拉永生的居民,是一個大漠的女子。再沒有什麼能夠懼怕了,包括早已在那片土地上教過了千次百次的生與死。
只要活著一天,就必然一次又一次的愛著你──撒哈拉。
沒有鄉愁,沒有離開過你。
如果今生有一個女人,她的丈夫叫她「撒哈拉之心」,那麼如果他們有一個女兒,那個名字必要被稱為:撒哈拉‧阿非利加。
此篇為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