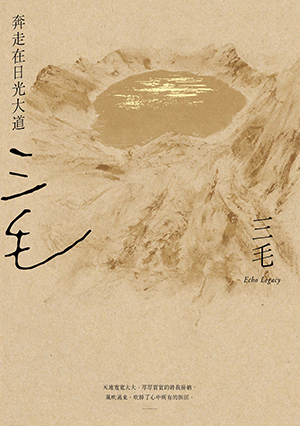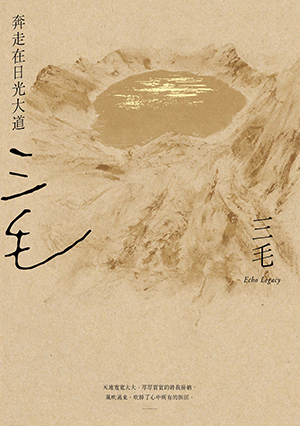內容試閱
車子是中午在炎熱的海港開出的,進入山區的時候,天氣變了,雨水傾倒而下,車廂內空氣渾濁不堪,我靠著窗戶不知不覺的睡了過去。
當我被刺骨的微風凍醒時,伏蓋著的安地斯蒼蒼茫茫的大草原,在雨後明淨如洗的黃昏裏將我整個擁抱起來。
眼前的景色,該是夢中來過千百次了,那份眼熟,令人有若回歸,鄉愁般的心境啊,怎麼竟是這兒!
車子轉了一個彎,大雪山「侵咆拉索」巨獸也似的撲面而來。
只因沒有防備這座在高原上仍然拔地而起的大山是這麼突然出現的,我往後一靠,仍是吃了一驚。
看見山的那一駭,我的靈魂衝了出去,飛過尤加利樹梢,飛過田野,飛過草原,繞著那座冷冰積雪的山峰怎麼也回不下來。
一時裏,以為自己是車禍死了,心神才離開了身體,可是看看全車的人,都好好的坐著。
「唉!回來了!」我心裏暗暗的嘆息起來。
對於這種似曾相識的感應,沒有人能數說,厄瓜多爾的高地,於我並不陌生的啊!
「阿平!阿平!」米夏一直在喊我,我無法回答他。
我定定的望著那座就似撲壓在胸前的六千多公尺高的雪山,覺著它的寒冷和熟悉,整個人完全飄浮起來,又要飛出去了。
一時裏,今生今世的種種歷練,電影般快速的掠過,那些悲歡歲月,那些在世和去世的親人,想起來竟然完全沒有絲毫感覺,好似在看別人的事情一般。
大概死,便是這樣明淨如雪般的清朗和淡漠吧!
「哎呀!妳的指甲和嘴唇都紫了!」米夏叫了起來。
我緩緩的問米夏:「海拔多少了?」
「這一帶,書上說超過三千兩百公尺,下到里奧龐巴是兩千六百五十。」
這時候我才看了一下自己的雙手,怎麼都腫起來了,呼吸也困難得很。
什麼靈魂出竅的感應,根本是身體不適才弄出來的幻覺。
車子停在一個小站上,司機喊著:「休息十分鐘!」
我沒有法子下車,這樣的高度使人難以動彈。
就在車站電線杆那支幽暗的路燈下,兩個老極了的印地安夫婦蹲坐在路邊。
女人圍著深色的長裙,披了好幾層彩色厚厚的肩毯,梳著粗辮子,頭上不可少的戴著舊呢帽。
兩個人專心的蹲在那兒用手撕一塊麵包吃。
我注視著這些純血的族人,心裏禁不住湧出一陣認同的狂喜,他們長得多麼好看啊!
「老媽媽啊!我已經去了一轉又回來了,妳怎麼還蹲在這兒呢!」我默默的與車邊的婦人在心裏交談起來。
有關自己前世是印地安人的那份猜測,又潮水似的湧上來。
這個小鎮的幾條街上,全是印地安人,平地人是看不到了。
暮色更濃了。街上人影幢幢,一切如夢如幻,真是不知身在何處?
方才下了里奧龐巴的公車站,一對歐洲模樣的男女好似來接我們似的走了上來。
那時我的心臟已經很不舒服了,對他們笑笑,便想走開去,並不想說什麼話。
他們攔住了我,一直請我們去住同一家旅館,說是那間房間有五個床,位子不滿,旅館叫他們自己出來選人。
下車的人那麼多,被人選中了,也算榮幸。
旅館是出租舖位的,一個大房間,宿舍一般,非常清潔安靜。
那對旅客是瑞士來的,兩人從基托坐車來這小城,預備看次日星期六的印地安人大趕集。看上去正正派派的人,也不拒絕他們了。
進了旅舍,選了靠窗的一張舖位,將簡單的小提包安置在床上,便去公用浴室刷牙了。
旅行了這一串國家,行李越來越多,可是大件的東西,必是寄存在抵達後的第一個旅舍裏,以後的國內遊走,便是小提包就上路了。
打開牙膏蓋子,裏面的牙膏嘩一下噴了出來,這樣的情形是突然上到高地來的壓力所造成的,非常有趣而新鮮。
初上高原,不過近三千公尺吧,我已舉步無力,晚飯亦不能吃,別人全都沒有不適的感覺,偏是自己的心臟,細細針刺般的疼痛又發作起來。
沒有敢去小城內逛街,早早睡下了。
因為睡的是大通舖,翻身都不敢,怕吵醒了同室的人,這樣徹夜失眠到清晨四點多,窗外街道上趕集的印地安人已經喧譁的由四面八方進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