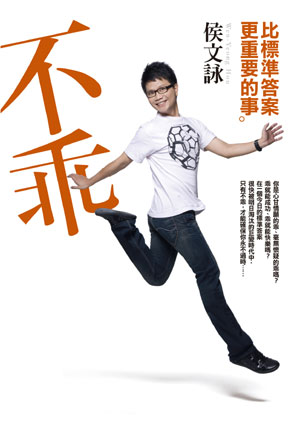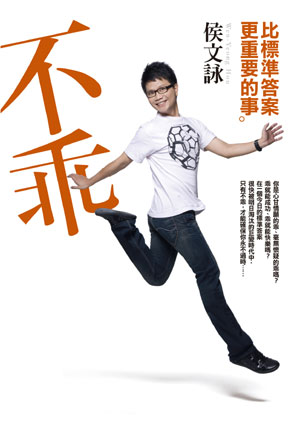內容試閱
有些人也許要問:如果可以不用經歷那些無可預測的「不乖」過程,乖乖地長大,不是很好嗎?
真的很好嗎?
人生真的可以這麼樣「乖乖」地到老死而沒有疑問?
同樣坐著校車上學,到底是有過「不乖」經驗,還是沒有「不乖」經驗的孩子更叫人放心呢?
答案其實是很清楚明白的。
和玩樂器很像,很多時候,人生中的完美演出也是必須通過許多錯誤與練習才能達到的。大部分小孩準備考試時,師長們會要求小孩做模擬考題或測驗練習題,覺得非這樣不能考得高分。可是回到「真實人生」這個場域──不管是談戀愛、交朋友、選填志願,大部分小孩卻連一點練習、嘗試錯誤的機會都沒有。
這樣,在面對人生試鍊時,如何能考取高分呢?
我們的人生太害怕「錯誤」了,覺得在嘗試錯誤的過程要付出太多無法預期的時間與代價。可是如果嘗試錯誤是學習過程必要的一部分呢?我們是不是得預留下一些「錯誤嘗試」與「不乖」的空間與機會給自己呢?
有些父母親不免要擔心地問:是不是等孩子長大一點,心智成熟一點,能夠自行判斷時,再給他們這個空間。
這樣的思考最大的謬誤在於:
首先,如果沒有這些空間,他們很可能心智上永遠都不會長大。
再來,更重要的,如果真的一定得有犯錯的經驗,當然是越年輕代價越小啊。
我年輕時曾經為人借貸當保證人,損失了幾百萬元。這些錢占了我當時的資產一半,覺得痛苦不堪,可是現在想想其實也算還好。幸好是年輕時就有這個經驗,並且學得教訓,從此人生就算打過疫苗了。否則到了這個年紀再遇到這種事,也損失現在一半以上的資產,那才是真正的慘不忍睹啊。
對很多捨不得小孩嘗試錯誤的父母親其實是要換個角度來看事情的,如果嘗試錯誤對孩子的成長是必須的,那麼孩子能在你看得見的時候嘗試,其實是件好事。不管後果如何,做父母的多少還可以陪伴孩子度過困境,或是給予一些必要的援助。否則等他離開父母時才碰到,就算有心可能都幫不上忙了。
以前常聽人說:「人不輕狂枉少年。」過去總覺得這話聽來有點輕狂。可是現在想想,這話實在是人生的至理名言。老實說,沒有輕狂少年的經驗,就不可能造就出一個深思熟慮的成人。就像許多植物都必須受到溫度或照光的刺激之後才能開花一樣。叛逆、不乖也是生命之中開花、結果必須的「生長激素」啊。
人不輕狂不但枉費少年,更進一步,我還要說:人不「叛逆」枉少年。人無「不乖」枉少年啊。
做一個太乖的人當然不好。
可不可以不寫功課
我這樣說,一定有人不以為然。反駁我:
「你說『不乖』才好,但殺人、搶劫、打架也是不乖啊。難道這樣也可以嗎?」
殺人、搶劫、打架當然是不對的事。但把「不乖」等同於「不對」,這樣的說法是有問題的。我認為,所謂的「不乖」,指的應該是一種反對「不加思考就聽話、順從」的態度。一個乖的人,待在腐敗、犯罪、落伍的群體中,反而最容易被同化,做出貪污、違法、無效率的壞事。因此,重點不是「聽不聽話」,而是事情有沒有經過自己的思考與價值判斷。如果經過自己的思考與價值判斷之後,是「好」的、「對」的事,當然要義無反顧去做。反之,就要有勇氣戒除、拒絕。
我再說另一個故事。
我們家小朋友在很小的時候曾經不寫功課,聯絡簿一拿回家裡,常常滿篇都被老師寫滿了紅字。為了這個,兒子常常和媽媽有意見衝突。後來兩個人鬧得雞飛狗跳,媽媽只好請我這個爸爸出面處理。
很多家長處理這種事的基本邏輯就是以「完成功課」為前提,在這個前提之下,展開威脅利誘──不用說,這樣的威脅利誘當然是以「乖」為前提的。
不過我個人的看法正好相反。在我看來,我的小孩好不容易對他的世界開始發出問題,開始有了不乖的「叛逆」思考,這樣的機會我當然不可輕易錯過。
我把決定換個角度,順著小孩的思路,從「不乖」為前提來思考問題。
如果要不乖的話,我們開始討論:怎麼樣才可以不寫功課呢?
小孩一開始聽到我的議題當然是一臉狐疑的表情,不過很快他就感受到,我是認真的。沒多久,我們就想出了不少辦法(雖然兒子覺得不太可行),這些辦法包括了:
一、我把印章交給他,讓他自己在聯絡簿上蓋章。
(小孩問:「可是功課沒寫,老師如果打電話來問我會怎麼說?」我說:「我當然實話實說,說章是你自己蓋的。我可不能幫你說謊。」這個提議立刻就胎死腹中了。)
二、或者,我打電話請老師允許他不要寫功課。
(小孩問:「全班只有我一個人不寫功課,同學會怎麼看?」我說:「別的同學要怎麼看你,我實在無能為力。再不然,我打電話給所有的家長,請他們叮嚀他們的小孩,去學校不可以嘲笑你。」當然,這個提議也出局了。)
三、最後,我們又想出了一個辦法:根據「沒有盲腸就沒有盲腸炎」的外科法則,如果不上學也就沒有功課了。(我表示可以向教育局提出在家自主學習的申請,這樣他不用去學校上學,也就沒有功課,更沒有蓋章或者是同學看法的問題了。)
小朋友聽了,似乎覺得這個方案有可行之處,不過為了慎重起見,他希望我讓他考慮三天。
我欣然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