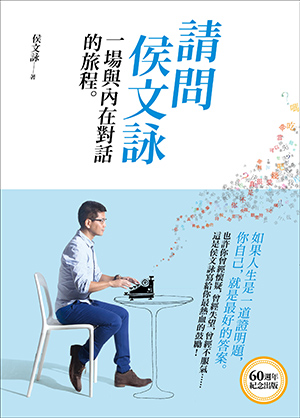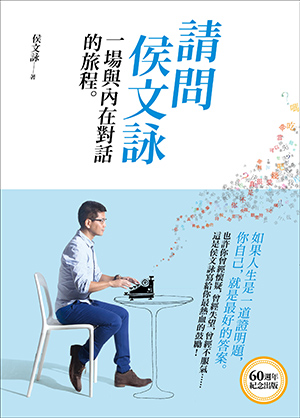內容試閱
4
或許有那麼一點點不甘心的成分吧,二○一二年夏天,當《我就是忍不住笑了》出版時,我和出版社的編輯、企劃商量之後,決定把過去例行的大型演講改成「小型」的、「專門回答問題」的座談會。我們事先在網路上公開徵求問題,根據讀者提出的問題,挑選並且邀請他們來參加發表會。
兩場座談會讓我有機會更靠近了讀者的心事,前前後後一共回答了一百多個問題。這個過程,固然彌補了一些無法回答完讀者的問題的遺憾,但是在理直氣壯地回答問題的過程中,另一種我始料未及的忐忑心情卻油然浮現。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我寫的小說《危險心靈》中,因為教育事件發動抗爭的謝正傑接受電視採訪時,主持人和他的對話。
「謝同學,以你的年紀從事這樣的抗爭,我相信一定承受了許多壓力,」主持人問:「自己會不會感到害怕呢?」
我(謝政傑)點點頭。「會。」
「你怕什麼?」
沉默。
「怕被老師批評?怕學測成績不好?」主持人試圖引導我,「怕影響將來前途?」
我不停地搖頭,又清了清喉嚨,最後終於說:「我怕萬一我相信的事情是錯的。」
一邊回答著這一百多個問題,我一邊懷疑起來:
一個像我這樣的作家,以我有限的人生經歷──外加這麼多連自己都找不到答案的問題,真的有能力回答所有這些包羅萬象的問題嗎?或者,就算真的回答了,我的答案對解決讀者的問題有幫助嗎?萬一,答案不但派不上用場,甚至造成反效果,怎麼辦?
我就這樣懷抱著複雜的心情,完成了這兩場座談會。座談會之後,出版社很貼心地把當日發表會的內容,聽寫成逐字稿讓我參考。一頁頁翻著這些逐字稿,更加深了我的忐忑不安──才經過沒幾個月,我很容易就看見自己思慮不周的漏洞不少。我發現,有些問題,我其實可以用更好的切入點去思考,有些答案,其實可以用更有趣、更周密的方式回答。
這些發現在在提醒我,「答案」是一種有機體──它會隨著時間、經驗的累積,不斷成長、變動的。也正是這個提醒,觸動了我寫作核心最敏感的那根神經。我開始想,隨著外在的環境、人事的變化,答案在未來是會不斷地被推翻、進化的。可是我的回答一旦化成了文字(或者是網路上的影像),卻會像死掉的標本一樣長久地存在。
既然如此,死掉的文字,如何追得上不斷在演化的答案呢?
如果我相信,一個作家應該帶著問題和讀者一起思索,不斷追求更好的答案,而不是提供答案,讓讀者和自己感到滿足,從此停止對問題的思考。那麼,為什麼還要回答這麼多我未必能解決的問題呢?
一方面我告訴自己:人之大患在好為人師。但另一方面,手機螢幕上像是河流般流過的問題所發出的嗶嗶聲,又給我另一種迫切。
To answer, or not to answer ?(回答,或不回答?)
對我而言,這變成了一個真實的兩難。
那次的座談會之後沒多久,我輾轉收到了一個母親的來函。
這個母親告訴我,她的孩子本來是個在各方面都表現得非常優秀的學生。自從看了我寫的幾部長篇小說之後,不但在校成績一落千丈,情緒也越來越不穩定。父母親試著跟她溝通,也拜託學校的輔導老師和她討論,試盡各種方法都沒有幫助。她知道孩子是我的粉絲,又曾經參加過我的座談會,因為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才會冒昧提出這個請求,希望我能跟孩子單獨談談。信末,這個母親還附上了一篇孩子的文章,讓我參考。
我讀了孩子的文章,注意到筆鋒之下有一種超乎她的年紀應有的細膩與早熟。我又回頭去查看了一下她在座談會的提問。儘管那天針對她的問題我做了回答,不過,顯然,我的答案並沒能為她釋疑解惑。
大概是自己沒回答好孩子問題的責任感吧,我開始和母親聯絡、安排和孩子見面的細節。母親客氣地透過出版社聯絡的人員,表示願意付給我諮詢費用。不過我委婉地拒絕了。幾番溝通往返之後,我告訴這位母親:如果她真的非得送什麼東西給我的話,就請她帶上一杯黑咖啡請我吧。
見面當天,一見到我,孩子的母親立刻遞上了熱騰騰的咖啡,對我深深地一鞠躬。她把孩子交給我。正要離開前,忽然伸出手來,握著我的手。
我稍稍地愣了一下。不知道是因為母親急切的心情給我的錯覺,或者是咖啡的熱度,那隻緊握著我的手有種很特別的溫度,讓我覺得有些意外。
「小孩就拜託你了。」
她就那樣殷重地握著我的手,一會兒,才放開我的手,轉身離開。
坐在我面前的孩子,有著一副鬱鬱寡歡的表情。她對我述說怎麼開始閱讀我的書,又說了閱讀我的書,個別的心得、心情。聽著她的敘述,你又感覺得到一種矛盾──一種在那張鬱鬱寡歡的表情之下,隱藏著澎湃情感的強烈矛盾。
「妳最喜歡我的故事裡面的哪一個角色?」
「沈韋。」她說。
「為什麼?」我問。沈韋是《危險心靈》中一個充滿思考的小孩。他在教育事件抗爭現場唱了一首〈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宣告了他的宣言之後沒多久,就以自殺結束了生命。
「我覺得他說出了我心裡的話。」接著這個孩子在我面前說出了小說裡面沈韋那段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