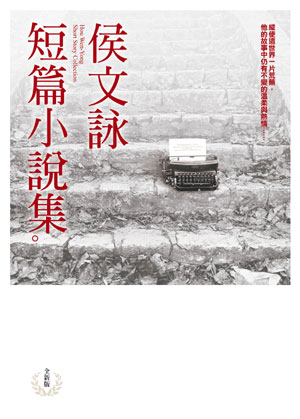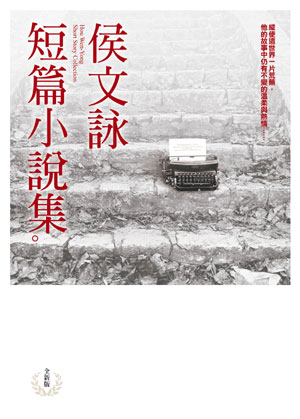內容試閱
《誰在遠方哭泣:原跋》在起跑線上──我認識侯文詠 張曼娟
他是一團流動著的溫暖。
初次相遇,是微涼的秋天,在一場頒獎典禮上。
典禮很熱鬧,寒暄道賀之聲把室溫逐漸升高。我獨自去領獎,縱然躋身在氣息交接的人群中,感覺仍然只是一個人。即將結束前,有個大男孩走來喚我的名,說了他自己的名字,並且合影。
我向來拙於結識新朋友,偶爾相遇,便有股難喻的欣欣然。讀了他那篇得獎的小小說和散文,同時發現,他有個非常適合寫作的名字──侯文詠。即使顛倒也雍容的名字。
並且,他還是那種聰明的、優秀的,從小到大一路領先,令我自慚形穢而望之生畏的醫科學生。
不久之後,合照的相片寄來了。我們兩人的身影佔去三分之二的畫面,但,焦距顯然有一點點失誤,因此,背後不相干的走動人群和擺設,十分鮮明清晰;我們這兩個主角臉上的表情,不知因模糊而不能確定;或是因為不能確定而模糊了。
可是,那張照片令我快樂了整個下午。原因之一,是我一向喜歡在焦點之外;原因之二是世上總有這些控制不住的突兀荒謬。
接著,我們便開始通信,持續地聯絡著。
這些年來,我已成為面對信紙便要遲疑的人;他在字裡行間的態度,則是一派興高采烈。
談文學、談電影、談醫學、談電腦……藉由四、五張整整密密的信紙,在我面前展開的是一個不十分熟悉的世界,事事樣樣充滿新奇。
讀他的信,便不能當他只是個年輕男孩;因為他那麼熱切地、溫和地、堅定而深刻地追尋探索的,都是生命最根源的問題,最繁複也最簡單的,生活的內涵。
七年嚴格的醫學教育,使他對人類生理各種結構組織都熟悉。然而,讀他小說時,禁不住要想,他又是用怎樣精密的器械解剖人心?
一位醫生是怎樣看待生命呢?
沒有人比他們更清楚地看見死亡的真相,知道貧富貴賤,都免不了這事;卻也沒有人比他們更執著地與死神拚搏,縱使到最後,死神總是絕對的贏家。
他好像也是用這種態度在寫作。明知道這世界千瘡百孔,不能細究,卻一點一滴的補綴著,儘管個人的聲嘶力竭,顯得如此薄弱,到底堅持下來了。
甚至還帶著微笑。
即使是敘述最慘酷的不幸滄桑,令聽者讀者聳然動容,他也會在故事的尾聲推開一扇向陽的窗,微笑著指引風中開放正好的花朵;清淺溪水;飄泊白雲,教人不要深陷在悲傷的情緒裡。
世上仍有許多值得盼望的。
細心的人也許會在轉瞬間,見到剎那燦亮,以為是他眼內淚華;而他畢竟帶著笑意,把許多事看得明白透徹以後,自然浮現的微笑。
在夏末秋初,季節交遞之際,日子突然變得索然冗苦,我記起遠在澎湖服役的他,那個在任何時空都能把自己妥貼安排的朋友。
到了澎湖,驀地擔憂,倘若我們已認不出彼此……而,很容易地,我在晃動的人群裡,一眼就看見他。他有自己的氣質。
島上三天,他帶我們去港口看紫色的船隻;沿途啃食冰淇淋;喝彈珠汽水;吃海鮮大餐;和我們坐在觀音亭,看著太陽一點一滴滑進金黃色的大海。
我的皮膚在陽光下,一次又一次,由紅轉黑;我那長滿硬繭的心在海風中,一層又一層剝落,回復到最初的柔軟敏銳。若不是他有著朋友珍貴的寬容瞭解,便不能夠。
坐在馬公航空站等飛機,原說了不勞他送;他也說了不一定能來。然而,穿著和天空同色制服,我那空軍軍官的朋友究竟還是來了。即將登機時,停機坪的另一邊,他向我們揮揚手臂。
天空的藍直瀉到地面,炙熱的太陽猛烈燒灼,狂飆的海風企圖拔起一切有根與無根的,這樣的天地,一片蒼茫原始。
只我的朋友踽踽獨行,甚至連影子也沒有。
那一次和夏季告別的旅行,我一直記得他從容不迫的向地平線走去。並不是刻意要頑強的執拗,只是謙遜平和,挺立在最惡劣的環境裡,自成一種莊嚴。
人,應該活得有尊嚴。他說,以各種不同的形式。
我認識文詠,最初是因為他的親和。後來是因為,總能發現一些新的好的,令人驚喜的。
旁人都說,我們的寫作和出書,是最好的時機;而他知道,我也知道,這未嘗不是最危險的時機。因此,看見對方仍認真的生活和寫作,便忍不住莫名的喜悅。
其實不曾預先約定,後來才發現,我們將在相同的時節,出版新書。彷彿並排在相同的起跑線上,等待槍響。終點是無盡的未知;腳步得自己調整,除了各自擁有不同的心情,過程中或還有風有雨,有疏疏密密的掌聲,成為一樁可以共享的秘密。
這是一條注定孤獨的道路,然而,因為有分享的朋友,於是,不覺得寂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