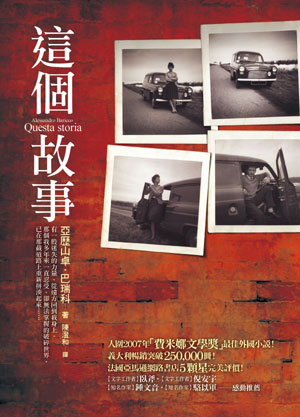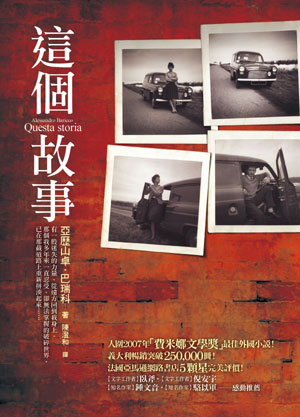內容試閱
雖然他叫老么,其實是第一個孩子。
「最後一個。」他母親才從分娩恢復意識就這麼說。
於是,他從此被喚作老么。
起初,他似乎根本不想知道這些。在他生下來的頭四年,幾乎所有的病都生過了。他們為他施洗了三次:因為神父無法為這樣一個張著眼睛的小不點做臨終塗油禮,所以每次都轉而為他施洗,免得沒做聖禮就空手回去。
「這沒什麼壞處。」
老么每一次都活下來,雖然蒼白、瘦小得有如一片破布,但總是活著。他有顆強壯的心,老爸這麼說。他運氣好,老媽說。
他就這樣活下來,一九○四年十一月他七歲又四個月的時候,父親帶他到牛棚,指著他僅有的財產,也就是牛棚裡的二十六頭法索尼品種乳牛,告訴他先不要跟媽媽提起,但他已準備要永遠擺脫這大堆的牛屎。
他做了個寬闊的手勢,表情相當莊嚴,像是在擁抱整個幽暗、發臭的牛棚,然後一字一字緩緩地說:李貝洛˙帕立修車庫(Libero Parri Garage)。Garage是老么從未聽過的一個法文字,當時他還以為是「飼養」或「乳製品」之類的意思,根本不瞭解箇中涵義。
「我們修理汽車。」父親扼要地說明。
事實上,這還是個新玩意。
「汽車還不存在。」等有一天晚上,在熄著燈的床上,老么的媽媽終於被告知時,她這樣註解。
「這是早晚的問題,汽車已經問世了。」李貝洛‧帕立告訴他的妻子,同時把一隻手伸到她的睡袍下。
「寶寶在旁邊。」
「沒問題,他也有事要做,他得學習。」
「寶寶在,手拿出來。」
「喔。」李貝洛‧帕立想起來在冬天的時候,為了節省爐火,他們都睡在同一個房間。
他們溫馨地躺了一會,然後他又開口。
「我和老么談過這件事,他也同意。」
「老么?」
「對。」
「老么還是個小孩,他才七歲,二十一公斤重,而且有氣喘病。」
「那有什麼關係,他是個很特別的小孩。」
在生過這麼多病,加上許多難以解釋的事情後,他們都認定老么或許是個不尋常的小孩。
「你難道不能和塔林談談?那還差不多。」
「他不會懂的,他跟別人一樣,腦子裡只有土地,土地和牲畜,他準會把我當作瘋子。」
「也許他是對的。」
「不,他不可能是對的。」
「你怎麼這麼說?」
「因為他是特雷札特人。」
在那個地方,這是個無法爭議的論點。
「那你去跟神父談。」
如果李貝洛‧帕立沒有成為無神論者或社會主義信徒,純粹只是因為他沒時間。只要給他幾小時多瞭解一點,他篤定會奉為圭臬。事實上,他痛恨教士。
「還有其他建議嗎?」他問。
「我只是開開玩笑。」
「不,妳不是開玩笑。」
「我發誓我是在開玩笑。」她伸一隻手到丈夫的褲襠裡,他喜歡她這麼做。
「寶寶在。」李貝洛‧帕立含糊地說。
「裝成若無其事就好。」她建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