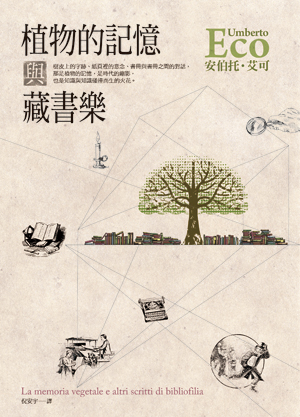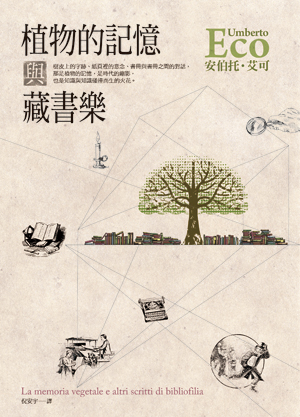內容試閱
植物的記憶
我首先要說明的是,由亞杜斯俱樂部主辦、布雷拉圖書館協辦的這場演講,對象並非樂此不疲的藏書家,或藏書甚豐、對此知之甚詳的博學之士,而是包括年輕一輩在內的普羅大眾,是從來不看書的那群人以外的人──根據義大利統計數據顯示一年閱讀不超過一本書的民眾。而且統計數字還無法說明這類閱讀人口中有多少人看的書其實是食譜,或警察笑話大全。
如果說因為場地太過嚴肅、演講題目艱澀,吸引了較多德高望重的大主教而非菜鳥教徒前來,也無關緊要。我建議大家可以把這場演講當作誦經修士在不同場合對不常誦經的修士循循說教的範例。
一,從亞當開始,人類就暴露出兩大缺點,一個是生理的,一個是心理的。生理缺點是,人終將一死;心理缺點是,人不喜歡死。既然無法修正生理缺點,人類就努力從心理層面著手,試圖找出死後的另一種存在模式。呼應這個問題的有哲學、啟示的宗教及其他神話、神秘信仰。某些東方哲學說生命之流不會停歇,死後會轉世投胎為另一個生命。但是聽到這樣的回答,我們自然會心生疑問:我轉世投胎後是否還記得我是誰,我的舊記憶可以與未來的記憶合而為一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們會很傷心,因為身為不知道自己以前是誰的另一個人,跟徹底消失並無差別。我不想要變成另一個人活著,我要做為我而活著。問題是我不再擁有軀體,便一心希望靈魂永存。而所有人給我們的答案,都告訴我們靈魂就是記憶。誠如法國哲學家梵樂希所說:「我之為我,我在每個瞬間,都是一個巨大的記憶」。
說起來,那些信誓旦旦向我們保證死後仍會記得自己一切的宗教有人性多了,而地獄會讓我們永遠記得被懲罰的原因。
如果我們知道在地獄裡要受的苦,不過就是不記得自己以前是誰的話,大家應該都會肆無忌憚地犯錯吧:一個既不擁有我的軀體,也不擁有我的記憶的傢伙受苦,與我有何相干呢?
記憶有兩個功能。第一個功能,也就是大家公認的功能,是將我們過去的經驗值留在回憶裡;第二個功能則是過濾經驗值,淘汰掉一些,把剩下的保留住。你們之中或許不少人知道波赫士的短篇小說《博聞強記的富內斯》,富內斯是一個對一切皆有所感照單全收的人,而且滴水不漏把一切都記在腦中:
我們看一眼,看到的是桌上有三個杯子。富內斯看到的卻是葡萄藤架上的枝條、葡萄串和每一顆葡萄。他記得一八八二年四月三十日黎明時分南方朝霞的形狀,而且能跟記憶中他只看過一次的大理石皮紋書封比較,跟奎布拉喬之役前夕他在尼格羅河上看到船槳激起的水花比較。那些記憶並非只是記憶:每一個視覺影像都跟肌肉、溫度等等感覺息息相關。他可以重現所有夢境,他睡夢中的所有影像。他曾經有兩、三次重現了一整天的時光,沒有半點猶豫,但每一次重現都需要耗掉一整天的時間。他跟我說:「我一個人的回憶,比開天闢地以來所有人類的回憶總和還要多。」他說:「睡夢中的我,跟清醒時的你們一樣。」還說:「先生,我的記憶,跟垃圾場一樣。」黑板上的圓形、直角三角形、菱形這些形狀,我們是用直覺感受,富內斯看到的卻是一匹小馬飛揚散亂的鬃毛、山崗上數不清的牛群、漫長守靈期間死者面容的千變萬化。我不知道他能看到天上多少星星(……)。
他不只記得每一座山上每一棵樹上的每片葉子,也記得每次看到或想像那片葉子的樣子。他決定把過去的每一天簡化為七萬個回憶,並加以編號。但是有兩個理由讓他打消了念頭:一是他意識到這件工作將永無止境;二是這麼做毫無意義。他想,恐怕到死的那一天,都還來不及把兒時回憶分門別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