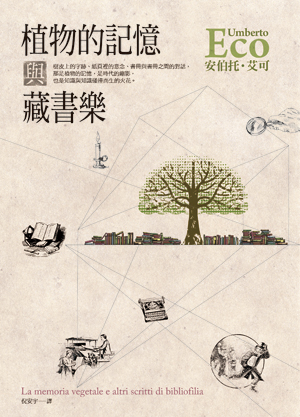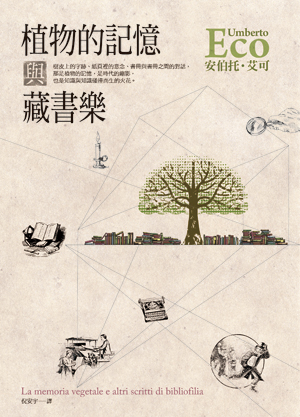內容試閱
書早於印刷,剛開始的形式是書卷,後來才慢慢變成我們今天熟悉的樣貌。無論是何種形式的書,都讓書寫更為個人化:書寫體現了部分記憶,雖然是集體記憶,但經過個人觀點的篩選。我們看到方尖碑、石碑、石板或刻在墓碑上的銘文,都會想要解碼,想要認識以前的字母,知道傳遞的訊息為何,例如是誰長眠於此、今年收成多少捆麥子、這個跟那個國家打敗了這位君主,卻不會問誰起草內容或負責銘刻。但我們看到一本書,想找的卻是人和看事情的個人角度。我們想要的不只是解碼,也想要詮釋一個想法跟企圖。既然想要探究的是企圖,會對文本產生質疑,也就會有不同的解讀。
閱讀變成了一種對話,但對話的對象(這是書弔詭的地方)不在我們面前,說不定數百年前就已過世,留下的只有他的書寫。對書提出質疑(是為詮釋學),既然有詮釋學就會有書本崇拜。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這三大一神教,就是以不斷質疑他們的經文而得以發展的。於是對質疑者而言,書本搖身一變,成為它保護、揭示的真理的象徵,要結束爭論、支持一篇文章或殲滅對手,可以說「這裡有寫」。我們對我們的生物記憶時常存疑:「我好像記得……但我也不確定」,而植物的記憶卻可以拿來展示,以消弭一切懷疑:「水真的是H2O,拿破崙真的是死於聖赫勒拿島,百科全書上是這麼寫的。」
在原始部落中,老者信誓旦旦地說:「在遙遠的那個夜晚發生了那些事,這是祖先口耳相傳直到今日的傳統」,部落很信任傳統。今天書本就是我們的老者。我們明知道書本常有錯誤,但還是願意認真看待它們。我們要書本將我們短暫一生無法累積的記憶交給我們。我們無法體會的是,文盲(或那些識字但不閱讀的人)的人生只有他自己,而我們卻經歷了許多人的人生,因此富裕。有一次邦皮亞尼想了一個口號:「閱讀的人,增值雙倍」。應該說增值一千倍吧。藉由書本的植物記憶,我們除了記得兒時遊戲,還記得普魯斯特;除了年少夢想,還記得尋找金銀島的吉姆的夢想;除了我們犯的錯之外,也從皮諾丘的自以為是或漢尼拔在卡普阿的判斷錯誤中學到教訓;我們不只為自己的愛情煎熬,也替阿里奧斯托筆下的安潔莉卡一掬同情淚,或在看完《百劫紅顏》中的安潔莉卡後比較不那麼自憐自艾;我們或多或少吸收了一點所羅門王的智慧,為聖赫勒拿島颳風的夜晚而顫抖,重溫奶奶說給我們聽的童話之外,也重溫了《一千零一夜》中莎赫扎德說的那些故事。
有人(例如尼采)認為如此一來,彷彿我們才剛出生,就已經老了。但文盲(無論先天或後天)從小就得忍受動脈硬化,而且不記得(因為沒有讀過)三月十五日發生了什麼事。當然,書本也可能讓我們記得許多謊言,但它們有互相反駁的優點,並教導我們要用批判的態度評估書本交到我們手中的資訊。不識他山之石,何以攻錯。
書是人生的一種保障,是關於永垂不朽的一個小小預告。不過是對過往的人生(阿門),不是對未來。我們不知道我們的經驗是否能在個人死後保存下來,但很確定我們保存了前人的經驗,後人也將保存我們的經驗。雖然我們不是荷馬,依舊可以在未來的記憶中擔任主角,例如,八月十四日晚間在米蘭-羅馬高速公路上意外發生車禍。這個結果不甚了了,但總好過什麼都沒有。為了能讓後人記得自己,黑若斯達特斯放火燒了以弗所的阿蒂蜜絲神殿,但後人記得的是他的愚昧。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去參加柯斯湯佐脫口秀節目當笨蛋,也一樣可以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