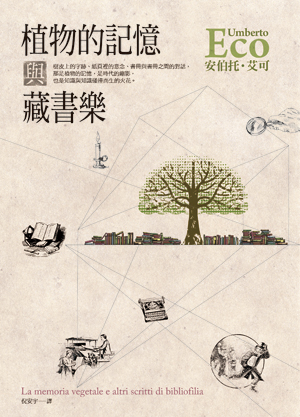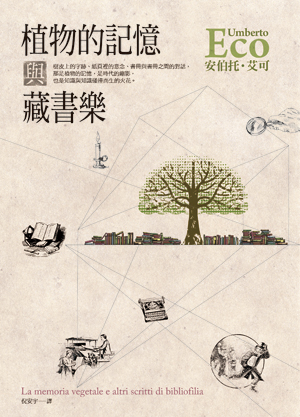內容試閱
二,偶爾有人會說今天閱讀的人口減少了,說年輕人不看書,說我們進入了某位美國評論家所稱讀寫能力下降的年代。我不知道,今天大家的確看很多電視,只看電視是有風險的,正如同喜歡在體內注射有毒物質也是有風險的:但不容否認的是,我們這個年代的印刷量達到顛峰,書店到處林立,跟夜店一樣擠滿了年輕人,即便不買書,也在翻書、看書或詢問書。
書也面臨的問題是,出版數量龐大,選擇困難,不知從何辨別。這很正常,植物記憶普及就跟民主一樣是有缺點的,因為要確保所有人都可以發言,包括言語空洞、甚至言語粗鄙的人都得讓他們講話。沒錯,問題在於要學會選擇,如果不懂得選擇,站在書本前面就如富內斯面對無窮盡的感知一樣:如果一切都看似值得記憶,其實毫無價值可言,值得遺忘。
要如何學會選擇呢?舉個例子,我們可以自問,現在準備要拿起來的那本書會不會在看過之後就被我們扔掉。你們會說,還沒有看過無法知道。那麼,如果在看了兩、三本書之後,我們發現不想留下來,或許就該重新審視選書的準則。看完一本書之後把它扔掉,跟剛和一個人發生性關係就不想再看到他是一樣的。會有這種感覺,表示那是生理需求,不是愛。我們其實需要跟人生中的這些書建立起愛戀關係。如果成功,表示那些書禁得起各種考驗,每一次重讀都能給我們不同的揭示。我說那是一種愛戀關係,是因為只有在相愛狀態中的戀人才會帶著喜悅,覺得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當你覺得每一次都像是第二次的時候,就差不多要準備離婚,或就書而言,是準備要被丟進垃圾桶了。
可捨可留,表示書是一個物,被愛不僅是因為內涵,也是因為外表。這場演講是由一群藏書迷組成的協會主辦,藏書迷也會因為一本書的排版、紙張、裝幀是否精美而收藏書。其中不乏本末倒置者沉迷在一本書的視覺、觸感中,如果書邊尚未裁切,他們就不將書頁割開,以免降低其商業價值。不過,每一種熱情都會衍生出專屬的戀物癖。藏書迷會渴望擁有同一本書的三個不同版本並沒有錯,因為各個版本之間的差異會影響我們閱讀的意願。我有一個朋友,是位詩人,偶爾會找到其他義大利詩人的古版書,他再三告訴我閱讀今天的但丁《神曲》口袋版跟閱讀阿蒂納版是截然不同的樂趣。很多人找到當代作家的初版作品,在閱讀那些曾經被最初的讀者閱讀過的文字時,也會有一種異樣的悸動。書除了原先要傳遞的記憶外,還有它屬於物的實體記憶,以及浸淫多年的歷史香氣。
一般咸認為藏書這個癖好所費不貲,如果我們想要擁有一本由古騰堡印刷、最早的四十二行《聖經》,至少要準備七十億。我說至少,是因為市面上僅有幾本流通(其他都由公立圖書館視如珍寶,妥善收藏),而其中一本在兩年前就是以這個金額賣出,如果買主今天出讓,可能會開出雙倍價格。不過想加入藏書行列,未必需要富有。
大家或許不知道,今天大約只要五萬里拉,就可以買到某些十六世紀的圖書,只要少去餐廳兩次或少抽兩條菸就可以存下這些錢。古版書未必昂貴,有些二十年前印刷的熱門藏書反而是天價。用買一雙Timberland的錢,就可以享受書架上有一本美麗對開本的喜悅,你可以觸摸羊皮紙裝幀、感受紙張質感,甚至藉由斑點、潮溼水漬、蠹蟲辛勤工作挖掘上百頁留下跟雪花同樣美麗的痕跡來體會時間的流逝和外在環境的變遷。即便是殘缺不全的一本書,往往也可以說出感人肺腑的故事:為了躲避嚴格的審查制度將出版社的名字刪掉,某些書頁被有意見的讀者或過於謹慎的圖書管理員撕下,因為印刷時用了廉價材料導致紙張變紅,長時間囤放在某個修道院地窖而留下印記,簽名、批註、畫重點,訴說的是兩、三百年來不同主人的故事……
無須追求古書,可以從蒐集近兩個世紀的圖書開始,在舊書攤、二手市集搜尋初版書和毛邊書。大多數人的荷包都可以負擔這樣的遊戲,而且樂趣不僅限於找到,而是尋找的過程,啟動嗅覺、翻找、在脆弱的小樓梯上攀爬,挖出舊貨商在多年沒有清撢灰塵的最後一格層架上究竟有些什麼。
收藏書,即便是少量的,即便是「當代收藏」,都是一種善舉,我是從關心生態的角度出發,因為需要我們拯救的不只是鯨魚、地中海僧海豹和馬西干棕熊,還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