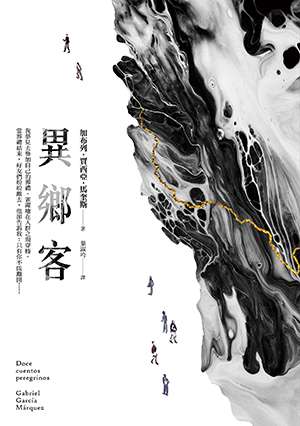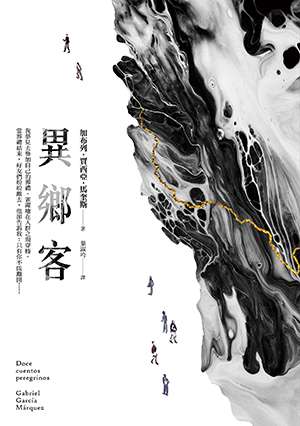內容試閱
【導讀】
與死亡同樣珍貴
作家/胡淑雯
我有兩次出國小住的經驗,一次八個月,去洛杉磯,另一次三個月,去巴黎,在斤斤計較行李負重之餘,兩次都帶了馬奎斯的《異鄉客》。這本書豐饒的程度,與它的輕盈同步,像某種不存在的終極行李箱,在極小值裡塞入極大值,適合所有的遠方。我將它擺在床邊,每晚睡前讀幾頁,也經常讀給床伴聽。這些故事怎麼也讀不爛,飽滿、精緻、蒼涼,時而幽默到奢侈的程度。我記得初讀的震撼,也喜愛那熟悉過後依舊不死的新鮮感。
新鮮,如〈聖女〉一篇中,死了十一年,體膚依舊完好如初的七歲女孩,手握的玫瑰聞起來,跟入殮時同樣芬芳。她跟那些「看起來就像死人」的木乃伊完全不在同一層次,張著孩童溫柔的雙眼,「彷彿正從死亡的世界望向我們」。然而那種凝視,對人間來說,未免太過古老深邃,令人難以消受。卻也正是這一份「難」,開啟了小說的美學時空。馬奎斯說,書中的故事皆以新聞實錄為根據,這說法,反而讓小說的魔力更強,以致,當我們得知女孩的身體「沒有重量」,瞬間就接受了這不可能的神蹟。同樣,當書中某個角色說,「這不能當電影題材,沒有人會相信的。」這句話說的正是,這是一則真人真事。真實,與真實的保證,讓想像力更敢於衝撞,衝撞文明與理性。
這本書從筆記階段到完稿,相隔了二十年。馬奎斯為了查核自己的記憶,在付印前重回歐洲,重新認識巴賽隆納、羅馬、巴黎、日內瓦,卻發現自己對記憶沒有一點把握。然而,在「假記憶」強而有力的自信底下,馬奎斯得到某種「唯歲月流逝」才能獲得的自由。旅程後,他花了八個月的時間瘋狂將每一個故事從頭改寫,於是我們得到了這本一九九二年問世的短篇集,在馬奎斯獲得諾貝爾獎十年之後,再一次,於這本小說中,經歷了「魔幻寫實」的力量。但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馬奎斯的提醒:你們所謂的魔幻,是我們的寫實,「魔幻寫實」這個字眼,反而加深了「拉丁美洲的孤寂」。
此刻,在我寫作當下的二○二○年,是一個聖人匱乏,甚至,不歡迎聖人的時代。小說中,那個一九七○年代的歐洲,管理神聖事務的教會,已演化出一套世俗的官僚作業。〈聖女〉中,女孩的父親第一次也唯一一次離家,就是天殺的遠途,從哥倫比亞安地斯山區的小村莊,來到天主教的心臟羅馬,這趟為女兒「封聖」的旅程,在不斷碰壁的枯耗中已漫漫度過二十二年。教宗都已經死掉五個了,「聖者」還在等待。那等待的聖者,是沒有重量的女孩,也是那艱苦卓絕的父親,一個從不抱怨的鄉下人。在官僚的拖延中,一種神聖性死亡了,另一種神聖性誕生了。然而在後續的短篇〈我只是來借個電話〉與〈雪地上的血跡〉,官僚殺死的是世俗,是那名之為愛情的,無上世俗的幸福。
死亡,是這本小說的核心。我們在十二篇作品中經歷了十二種死亡。北風可以殺人。燈光可以像水一樣積蓄、淹高,將小孩溺死。絕色美女在飛機上睡死,令身旁的「我」看得入迷深怕失去了自己,以致「我唯一的願望是看見她醒著,如此,我才能恢復自由。」獨居的老娼瑪莉亞,在夢兆中預見了自己的死訊,她積極辦理後事,訓練小狗替自己哭墓、認墓、認路、等紅綠燈、跟著公車路線往返來去……每一種能力都需要反覆訓練、反覆排演、反覆驗收,她幾乎就要成功了,夢中的場景即將兌現,那攜帶著暴力暗示的男人果然出現了,但是,尾隨在她身後的似乎不是死神,而是不可能的青春。當年輕的男人問她,「我可以上去嗎?」她說,「我可不容許你這樣嘲弄我。」這一刻,她發現自己漫長的、有過無數男人的一生,從未有過如此害怕做決定的時刻。她開始爬樓梯,感覺膝蓋發抖,無法呼吸,以為這本是死亡當下的驚恐,心臟緊張得簡直要爆裂,「老天哪,」她驚愕地自言自語,「所以這根本不是死亡啊。」我尤其鍾愛以下這段:當男人再問一次,「我可以上去嗎?」她尊嚴地改用西班牙語,好確保對方聽得懂,而她的回答是:「隨便你。」真是太幽默了我的天啊。
青春之後還有青春。退休之後還有事業。比如我最喜愛的開篇〈一路順風,總統先生〉,政變後流亡的前總統,在日內瓦等死,被同鄉的救護車司機盯上了,本是為了拉關係、撈好處,推銷全套的喪禮服務,包括屍體防腐與運送回國。但隨著雙方關係的進展,司機與其太太自以為機關算盡,做出的盡是倒貼幫助老總統的事。終於,老總統回家了,不料身體卻沒有依照咖啡渣的諭示走向衰亡。一年多以後的七十五歲那年,他決定重返政壇,雖說「每個人都跟我一樣:獨占我們配不上的榮譽,不知該怎麼做好這份工作。他們有些人只追求權力,但是大多數人要的更少:只求一份工作。」貌似高貴的作為,背後的動機往往並不高貴。然而這不可愛嗎?一如那對司機夫妻,出於卑瑣的理由,做出了高貴的事。在目送老總統驚險地在火車最後一節的敞篷區,保持即將墜車卻始終不墜的平衡,太太含淚勉強笑了出來,說,「天哪,那個男人怎麼也死不了!」
這篇小說的靈感,據馬奎斯說,源自他親身的夢。在夢中,他參加了自己的葬禮。摯愛的朋友們都來了,個個都身穿葬服,心情卻像在過節,他們因為相聚而感到幸福。一個人的葬亡,是一群人珍貴的相聚。葬禮結束,馬奎斯想要跟朋友們一起離開,但是不行,「唯有你不能走,」夢中的朋友這樣果斷地阻止他。
只有他不能走。
只有我不能走。
馬奎斯說,這時我才明白,死亡的意思是,你再也不能跟朋友在一起了。
原來這就是流亡,就是離散。馬奎斯知道自己要寫什麼了。
在這本小說中,我們讀到拉美人在歐洲的離散。並且在多年後的今天,也許,讀到了香港人的離散,圖博(藏人)的離散,以及,我們自身的離散。這本書我已讀過許多遍,最近再讀一遍,竟一再想起台灣的老政治犯,與政治犯的葬禮。他們跟馬奎斯的夢中同樣,因為一位老難友的葬亡,而得到難能可貴的、相聚的機會。而這樣的相聚,每發生一次就少一次。每一次都跟最後一次同樣珍貴。每一次都跟死亡同樣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