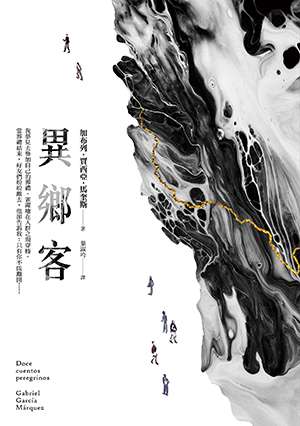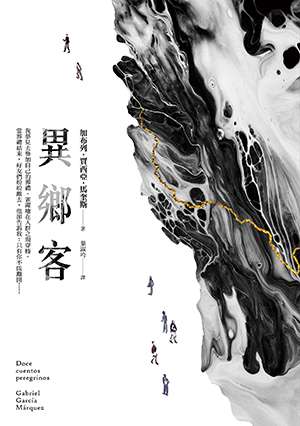內容試閱
「我只是來借個電話。」
春天一個下雨的午後,瑪莉亞.德拉露茲.塞萬提斯獨自開著租來的車前往巴塞隆納,就在路經莫內格羅斯沙漠時遇上車子拋錨。她是個二十七歲的墨西哥女郎,長得很美,個性認真,幾年前當過綜藝節目演員,還小有名聲。她嫁給一個秀場魔術師,這一天她拜訪完幾個住在薩拉戈薩的親戚後,正是要去跟他會合。她在暴雨中拚命地向飛快駛過的汽車和卡車求救,一個小時過後,總算有個開著破巴士的司機同情她。他告訴她車子不會開太遠。
「沒關係。」瑪莉亞說。「我只需要電話。」
沒錯,她只需要通知丈夫她沒辦法在晚上七點前趕回家。她淋成落湯雞,身上穿著一件學生外套和一雙四月穿的海灘鞋,她還在為倒楣遭遇驚慌失措,竟忘了拔走汽車的鑰匙。司機旁有個女人,看起來像軍人,但是散發甜美的氣質,她遞過來一條毛巾和一條毛毯,讓出旁邊一個空位給她。瑪莉亞大略擦乾身體,坐下來裹上毯子,她想點根菸,但是火柴淋溼了。身邊的女人借她火,並向她要一根剩下的少數沒溼的香菸。她們一起抽菸,瑪莉亞耐不住焦躁,她發洩的聲音還壓過了雨聲和巴士的喀啦聲。女人舉起食指壓住嘴脣,打斷她的話。
「她們睡著了。」她低聲說。
瑪莉亞轉過頭去,看見巴士載著幾個年紀不明和狀況不一的女人,她們跟她一樣裹著一條毯子,全都睡著。瑪莉亞感染了她們的安靜,在座位上蜷曲一團,跟著雨聲睡去。當她睜開眼睛時,天色已黑,暴雨減弱為冰冷的溼氣。她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也不知道自己在世界的哪個角落。她旁邊的女人一臉警覺。
「我們在哪裡?」瑪莉亞問。
「我們到了。」女人回答。
巴士開進一個石磚地庭院,裡頭有一棟陰森森的龐然建築,看似森林深處的古老修道院,四周圍繞著參天樹木。庭院點著一盞燈,車上的女乘客在黯淡的燈光下靜止不動,直到軍人樣貌的女人像是在幼兒園,用一連串簡單的命令要她們下車。她們全都上年紀,緩緩地走在昏暗的庭院,像是夢裡的幽影。瑪莉亞最後一個下車,她想她們可能都是修女。但又不太確定,因為她看見巴士門口有好幾個穿制服的女人接她們,拿毛毯蓋她們的頭以免淋溼,要她們排成一排,以有力的節奏擊掌指示她們,卻不跟她們說話。瑪莉亞跟坐在她身邊的女人道別,想把毯子還給她,但是對方要她拿毯子蓋住頭部走過庭院,在門房那裡歸還。
「這裡有電話嗎?」瑪莉亞問。
「當然有。」女人說。「裡面會有人告訴妳在哪裡。」
她又要了一根菸,瑪莉亞把淋溼的菸盒給她。「路上會乾。」她說。女人站在踏腳板上向她揮手說再見,然後幾乎是大喊地說:「祝妳好運。」巴士開走,沒多給她時間回答。
瑪莉亞奔向建築物入口。有個女守衛用力拍手想擋下她,可最後不得不加上一句大喊:「我說停下來!」瑪莉亞掀起毯子一瞧,迎上一雙冰冷的眼睛,看見對方舉起食指要求她排隊,不得違抗。她乖乖聽話。到了建築物的門廳,她離開隊伍問門房哪裡有電話。其中一名女守衛拍拍她的後背,要她歸隊,並用非常甜美的口吻說:
「美麗的小姐,走這邊,這邊有電話。」
瑪莉亞跟著其他女人沿著一條陰暗的走廊走到盡頭,進入一間集體宿舍,裡面有幾位女守衛向她們收回毯子,接著分配床鋪。瑪莉亞感覺其中有個女人似乎位階比較高,也比較有人情味,她拿著名單跟剛到的人逐一比對縫在她們胸衣上的名牌。當她來到瑪莉亞面前,很驚訝地發現她竟然沒有識別名牌。
「我只是來借個電話。」瑪莉亞跟她說。
她很快地解釋她的汽車在公路上拋錨。她的丈夫是專門在慶祝會表演的魔術師,他們今晚有三場表演,工作到午夜才會結束,他現在正在巴塞隆納等她,她想要通知丈夫來不及陪他一起表演。這時已經快七點。他再過十分鐘就要出門,她怕他會因為她遲遲未歸而取消所有表演。女守衛似乎相當仔細聽她說。
「妳叫什麼名字?」
瑪莉亞鬆了一口氣,說出她的名字,女人將名單檢查好幾遍,就是沒找到一樣的名字。她心生警覺,問了另一個女守衛,可是後者聳聳肩,無話可說。
「我只是來借個電話。」瑪莉亞說。
「好吧,親愛的。」女主管說,接著帶她到她的床位,她的動作太過溫柔,看起來虛假而不真實。「如果妳乖乖聽話,明天想打電話給誰都可以。但是現在不行,要等到明天。」
這時瑪莉亞的腦海閃過一個想法,於是明白巴士上的女人的動作為什麼像是在水族缸裡。她們那麼安靜,其實是注射鎮靜劑,而這座黑影幢幢的宮殿、方石厚牆和冰冷的樓梯,其實是一間收容精神病患的醫院。她驚慌不已,拔腿逃出宿舍,但還來不及抵達大門邊,一位穿著連身工作服的魁梧女守衛一把抓住她,以無敵的擒拿術將她制伏在地。瑪莉亞嚇得動彈不得,斜眼看她。
「看在天主的分上,」她說。「我以我死去的母親發誓,我只是來借個電話而已。」
瑪莉亞只消看到她的臉,就明白任何哀求都無法打動這個穿連身工作服的女瘋子,而她因為力大無窮有個女力士的封號。她負責所有棘手病患,那隻北極熊般強壯的手臂很容易失手殺人,還曾因此勒死兩個女病患。第一個病患以證實是意外事件收場;第二個就沒那麼簡單,女力士遭到懲戒,和警告下一次就會深入調查。聽說她是出身某個名門望族的家族之恥,曾在西班牙的好幾間療養院工作,都發生過不明不白的意外事件。
第一晚,她們給瑪莉亞注射安眠藥睡覺。天亮前,她犯了菸癮醒來,發現手腕跟腳踝被綁在床鋪的棒條上。她尖聲呼叫,但是沒人理會。到了早上,當她在巴塞隆納的丈夫遍尋不著她的下落,她卻深陷悲慘的困境而不省人事,療養院的人不得不把她送到醫療室。
她不知道自己過了多久才甦醒。但這時她覺得世界充滿愛,她的床前有位高大的老人,他踮腳走路,帶著安撫人的笑容,兩招厲害的催眠術就讓她重新找回活著的幸福感。他是這間療養院的院長。
瑪莉亞沒說什麼,甚至沒打招呼,只是先跟他要根菸。他遞給她一根點燃的菸,和一整包幾乎全滿的菸,瑪莉亞不禁哽咽出聲。
「趁現在想哭盡量哭。」醫生用催眠的口吻對她說。「眼淚是最佳良藥。」
瑪莉亞放下羞恥盡情發洩,即使是跟逢場作戲的情人在歡愛過後感到心情煩悶,她也不曾這麼做到。醫生一邊聽她說,一邊用手指整理她的頭髮,替她整理枕頭讓她呼吸順暢,以一種她做夢都不曾想過的智慧和溫柔,引導她走出不安的迷宮。真是不可思議,這是她這輩子第一次感覺有個男人了解她,全心全意聽她傾訴,不求跟她上床做為回報。她發洩了漫長的一個小時,完畢之後,便跟他要求打電話給丈夫。
這時醫生重新拿出他的位階的權威。「還不行,女王。」他對她說,並用一種她從未感受過的溫柔輕拍她的臉頰。「一切都有它的時序。」他站在門口,像個主教對她祝福,自此消失無蹤。
「相信我。」臨走前他對她說。
這天下午,他們把瑪莉亞編入住院名單,附上一組病歷號碼,和幾句對她的背景和身分之謎的輕描淡寫。院長在一旁空白處親筆註記診斷:躁鬱。
正如瑪莉亞預測,她的丈夫多等了半個小時後,離開他們在奧爾塔街區的公寓,打算完成三場表演。他們的婚姻生活很自由,但這是結婚近兩年來,她第一次沒準時到家,他猜測她的晚歸應該是遇上週末肆虐外省的暴雨。出門前,他在門上釘上字條,交代晚上的表演行程。
在第一場慶祝會上,所有的小孩都扮成袋鼠,他少了她當助手,只得放棄精采的隱形魚魔術表演。第二場表演是在一個坐輪椅的九十三歲老婆婆家中,她相當自豪三十年來的生日都邀請不同的魔術師來表演。他很氣瑪莉亞遲到,連最簡單的魔術都無法好好專心表演。第三個工作是每晚在蘭布拉大道的音樂咖啡館,他懶洋洋地表演給一群不相信魔術,所以不信親眼所見的法國觀光客觀看。每場表演結束,他都打電話回家,希望瑪莉亞會接電話,但不抱太大幻想。到了最後一場表演,他再也忍不住擔心她可能發生什麼意外。
回家途中,他開著改造成表演用的小卡車經過格拉西亞大道,在路旁的棕櫚樹看見絢爛春光,他悲傷想著失去瑪莉亞,這座城市會變成什麼樣貌,不禁身體發抖。當他發現字條還在門上,最後一絲希望破滅。他太過生氣,還因此忘記餵貓。
現在寫這個故事,我才發現我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在巴塞隆納我們只知道他的藝名:魔術師沙度諾。他個性古怪,社交能力無可救藥笨拙,但是瑪莉亞擁有他欠缺的圓滑和風趣。是她牽著他的手走進這個充滿神秘的社區,在這裡沒有人會在大半夜打電話詢問妻子的下落。沙度諾剛搬來時曾這麼做,如今他不願回想那段過往。因此,這一晚他僅僅打電話到薩拉戈薩,一個半夢半醒的老祖母完全沒發現什麼不對,只是回答他瑪莉亞吃完午飯後就離開。他只在天亮時睡了一個小時。他迷迷糊糊,夢見瑪莉亞穿著一件血跡斑斑的破新娘禮服,他驚醒過來,相信她又再次丟下他,這一次一去不回,丟下他在沒有她的茫茫世界……
---
當靈魂被貼上了不被信任的標籤,當不知身在何處的驚恐在心中迴盪,瑪莉亞究竟能不能再重新回到她的「正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