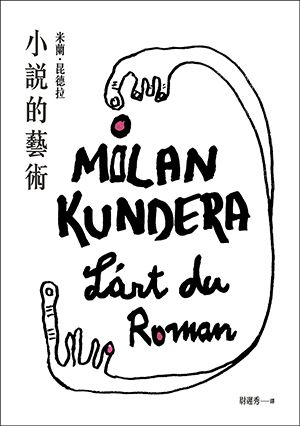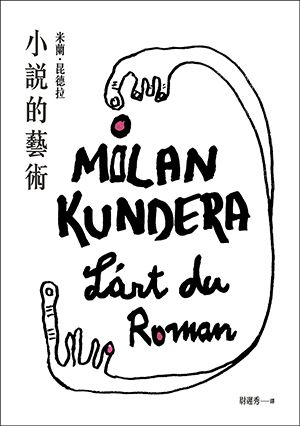內容試閱
以色列頒發的最重要獎項保留給國際文學,在我看來,這並非偶然的現象,而是悠久的傳統。事實上,這是因為偉大的猶太賢人志士,他們遠離了自己原初的土地,在超越了國族主義激情的環境下成長,他們始終對於超越國族的歐洲展現著一種特殊的感受性,他們將歐洲想像為文化,而非領土。儘管歐洲曾以悲劇讓猶太人陷入了絕望之境,可是在此之後,猶太人卻對這歐洲的世界主義忠誠依舊,而他們終於失而復得的小小祖國以色列,在我眼裡,則有如歐洲真正的心臟,這個奇異的心臟,長在身體之外。
今天,我帶著極為激動的心情來領獎,領取這個帶著耶路撒冷之名,帶著猶太人偉大的世界主義精神印記的獎。我以小說家的身分得到這個獎。我強調,我說的是小說家,不是作家。依照福樓拜的說法,小說家是想要消失在自己作品之後的人。消失在自己作品之後,意思是要放棄公眾人物的角色。這並非易事,今天,無論任何雞毛蒜皮的小事都得通過大眾傳媒那座照亮得令人無法忍受的舞臺,這跟福樓拜的意願完全背道而馳,結果是作品消失在作者的形象之後。在這種處境裡,沒有人能夠全身而退,福樓拜的見解在我看來幾乎是一種預警:小說家一旦接受了公眾人物的角色,就會讓自己的作品陷入險境,作品有可能被當作一條闌尾,附庸於他的所作所為、他的公開發言、他所採取的立場。然而,小說家並不是任何人的代言人,我要將這個論點一直推到小說家甚至不是自己想法的代言人。托爾斯泰在寫《安娜.卡列尼娜》的初稿時,安娜是個非常令人反感的女人,而她悲劇性的下場不過是罪有應得罷了。小說最後的定稿卻大異其趣,但我不相信托爾斯泰在這段期間改變了他的道德觀,我會說,應該是在寫作的時候,他聆聽著另一個聲音,這聲音並非他個人的道德信念。他聆聽的聲音,我喜歡稱之為小說的智慧。所有真正的小說家都聆聽這超越個人的智慧,這說明了偉大的小說總是比它們的作者稍微聰明一點。比自己作品聰明的小說家都應該改行。
但是這智慧究竟是什麼?小說又是什麼?有一句猶太諺語很令人讚嘆: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這個警句帶給我一些啟發,我常想像有一天弗朗索瓦.拉伯雷聽見上帝的笑聲,於是歐洲第一部偉大的小說就這樣誕生了。我喜歡把小說藝術來到世界想作是上帝笑聲的回音。
但是為什麼上帝看著人類思考就要發笑呢?因為人在思考而真理卻逃離他。因為人們越思考,一個人的真理就會離另一個人的真理更遠。而最終的原因,是因為人從來不是他自己所想像的那樣。正是在現代的黎明之際,從中世紀走出來的人,顯露了這個基本處境:唐吉訶德思考,桑喬思考,不僅是世界的真理躲開了他們,連屬於他們自我的真理都避開了。最早期的幾位歐洲小說家看到也捕捉到人的這個新處境,並且在其上建立了一門新的藝術,那就是小說的藝術。
弗朗索瓦.拉伯雷發明了許多新詞,後來這些詞都進入了法語和其他語言之中,但是其中有一個詞被遺忘了,或許我們會為此感到遺憾。這個詞就是扼結樂思忒(agélaste);它是從希臘文來的,意思是:不笑的人,沒有幽默感的人。拉伯雷討厭扼結樂思忒。他對這種人感到害怕。他抱怨說這些扼結樂思忒「對他如此殘酷」,害他幾乎要停止寫作,永遠停止。
小說家和扼結樂思忒之間永無寧日。這些扼結樂思忒從來不曾聽到上帝的笑聲,他們相信真理是清晰的,他們相信所有人的想法都應該相同,他們相信自己和心裡所想的自己一模一樣。然而人之所以成為個人,恰恰是因為他失去了對於真理的確信以及其他人的一致共識。小說,是屬於個人的想像天堂。在這片領土上,沒有人是真理的占有者,安娜不是,卡列寧也不是,在這裡,所有人都有權被人理解,安娜有權,卡列寧也有。
在《巨人傳》的《第三書》裡,歐洲第一個偉大的小說人物巴汝奇(Panurge)為了一個問題感到苦惱:他該不該結婚?他請教了醫生、算命師、教授、詩人、哲學家,這些人輪番引述希波克拉提(Hippocrate)、亞里斯多德(Aristote)、荷馬、赫拉克利特(Héraclite)、柏拉圖的話。但是在這占據了整本書的浩瀚博學研究之後,巴汝奇始終不知道他是不是應該結婚。我們這些讀者呢,我們也不知道,但是相對的,我們卻從所有可能的角度探索了不知該不該結婚的人既可笑又基本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