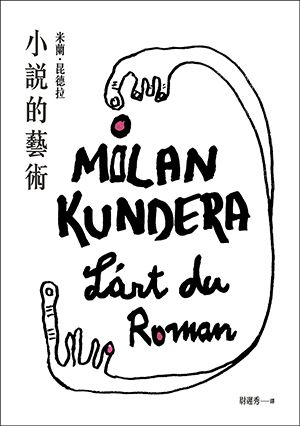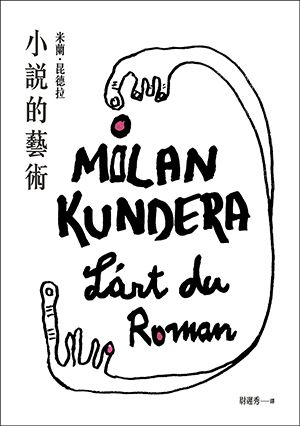內容試閱
拉伯雷的旁徵博引如此大氣,但是和笛卡兒的博學相比,還有另一種意義。小說的智慧和哲學的智慧是不同的。小說並非誕生於理論的精神,而是誕生於幽默的精神。歐洲的一個失敗,就在於它從來不曾理解歐洲最偉大的藝術——小說;歐洲不理解小說的精神,不理解小說無邊無際的認識與發現,也不理解小說歷史的自主性。受到上帝笑聲啟發的藝術,其本質並非屈從於意識形態的確信態度,而是去反對它。跟佩涅洛佩一樣,這門藝術在夜裡拆散了神學家、哲學家、學者在前一天編織的掛毯。
近來,人們習於談論十八世紀的壞處,甚至一直談到這個陳腔濫調:俄羅斯極權主義的不幸,是歐洲的作品,尤其是啟蒙時代無神論的理性主義,因為它信仰著理性至高無上的權力。那些人把伏爾泰說成該為古拉格負責,我不覺得自己有能力同他們論戰。相反的,我覺得自己有能力說:十八世紀不只是盧梭、伏爾泰、霍爾巴赫(Holbach)的時代,也是(或者該說,尤其是!)菲爾丁、斯特恩、歌德、拉克羅的時代。
這個時代所有的小說,我最喜歡的是勞倫斯.斯特恩的《崔斯川.山迪》。這是一部奇怪的小說。斯特恩追憶著崔斯川被孕育的那個夜晚,以此開展這部小說,但他才剛開始說這件事,另一個想法隨即吸引了他,而這個想法又通過自由聯想喚起了另一個反思,接著是另一個小故事,結果是一次又一次的離題,而小說的主人翁崔斯川,則在長達一百多頁的篇幅裡被遺忘了。這種怪誕的小說寫法或許會讓人看作一種單純的形式遊戲。然而,在藝術裡,形式永遠不只是形式。每一部小說,不管願不願意,它都要提供一個答案給這個問題:什麼是人的存在?它的詩意又在哪裡?斯特恩的同代作家,像是菲爾丁等人,他們特別懂得品味行動與冒險的非凡魅力。但是斯特恩小說裡暗示的答案是不一樣的:詩意,照他的說法,不在行動裡,而是在行動的中斷裡。
或許,小說與哲學之間,一場偉大的對話間接地在這裡發生了。十八世紀的理性主義建築在萊布尼茲著名的句子上:nihil est sine ratione.——沒有任何存在之物不具理性。科學受到這個信念的刺激,熱烈地檢視著一切事物的為什麼,好讓一切存在之物看起來都是可以解釋的,所以,也是可以計算的。人,希望自己的生命擁有某種意義,他會放棄每一個沒有原因和目的的行為。所有的傳記都是如此寫下的。生命看起來像是一道因、果、成、敗的明亮軌跡,人則是一邊以焦急的目光緊盯著自己行為的因果鏈,一邊繼續加速向死亡狂奔而去。
世界退縮成一連串事件的接續交替,面對這樣的簡化,斯特恩的小說以其唯一的形式肯定了:詩意不在行動裡,而是在行動中止之處;在那兒,因果之間的橋梁被摧毀,思想在無所事事的甜美自由裡遊蕩。存在的詩意,斯特恩說,它處在離題之中。它在無法計算的事物之中。它在因果關係的另一邊。它sine ratione——不具理性。它在萊布尼茲的句子的另一邊。
我們不能僅僅根據思想、理論概念就來評價一個世紀的精神,卻不去注意藝術(尤其是小說)。十九世紀發明了蒸氣火車頭,黑格爾也確信自己已經掌握到世界歷史的精神。福樓拜發現了愚蠢。我敢說,這個以科學理性而如此自傲的世紀,它最偉大的發現就在這裡。
當然,即使在福樓拜以前,人們也已經知道了愚蠢的存在,但是人們理解的方式有一點不同:愚蠢被視作一種單純的缺乏知識,一種可以經由教育矯正的缺點。但是,在福樓拜的小說裡,愚蠢是跟人的存在密不可分的一個維度。它伴隨著可憐的艾瑪度日,直到她做愛的床笫,直到她臨終的病榻,病榻旁,還有兩個嚇人的扼結樂思忒,奧默(Homais)和布尼賢(Bournisien)在那兒交流著他們漫長的蠢話,彷彿悼詞似的。但是在福樓拜對愚蠢的看法裡,最嚇人、最令人憤慨的是:愚蠢在科學、技術、進步、現代性的面前並未被抹去身影,相反的,世界在進步,愚蠢也跟著進步!
福樓拜懷抱著一股淘氣的激情,蒐集了他身邊的人們為了表現聰明、跟得上潮流的樣子,而對他說出的刻板用語。他把這些用語編成了一本著名的《既成思想辭典》(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我們就借用這個書名來說吧:現代的愚蠢不是意謂著無知,而是對於既成思想的不思考。對於世界的未來,福樓拜的發現比起馬克思(Marx)或弗洛伊德那些震撼人心的思想更加重要。因為我們可以想像未來沒有階級鬥爭,沒有心理分析,卻不可能沒有既成思想無可抗拒的潮湧,既成思想被輸入電腦,被大眾傳播媒體廣為宣傳,很可能即將成為一股粉碎一切原創與個人思維的力量,因而扼殺現代歐洲文化的本質。
福樓拜想像出他的艾瑪.包法利,之後約莫八十年,在我們這個世紀的三○年代,有一位偉大的小說家赫曼.布羅赫談到現代小說反對媚俗潮流的壯烈努力,最後卻被媚俗擊垮。「媚俗」這個詞指稱的態度,是想要不惜任何代價討好大多數人。為了討好,就得去確定什麼是人人想聽的話,就得去為既成思想服務。媚俗,就是將既成思想的愚蠢轉譯成美和感動的語言。媚俗從我們身上淘出了同情的淚水,為了我們自己,為了我們所思所感的平庸事物。五十年後的今天,布羅赫的句子變得越來越真確。由於討好並且贏得大多數人的注意是迫切必要的,大眾傳播的美學無可避免地成了媚俗的美學;漸漸地,大眾傳播全面擁抱、滲透著我們的生活,媚俗變成我們日常生活的美學與道德。現代主義直到最近某個時期都還意謂著不因循隨俗的一種反叛,對抗著既成思想與媚俗。今天,現代性卻與大眾媒體無邊無際的生命力混在一起,「成為現代的」意謂著一種狂熱的努力,為的是要跟上時代,因循隨俗,比最因循隨俗的人還要因循隨俗。現代性穿上了媚俗的長袍。
扼結樂思忒、對於既成思想的不思考、媚俗,這個三頭怪物,是作為上帝笑聲而生的藝術唯一且同一的敵人。這門藝術知道如何創造迷人的想像空間,在其中,沒有人是真理的占有者,每個人都有權被理解。這個想像空間和現代歐洲一同誕生,它是歐洲的形象,或者,至少是我們夢想的歐洲。夢想屢屢遭到背叛,但卻依然強大,足以將我們全部團結在遠遠超越我們小小歐陸的友愛之中。然而我們知道,個人受到尊重的這個世界(小說的想像世界、歐洲的真實世界)是脆弱、稍縱即逝的。我們看到扼結樂思忒的大軍出現在地平線上,窺伺著我們。恰恰是在這場沒有宣戰的永恆戰爭時代裡,在這個命運如此戲劇化、如此殘酷的城市裡,我決定只談論小說。或許各位也明白,這並不是我在逃避所謂嚴重的問題。因為,儘管歐洲文化在今天似乎受到威脅,受到來自外部和內部的威脅——在它最珍貴之處:尊重個人、尊重個人原創的思想、尊重個人不可侵犯的隱私權——但是,歐洲精神的這種珍貴本質,卻宛如存放在小說歷史的銀匣子裡,存放在小說的智慧裡。在這篇謝辭裡,我要致敬的對象正是這小說的智慧。可我這會兒也該打住了。我剛剛一直忘了,上帝看見我在思考,祂就會發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