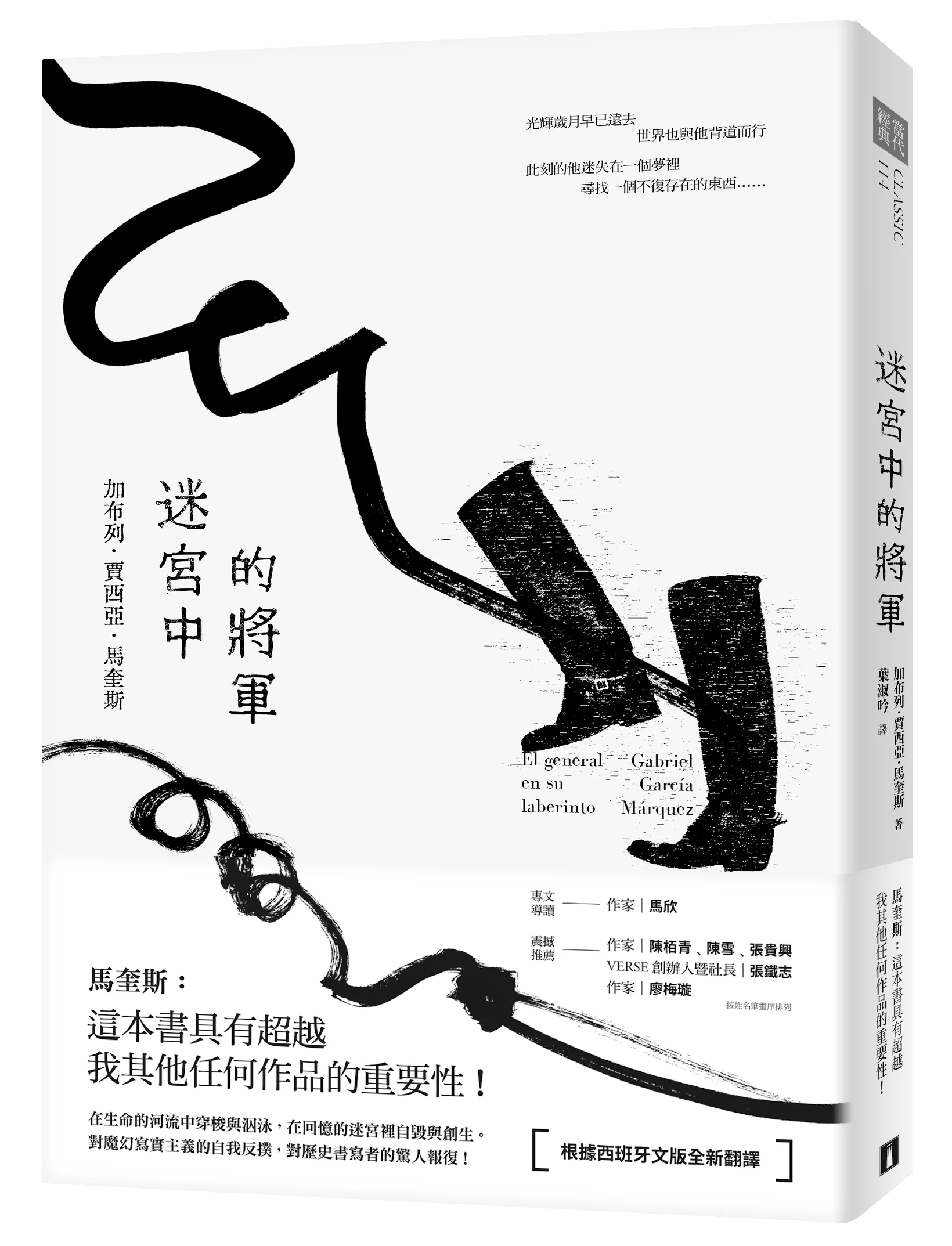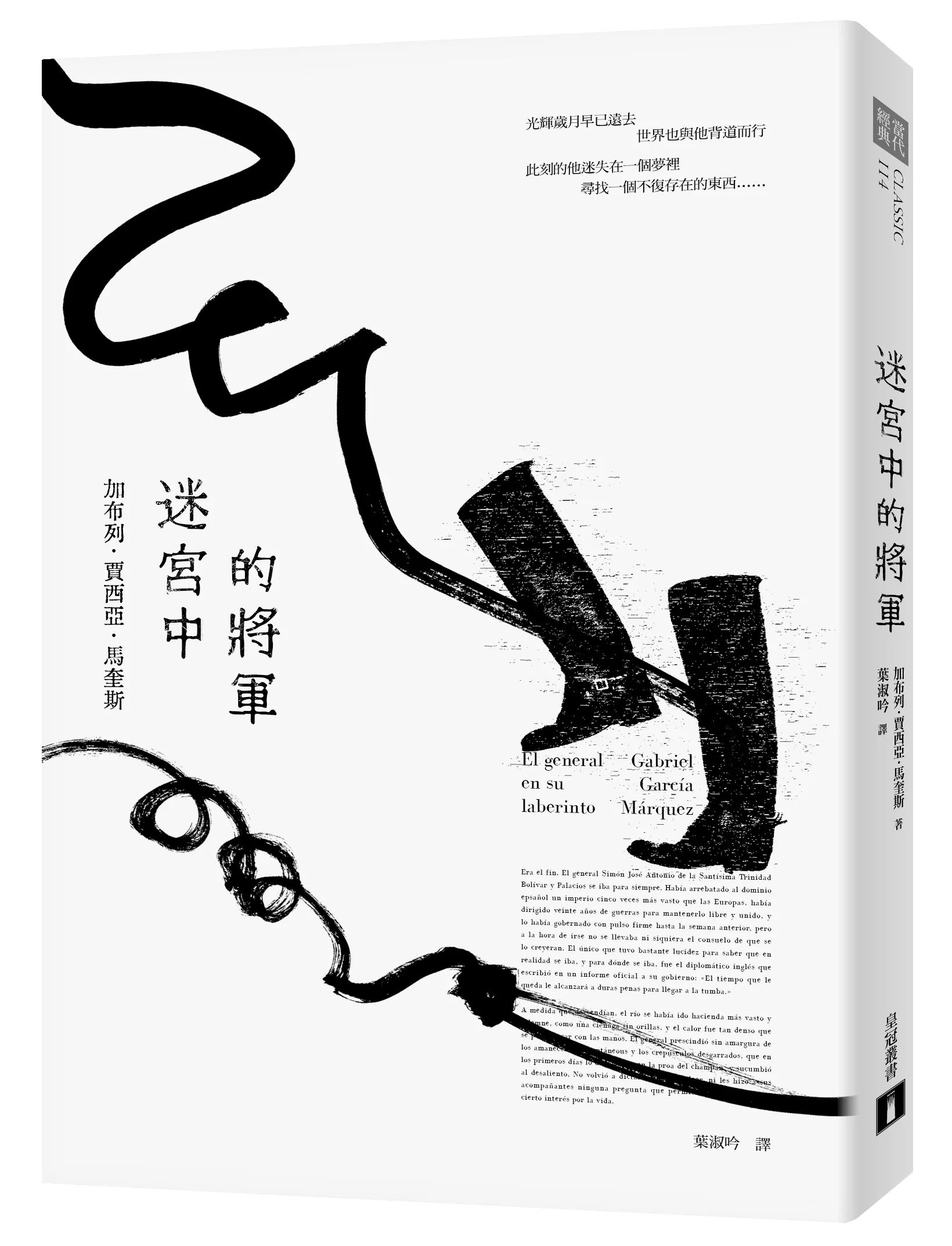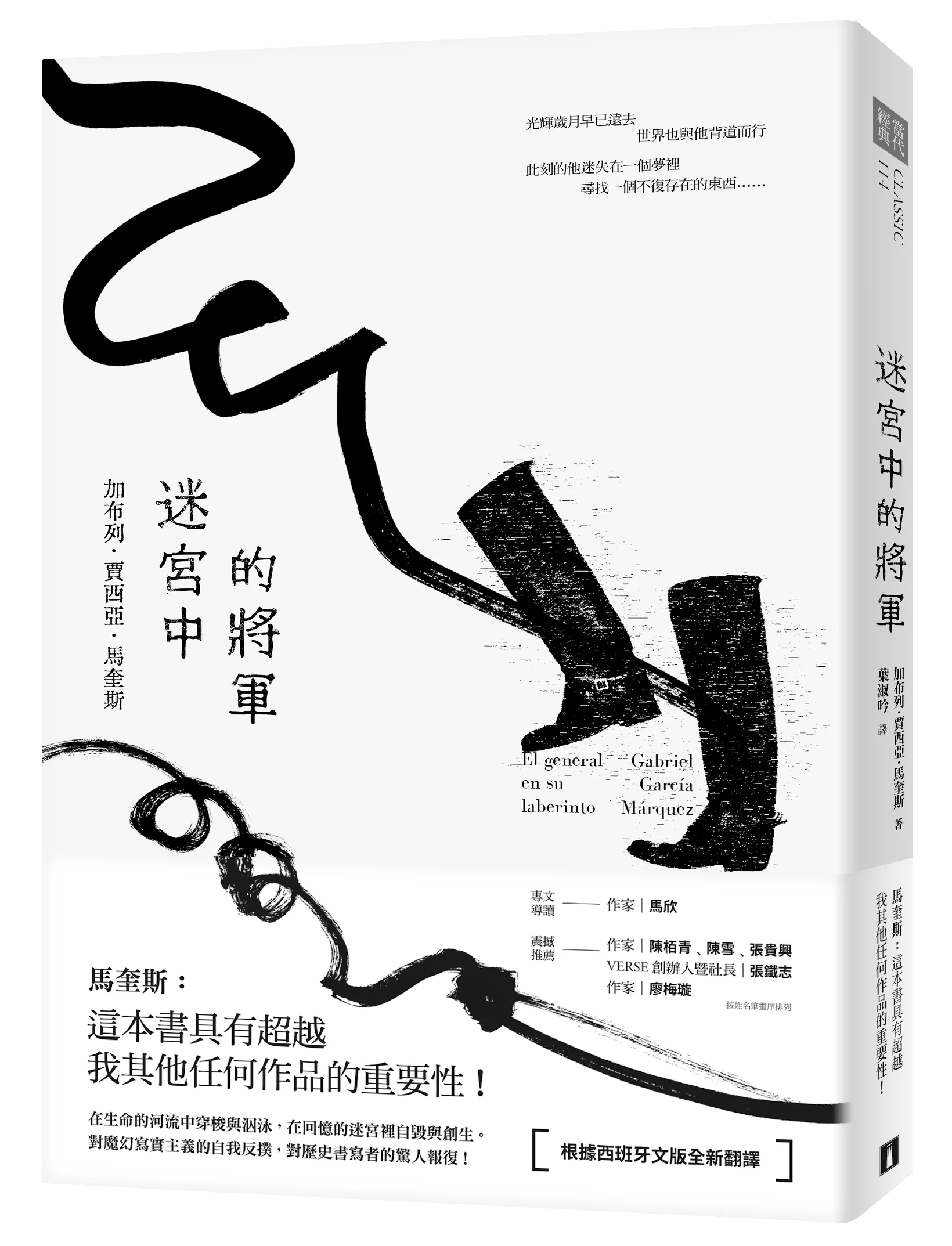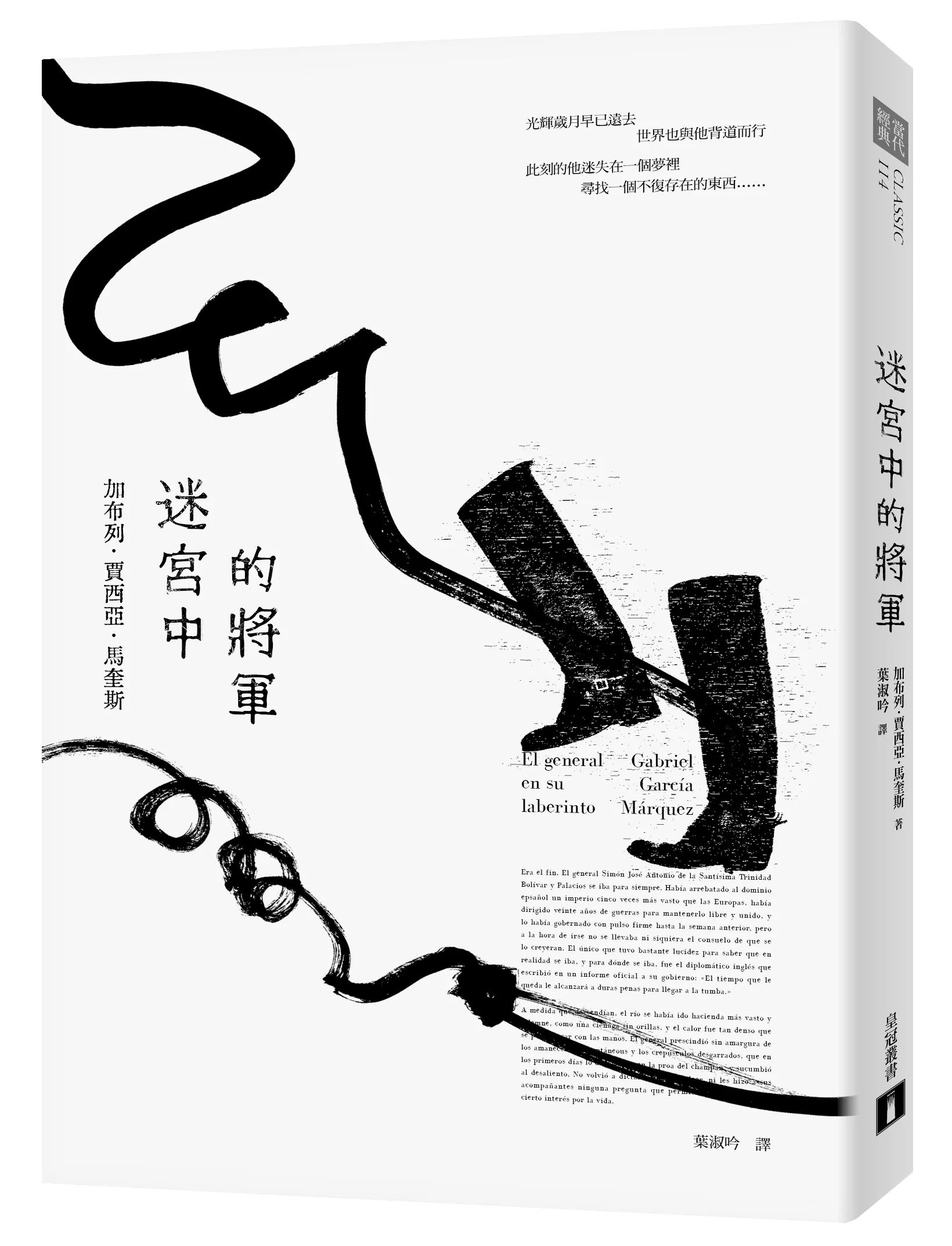內容試閱
他總是把死亡當作這個職業無可避免會遇上的一種風險。他遊走在危險的邊緣打仗,但從未受苦或受傷,他穿梭在敵軍的戰火中,卻能保持近乎不理智的冷靜,他的軍官們的解釋很簡單,那就是他自以為所向無敵。他遇過無數密謀害他的襲擊,全都毫髮無傷,他曾因沒睡在自己的床上,數度逃過一劫。他沒有隨身護衛,吃喝從不注意食物是從哪邊送來的。只有瑪芮拉知道,他的漫不經心並不是毫無自覺或相信宿命論,而是哀傷地深信著,他不會可憐兮兮、一絲不掛死在自己的床上,不會不受眾人感念。
在這個臨行前的夜晚,他依然失眠,而例行會所做的只有一件事與平常相當不同,他沒在上床前洗熱水澡。荷西.帕拉西歐斯很早就替他備好藥草浴,用以恢復體力,幫助化痰,而且保持水溫,隨時都可以洗。但是他不想洗。他吞下紓緩習慣性便秘的通便藥丸,準備一邊聽她輕聲呢喃利馬的豔情八卦一邊打個盹。突然間,他無來由犯了一陣咳嗽,彷彿撼動整棟屋子的牆壁。在隔壁廳堂的副官停下打牌。其中一個叫貝爾福特.韓頓.威爾森的愛爾蘭人在房門口探頭,看看他們有什麼吩咐,卻撞見將軍斜趴著在床上,想嘔出肚子裡的東西。瑪芮拉扶著他的頭俯在夜壺上方。荷西.帕拉西歐斯是唯一經過允許不用敲門進臥室的人。他一臉警戒守在床邊,直到意外結束。將軍眼眶含淚,深深地吸氣,指向化妝台方向。
「都怪那些枯死的花。」他說。
他一如往常,總是替自己的不幸隨便找個怪罪對象。瑪芮拉比任何人都還了解他,她示意荷西.帕拉西歐斯把花瓶拿走,裡面插的夜來香已在清晨枯萎。將軍再次躺回床上,閉上雙眼,她重拾剛才的語調繼續朗讀。直到她感覺他睡著,才將書本放在夜桌上,在他發燒的滾燙額頭上印下一吻,低聲交代荷西.帕拉西歐斯,早上六點她會到四角路口做最後道別,那裡是通往沃達那條路的起點。接著她披上厚斗篷,躡手躡腳離開臥室。這時將軍睜開雙眼,用微弱的聲音對荷西.帕拉西歐斯說:
「叫威爾森送她回家。」
縱使瑪芮拉千百個不願意,這個命令最後還是達成,因為她自認能照顧自己,不需要一群長矛兵護送。荷西.帕拉西歐斯拿著油燈走在她前面,往內院附近的馬廄而去,院子裡有一座石頭噴泉,夜來香已在凌晨時分先綻放一批。雨停歇了一會兒,穿梭在樹林間的風停止了嘶喊,但是冰冷的夜空連一顆星子也不見蹤影。貝爾福特.威爾森上校不斷說著夜間的通關密語,要躺在走廊蓆子上的哨兵安心。經過大廳窗前時,荷西.帕拉西歐斯看見屋主正在倒咖啡給一群朋友、軍人和民眾,他們徹夜未眠,聚在這裡等待啟程時刻。
荷西.帕拉西歐斯回到臥室,發現將軍身陷夢囈。他聽見他斷續吐出幾個字,湊起來剛好是一句話:「沒人能了解。」他的身體像是高溫燃燒的火堆,放出陣陣熏天的臭屁。第二天,將軍根本搞不清自己究竟是睡著說夢話,還是醒著說胡話,也不記得這件事。這是他所謂的「我的失智危機」。不過沒人大驚小怪,因為他從四年多前出現症狀,卻沒半個醫生敢以科學角度大膽給出解釋,每到第二天,他就會像是從灰燼重生,完全恢復理智。荷西.帕拉西歐斯拿條毛毯包住他,把點燃的油燈放在大理石化妝台上,退出房間,他沒關上門,待在隔壁廳堂熬夜待命。他知道將軍會在黎明的任何時刻煥然一新,踏進裝著水面靜止的浴缸,試著恢復被可怕的惡夢啃噬的精氣。
這時喧鬧的一天終於抵達盡頭。一支七百八十九名騎兵和擲彈兵的軍隊藉故發動叛亂,請求發放已經拖延三個月的薪餉。其實他們別有目的:他們大部分來自委內瑞拉,多數人打的是解放四個國家的戰爭,最近幾個禮拜以來,他們屢遭謾罵,在街上遇到不計其數的挑釁,確實有理由擔憂他們在將軍離國之後的命運。最後這場紛爭解決了,但不是發放叛亂分子要求的七萬塊披索,而只有津貼和一千塊披索,這些人在黃昏時組隊返回他們的故土,身後跟著一群扛著家當的女人和她們孩子以及家畜。群眾對著他們咆哮,連鑼鼓喧天的軍樂也無法蓋過,他們放狗攻擊他們,拿一串串鞭炮丟他們,打亂他們的腳步,那舉動彷彿從未對敵軍這麼做過。十一年前,當脫離長達三個世紀的西班牙統治,人稱登徒子的墮落者薩馬諾總督假扮朝聖者,從同樣的街道竄逃,不過他帶著一箱箱塞滿黃金偶像和祖母綠原石的寶物,以及巨嘴鳥、閃耀的蛺蝶彩繪玻璃,此時當然一定也有人在陽台為他哭泣,拋去一朵鮮花,和真心祝福他一帆風順,旅途多彩多姿。
將軍待在向戰爭與海事部長借住的屋子裡寸步不離,但秘密參加了解決衝突的協商,最後他派出荷西.勞倫西歐.席爾瓦將軍跟著叛軍到委內瑞拉邊界,以防混亂情勢再起,他信任這位投身政治成為他的助手的侄子。他沒看見隊伍從他的陽台下經過,但是聽見號角和小鼓響起,以及聚集在街道上的群眾的喧鬧聲,至於他們叫喊些什麼卻聽不清楚。這並不重要,他正在跟抄寫員檢視延遲收到的信件,口述一封給玻利維亞總統安德烈斯.德聖塔.克魯茲大元帥的信,在信裡宣布他要交權讓位,但不太確定他是否會前往國外。寫完信時,他說:「我這輩子再也不寫信了。」不久,他在午睡時熱得冒汗,夢中聽見遠處傳來吵鬧的叫喊,接著被一串劈啪聲嚇醒,那可能是叛亂分子的槍聲,也可能是煙火販的鞭炮聲。但是他問起時,有人回說那是節慶活動。就這麼簡單:「將軍,那是節慶活動。」包括荷西.帕拉西歐斯在內,沒人敢跟他說清楚是什麼節慶活動。
等到瑪芮拉晚上來訪時,他才知道他口中稱的煽動黨,也就是他的政敵的支持者在警衛隊的縱容下,走上街頭慫恿工匠工會反抗他。這一天是禮拜五,也是市集日,更容易在大廣場上引起混亂。天黑時下了一場驟雨,雨勢比平常還要猛烈,夾雜著閃電和雷聲。但是傷害已經造成。聖巴爾托洛梅中學的學生闖進最高司法機關辦公室,要求展開一場不利將軍的公開審理,他們手持刺刀毀壞一幅他的真人尺寸肖像畫,那幅油畫出自一位自由黨軍隊昔日的掌旗官之手,然後他們把畫從陽台丟了下去。一群喝完奇恰酒爛醉的暴民洗劫皇家街的商店,和郊區幾間來不及關門的酒館,還在大廣場上槍決一尊塞滿木屑的枕頭將軍,即使沒穿金鈕扣的藍色軍服,大家也能認出那是誰。他們控訴他背地裡鼓動軍隊造反,企圖奪回連續握權十二年後經議會全體投票所剝奪的權力。他們控訴他妄想當終身總統,再傳位給一位歐洲王儲。他們控訴他假裝出國,其實是要前往委內瑞拉邊境,再從那裡計畫回國,指揮叛軍奪取大權。公共建築外牆張貼著抗議海報,上面印著反將軍的辱罵字眼,他的一些眾人熟知的支持者躲在別人家裡,等待沸騰的情緒平息。崇拜他的頭號政敵法蘭西斯科.德寶拉.桑坦德將軍的報紙,也大肆造謠他的不明病症,和不斷強調他將離開,這一切不過是希望大家挽留他的政治手段。這一晚,當瑪芮拉.沙耶茲鉅細靡遺地向他描述下暴雨的白天發生的事,代理總統的士兵正試著清除大主教宮殿牆壁上用木炭寫下的標語:「他不會離開也不可能會死。」將軍吐出一聲嘆息。
「局勢或許非常糟糕。」他說。「但我的境況恐怕更慘,因為大家竟然要我相信,所有離這裡不過一個街區距離發生的事是節慶活動。」
事實上,連他最親近的朋友也不相信他就要離去,不管是交出權位還是告別國家。這座城市太過狹小,居民目光如豆,不了解他這趟不確定的遠行有兩大問題:他沒足夠的錢帶龐大的隨從去任何地方,他曾擔任國家總統,一年內離國必須經過政府允許,他卻壓根兒不打算申請。他下令打包行李,是刻意講給想聽的人聽,就連荷西.帕拉西歐斯都不認為這足以證明他下定決心,因為他曾不惜拆掉屋子,只為假裝離開,結果只是有效的政治花招。他的副官感到他沮喪的症狀在過去一年太過明顯。然而,這已經發生過幾回,而就在最出其不意的一天,他們目睹他醒來後煥然一新,重拾往日的活力,回到生活的正軌。荷西.帕拉西歐斯一直跟緊盯這些難以預料的變化,他以自己的方式表達看法:「我的主子想什麼,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他的反覆交權讓位被編入了民歌,最早的是他在宣誓就職總統的演說中一句含糊不清的話:「我能平靜度日的第一天,就是我在位的最後一天。」接下來幾年,他曾交權讓位相當多次,每一次的情況都大不相同,從來不知道哪一次才是真的。其中鬧得最沸沸揚揚的一次,是兩年前的九月二十五日那晚,他在總統府臥室遭遇暗殺,沒穿外套躲在一座橋下六個小時,最後安然無恙逃脫。凌晨時分,議會派委員會探訪,看見他包著一條羊毛毯,雙腳泡在一盆熱水裡,他筋疲力竭,但不是因為發燒,而是萬念俱灰。他向他們宣布,這樁陰謀不會遭到調查,不會有人被起訴,預定新年召開的議會改為立即召開,以選出另一位共和國總統。
「選完以後,」他下結論。「我將永遠離開哥倫比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