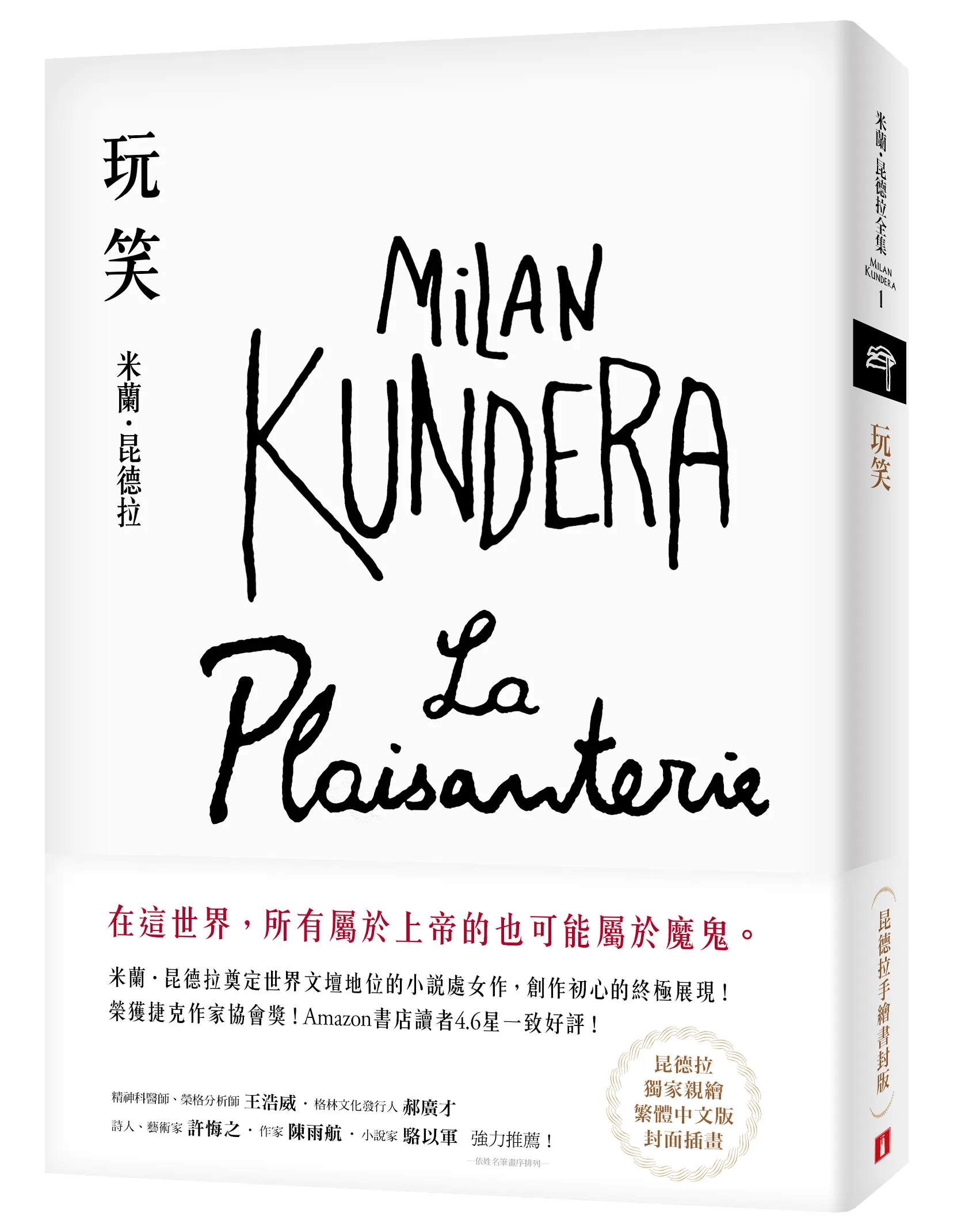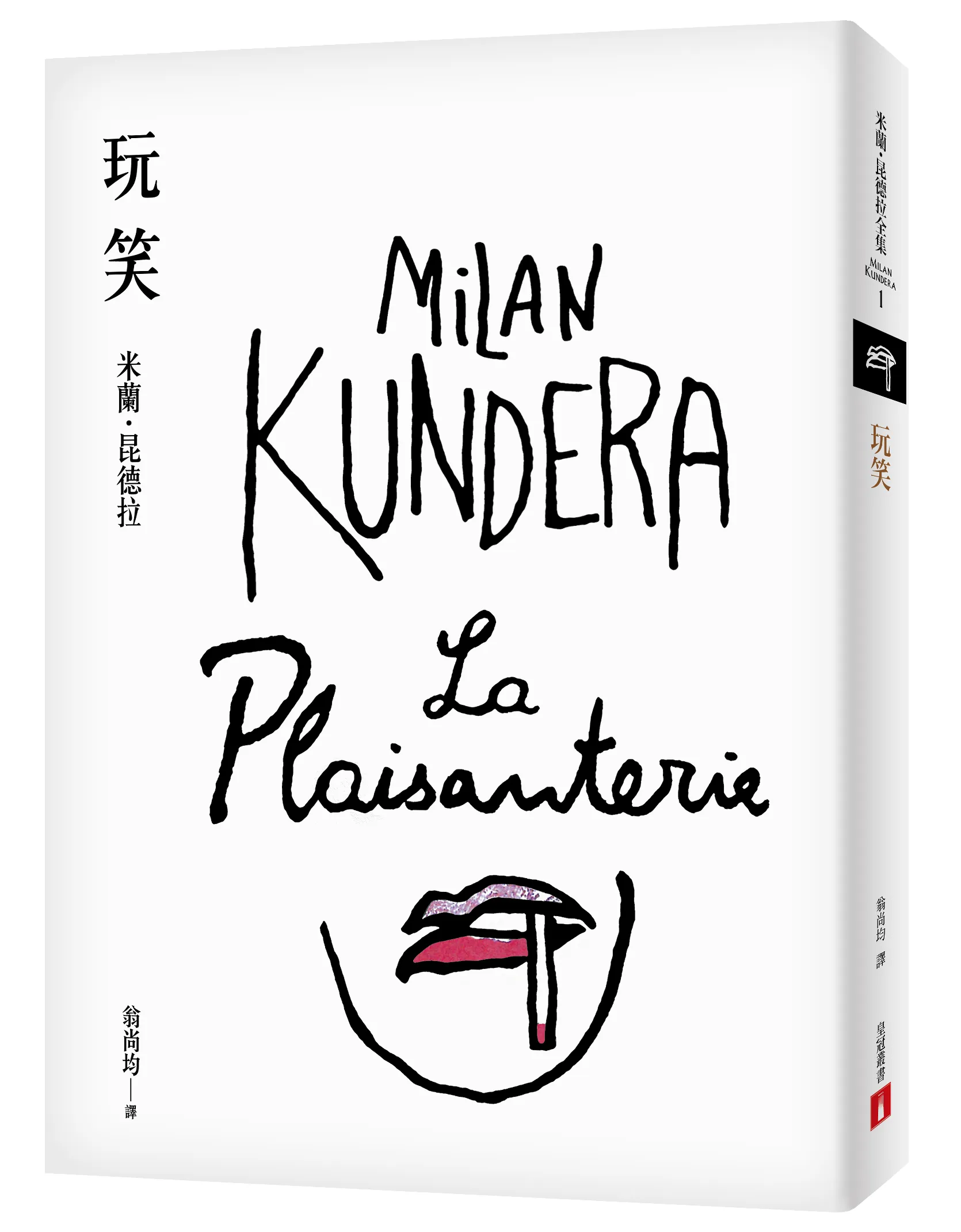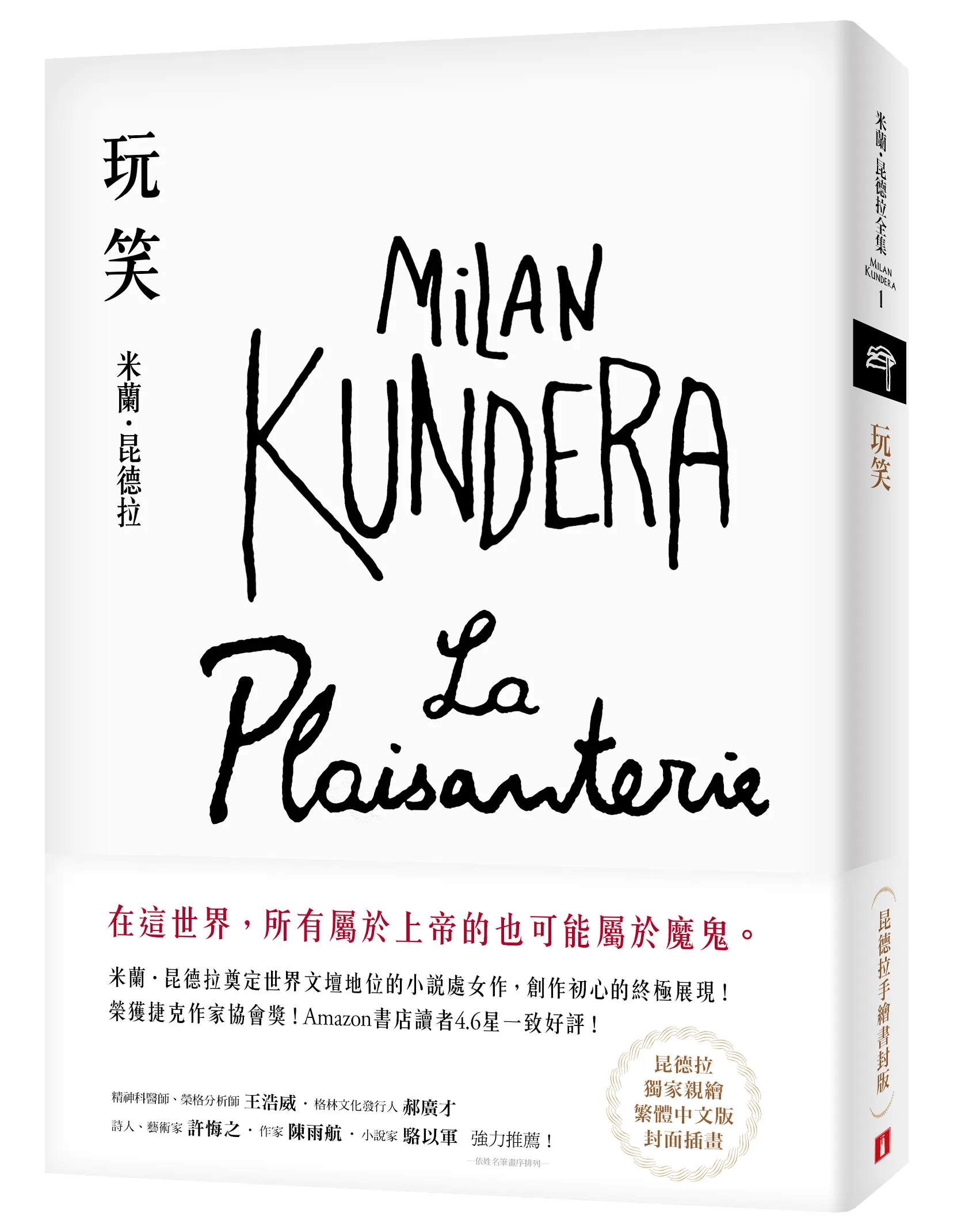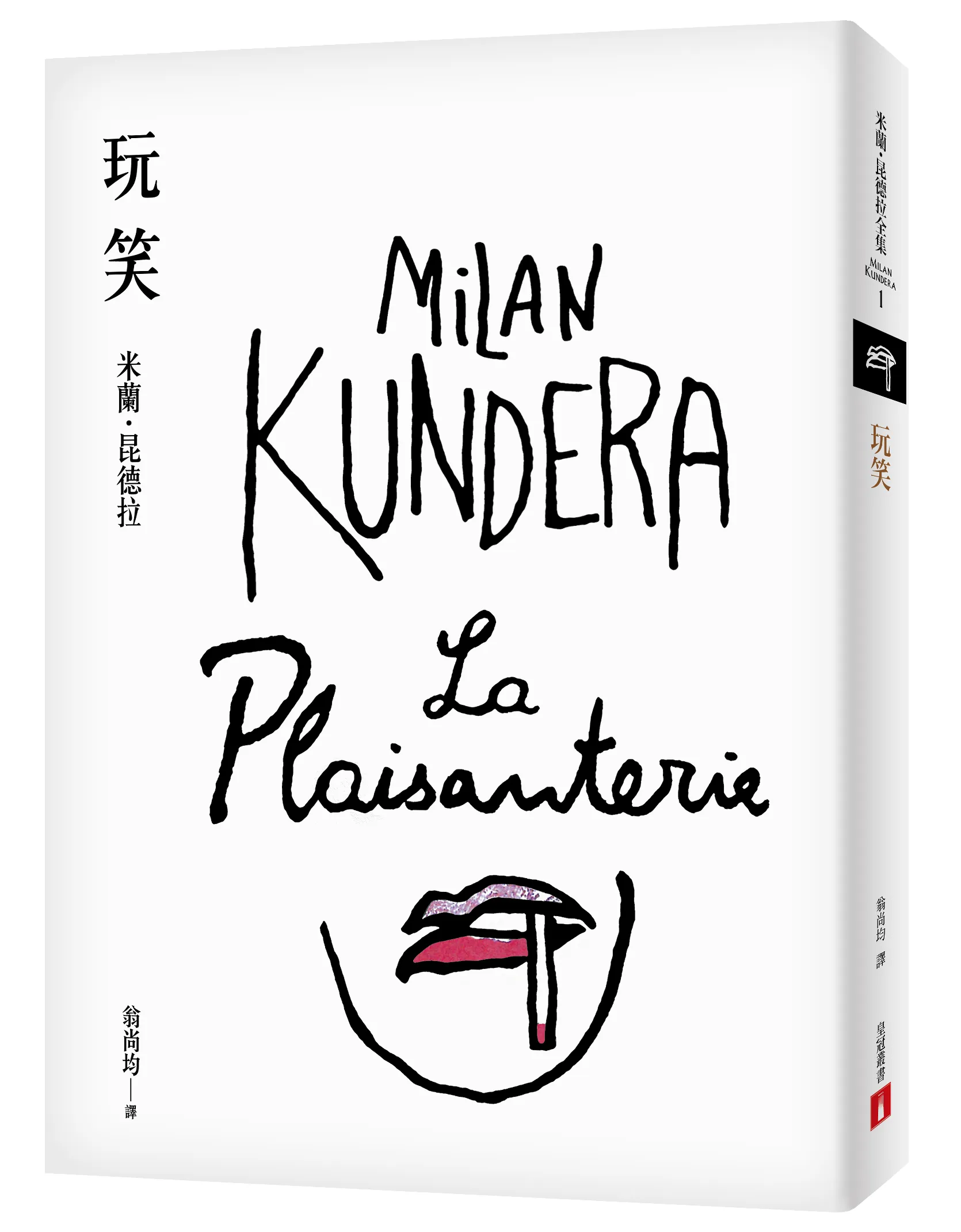內容試閱
最後告辭出門以前,寇斯特卡還客套一番,希望他的套間能「真正帶給我一些美好的事」。我回答他:「是啊,恐怕到時會像颶風過境,無堅不摧。」寇斯特卡答道:「哦,弄得滿目瘡痍也是美好的事?」而我只是在心裡暗笑,因為透過這個問題(說出來的時候雖是語氣輕柔,但意象裡面可是鬥志昂揚),這下子我重新拾回舊日對他的認識──既滑稽又親切的個性。那是十五年前事了。我回嘴道:「我很清楚,你是上帝那永恆工地中的安靜工人,聽見無堅不摧這碼子事你就不稱心如意,可是我無可奈何。說到我,我才不是上帝的一個泥水工學徒。要是上帝的泥水工學徒們在這塵世建造起真牆寬壁的高樓大廈,那麼我們真想摧毀什麼也是無處下手。然而,我看不見任何堅硬牆壁,有的只是裝飾。摧毀裝飾其實是件合情合理的事呀。」
我們這段談話接續了上次我們分手時(大概九年前吧)沒談完的主題。如今,我們這種意見相左的情況竟蒙上一層隱喻的色彩,因為我們都已知道深入到最底層會是什麼,同時也沒有感受到需要再回到那主題上面;我們只需要彼此一再重複,說是對方沒有改變,說是對方和自己竟始終和昔日一樣不同(關於這點,我得聲明,我很欣賞寇斯特卡和我的差異,也正因如此,我才樂意與他探討事情,唯有這樣,我才一直可以證實自己是誰以及我的思想為何)。因此,為了解除我對他的一切疑慮,他回答我道:「你剛才那一番話聽起來頭頭是道。不過我想知道:像你這種凡事存疑的人,現在為什麼自信飽滿,讓你可以確定什麼是牆壁,什麼又是裝飾?你難道不曾懷疑過,你所嘲弄的假象果真就是假象?你難道不可能搞錯?如果那些是價值觀,那麼你就是價值觀的摧毀者了?」接著他補充道:「一個糟糕的價值觀和一個被揭穿的假象都具有相同可憐的體質,兩者沆瀣一氣,沒有什麼比將兩者混為一談更容易的了。」
就在我陪同寇斯特卡返回那座位於城市另一端盡頭的醫院時,我的手一直在口袋裡玩弄那兩支鑰匙。能夠陪在昔日老友的身邊可真是件愉快的事,因為他不論在什麼地方,不論在什麼時候,總是不斷嘗試讓我信服他心目中的真理,甚至像現在,就在我們一起穿越崎嶇不平的新建區域時也是如此。很明顯地,寇斯特卡想起隔天我們一整個晚上都會聚在一起,所以暫停哲學討論,轉而聊起一些平凡無奇的話題。他知道隔天晚上七點左右從醫院下班後一定會在他家看到我(他自己並沒有備份鑰匙)。他又問道,我是不是真的什麼都不缺了。我摸了摸自己的臉,然後回答他說,只差上理髮店走一趟,因為鬍鬚長了,不很舒服。寇斯特卡答道:「那我這就早早帶你去理髮師那裡好好刮上一頓鬍子!」
我沒拒絕寇斯特卡的美意,讓他領我走進一家規模不算大的理容院。三面大鏡子前面安裝了三張可旋轉的大扶手椅,其中兩張已經坐了兩個男的,他們低著頭,臉上抹足了刮鬍泡沫。兩個穿著白罩袍的女人傾身向著他們。寇斯特卡走到其中一個女的身邊,向她嘀咕了幾句話;那個女的拿毛巾將剃刀上的泡沫揩淨,然後對著店舖後間喊了一個名字,立刻有一位也是身穿白色罩袍的年輕女子走了出來,然後接手照料剛才坐在大扶手椅裡,暫時被撂下的那個男的。先前寇斯特卡對她低聲說話的那個女人向我微微點頭,伸手示意要我坐在最後那張還沒人坐的大扶手椅裡。這時,寇斯特卡和我握過了手便互相道別了。我在大扶手椅裡坐定,將頭倚在權充支撐的小靠墊上。因為好些年來,我一直都不喜歡觀看自己的臉孔,所以就避開了那張放置在我面前的鏡子,並將眼睛抬起,讓目光梭巡在那片以白石灰塗飾,但已有骯髒污斑的天花板上。
甚至等到那位女理容師用手指將一條白色布巾的邊緣塞入我襯衫的領口時,我的目光依舊駐留在天花板上。接著女理容師移開一步,然後我便聽到剃鬚刀在一塊皮革上來回磨利的聲音,這時我一動也不動地僵在椅子裡,渾身漫過一種無須掛念任何事情的愜意感覺。過了片刻,我感覺到幾根潮濕的指頭在我的臉頰皮膚上敷塗大量的剃鬚乳膏,突然之間,我的心中興起一種奇怪的意識:一個與我無關,而我也與她無關的陌生女人正溫柔地撫摸我的面容。接著,那位女理容師拿起剃鬚用的刷子,開始將肥皂推勻在我臉上。我感覺自己似乎甚至不是坐在椅子上面,而是飄浮在一片污漬斑駁的白色空間裡。這時我想像(因為就算在我休息的時刻,意念仍舊不停地運轉)自己是個手無寸鐵的犧牲者,完全受制於一位磨快剃鬚刀刃的女人。我的身軀彷彿消融在空間裡面,只覺得臉上有指頭不停來回。我毫不困難便想像到她那輕軟的雙手捧著(側過左邊,側過右邊,又是細膩撫摸)我的腦袋,彷彿那雙手根本不把它當作連在我軀幹上的東西,而是把它看成完全獨立分離的物件,以至於那把躺在一旁小桌子上的鋒利刀刃似乎就等著從脖子割下,成就我頭部的美妙自主狀態。
接著,撫摸的動作停了下來,然後我聽見那女理容師走開的聲音。這次,她真的一把抓來,這時我心裡暗忖(因為此際思想依然繼續它們的遊戲),無論如何我得看看我這頭顱的女主人到底什麼表情,我那溫柔的劊子手究竟哪副德行。我將目光從天花板移開,然後看鏡子一眼。我嚇壞了:剛才我為了自娛所幻想的情況突然之間詭異地形成真實的輪廓;我覺得那個女人,在鏡子裡傾身向我的那個女人,我是認識她的。
她先伸出一隻手捏定我的耳垂,然後另一隻手便小心謹慎開始刮除我臉上那堆肥皂泡沫;我仔細觀察她的臉,前一刻我才訝異不已瞥見的那張臉,現在對於它的熟稔,以為她是哪個舊識的想法居然一丁點一丁點崩解,最後消失於無形。接著,她又微彎腰肢,在洗臉台上將剃鬚刀上面一大坨的肥皂泡沫抹除下來後,站直身子,然後推轉一下我坐的那張大扶手椅;我們的目光剎那間交會一起,我突然再度認定是她沒錯!當然,這一張臉略有不同,彷彿是她大姊的,只是膚色變得暗沉,失了彈性,又有一點凹陷。畢竟我上一次看見她已經是十五年前的事了!歲月悠長,時間在她的五官上罩上一張欺瞞人的面具,但是幸好,這張面具還有兩個孔穴,因為她仍舊可以用她那雙真正的、實際的眼睛看我,十五年前我所認識的那雙眼睛。
但是這條原本清晰可辨的線索卻又被一件突如其來的事給弄亂了:理容院裡又進來一位顧客。進來以後他就坐在我背後的一張椅子上,等著輪到他的時候再坐上大扶手椅。過一會兒,他開始對我的女理容師講話,所發表的議論內容針對夏日的美好天氣以及城郊接壤地帶正在興建的游泳池,女理容師回答他一些話(我只注意她的音質,沒有注意答腔內容,反正是東拉西扯無甚深義的話)。我卻發現我認不出這個聲音;她的聲音一派從容不迫,完全沒有急躁味兒,幾乎稱得上俗氣,總之是個壓根陌生的聲音。
現在她洗著我的臉,並用手掌心又揉又按,而我(儘管剛才辨音的經驗)卻又再度深信一定是她,錯不了的。十五年過去了,那雙手按在我臉上的感覺依然沒變。她又一次摩挲我的臉,撫摸良久,而且那樣溫柔(我完全忘記,她只是清洗我的臉,不是撫摸)。她那陌生的聲音依然不停和那聊天興致越來越高的男人應對,可是我拒絕相信聲音,寧可相信她那雙手,我是靠那雙手認出她的;碰觸在我皮膚上的感覺如此溫柔,我嘗試要進一步審視她,還要看看她是否認出是我。
接著,她取來一條布巾然後擦乾我的雙頰。那個囉嗦個不停的男人因為自己方才說的笑話而爆出一陣狂笑,然而我注意到,女理容師並沒有跟著陪笑,也就是說,她也許根本沒太注意那傢伙在東扯西扯些什麼。這層認識令我感到些許不安,因為這事證明了她已經認出我來,此刻她應該努力在壓抑心中的情緒激盪。我下定決心,一離開座位便要和她說話。她把圍繞在我頸項間的布巾取下。我站起身。我從外套內裡的口袋裡拿出一張五克朗的鈔票。我等著,等著我們雙方目光再度交會,然後便叫一聲她的小名,開始和她說話(那個傢伙還在那裡扯淡)。可是她表情漠然地將頭偏轉過去,乾淨俐落地接過紙鈔,沒有參雜絲毫個人情感在裡面,以至於我落得像個愚信自己幻象的傻瓜,完全鼓不起向她說出隻字片語的勇氣。
我走出理容院,心裡有股不滿足的古怪感覺;我唯一確定的事便是我什麼都不知道。在我看來,過去自己曾經迷戀的臉龐,現在對它卻搖擺在認得出與認不出的猶豫狀態,這可是一件十分「粗鄙」的事。
當然,要了解真相其實並不困難。我加緊腳步朝旅館的方向走去(途中我在人行道上認出一位年輕時代老朋友的面孔,他叫賈洛斯拉夫,是某個洋琴樂團的指揮,可是彷彿我要逃避太尖銳、太嘈雜的樂音似的,我迅速地把目光偏移開去)。回到旅館以後,我打電話給寇斯特卡;他還在醫院裡忙。「告訴我,你介紹給我的那位女理容師是不是叫作露西.塞貝特闊娃?」「現在她改名了,不過確實是她。你是怎麼知道她以前的名字的?」寇斯特卡問道。我回答他道:「那是天荒地老以前的事。」之後,我離開旅館,根本沒想到該吃晚飯(天色已經全暗下來),只是漫無目標閒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