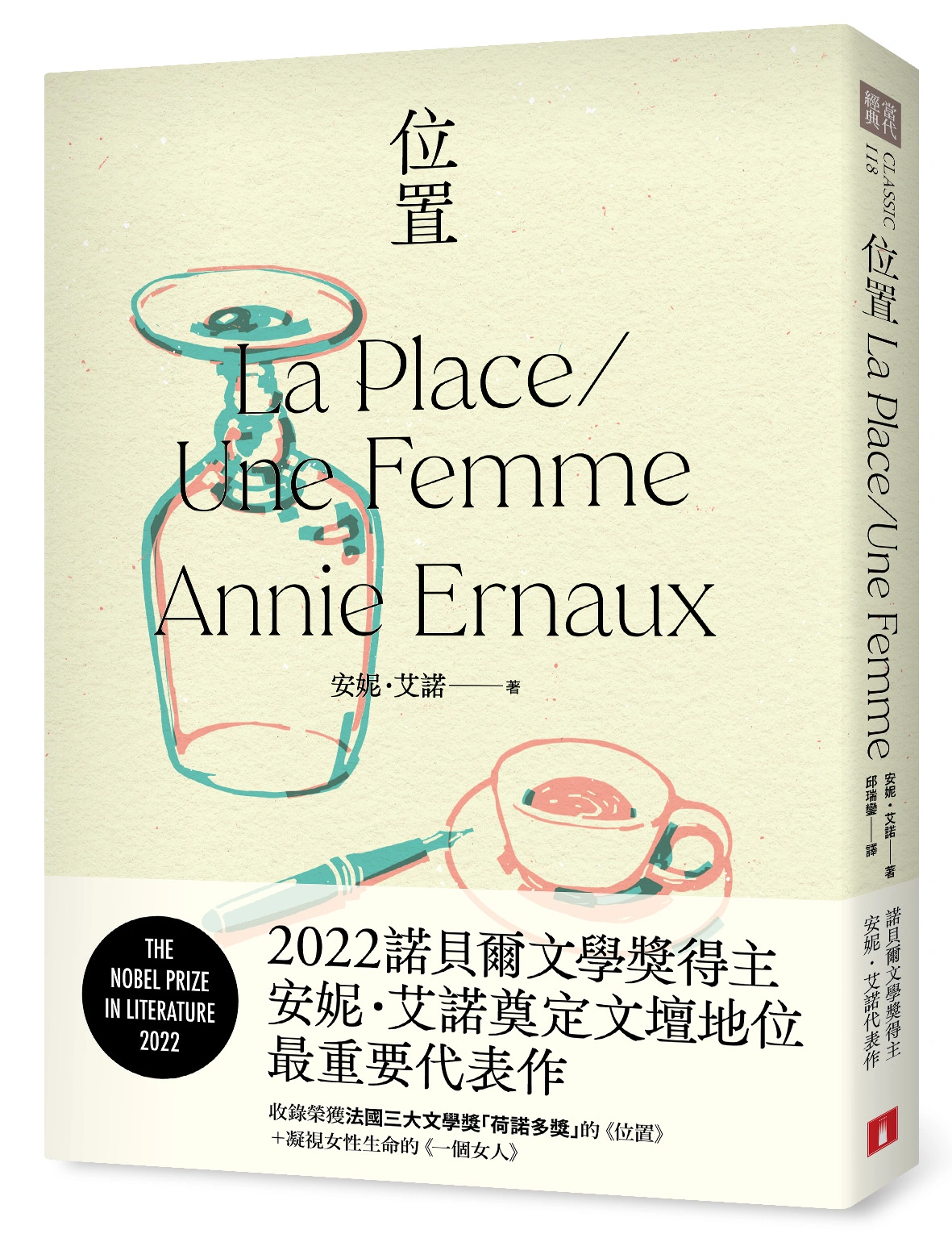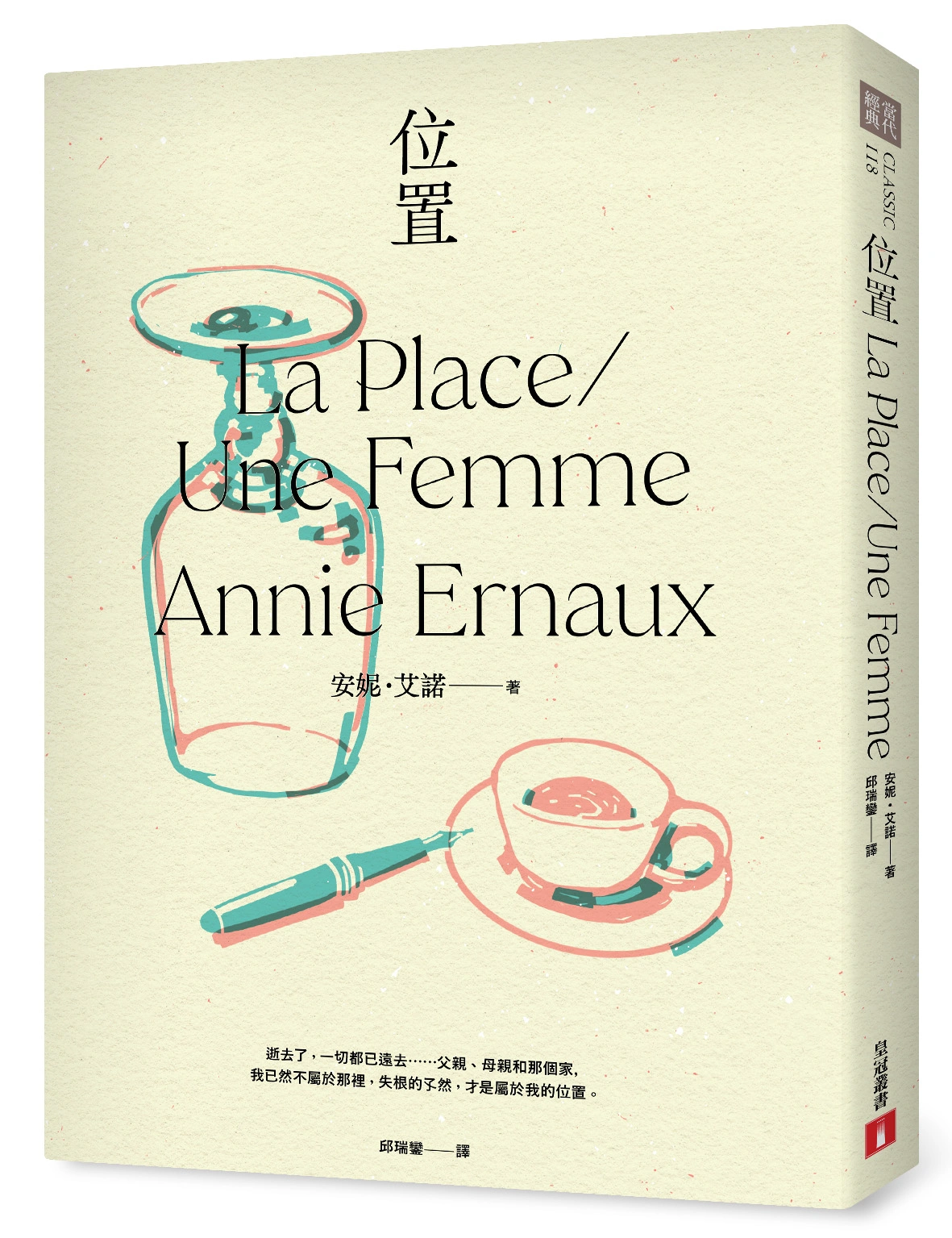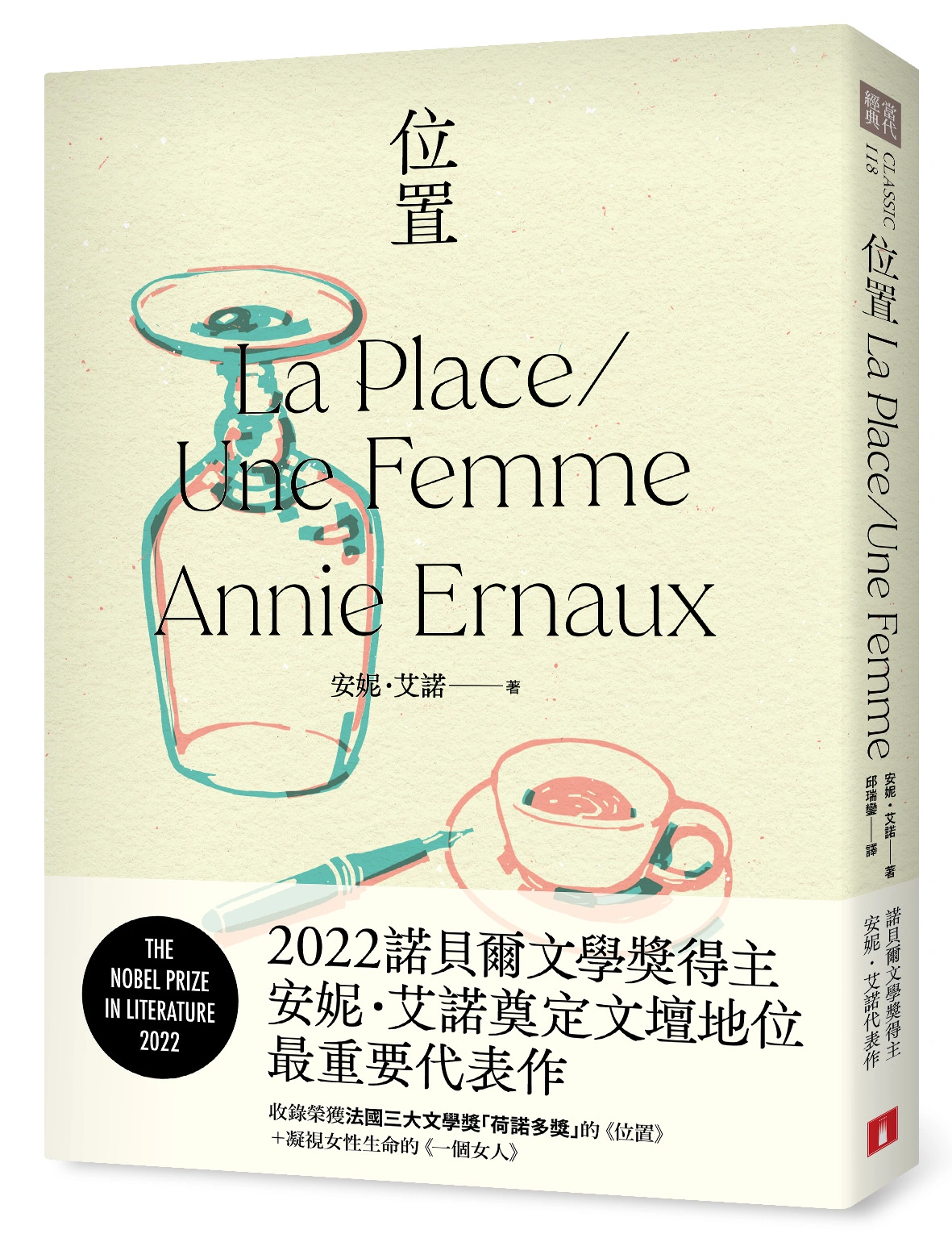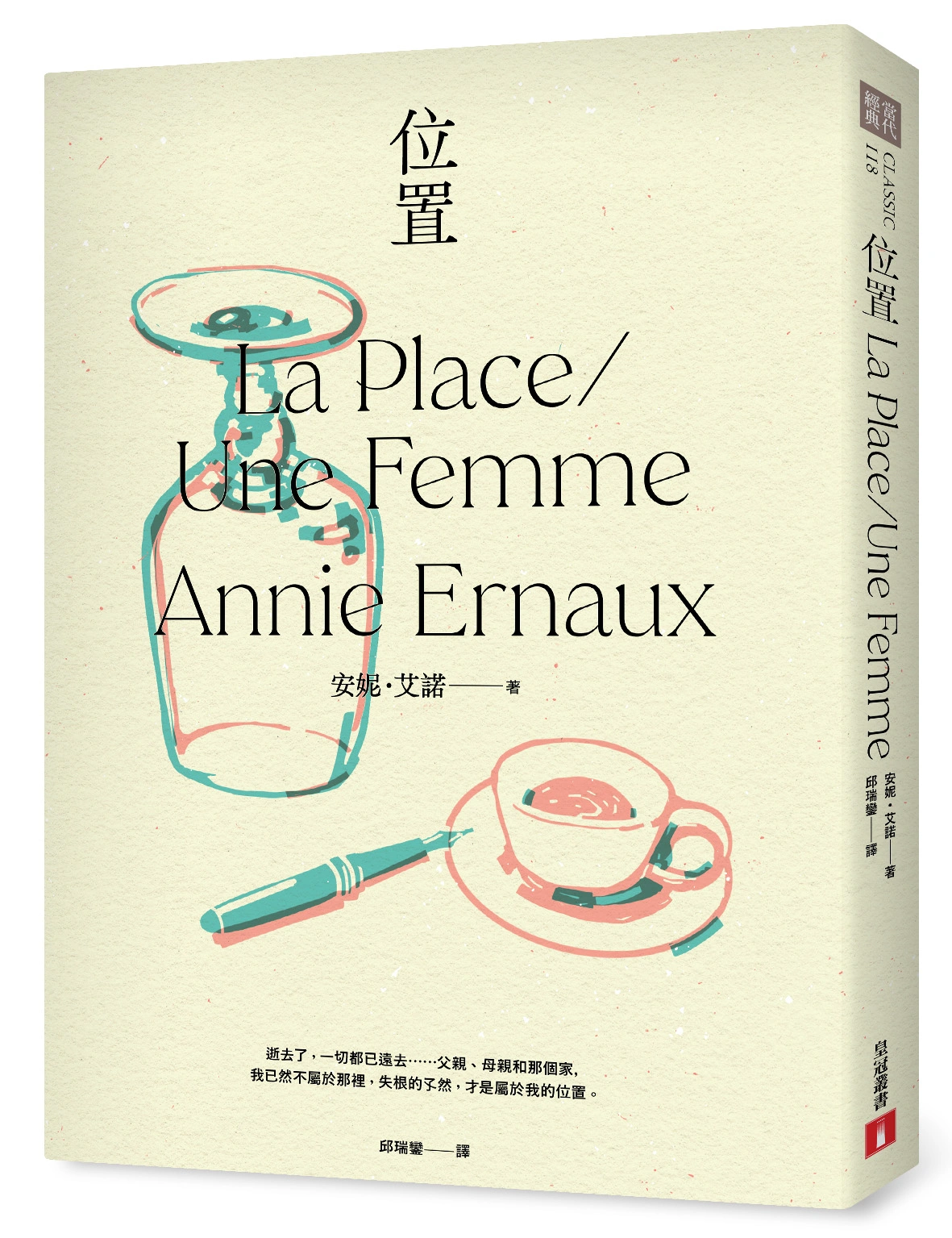內容試閱
我們附近鄰居,很多人都去了教堂,不用工作的女人,請一個小時假的工人。當然,那些「有地位」的人沒一個到,雖然我爸爸生前狀況還好的時候,曾經跟他們打過交道;而且,也見不到別的生意人。他從來不屬於任何團體,只繳商業公會的會費,什麼活動都不參加。本堂神父致悼詞的時候,說他「為人正派、工作勤奮」、「是個從來沒有對不起別人的人」。
來參加喪禮的人和我們握手致意。因為司儀弄錯了──除非他想讓大家多走一圈,好讓出席的人數看起來倍增──已經跟我們握過手的人又重新來一回。這一次大家速度比較快,沒有致哀的話語。墓園裡,繩子吊著棺木搖搖晃晃的往下沉,這時候,我媽媽突然啜泣起來,就像我婚禮那天,做彌撒的時候。
葬禮後,大家在咖啡坊裡用餐,桌子一張一張併起來。剛開始,是一片寂靜,然後談話轉趨熱絡。孩子,睡飽了午覺醒來,一朵小花、一把石子,所有他在花園裡找到的東西,一樣樣拿來送給每個人。我爸爸的哥哥,座位離我滿遠的,他探過身子湊近我,跟我說一句話:「你爸爸以前都騎腳踏車載你上學,你還記得嗎?」他聲音和我爸爸很相像。約莫五點鐘,客人都走了。我們把桌子整理好,誰都沒說話。我先生當天晚上又搭火車走了。
我留下來幾天,陪我媽媽一起辦喪事之後的一些手續。到戶政事務所辦死亡登記、付葬儀社的錢、回覆慰問函。用A.D.遺孀的身分印新名片。一段空白時期,腦子空空。有好幾次,在街上走,心裡盤旋一個念頭:「我是個大人了」。(以前,我媽媽說:「你是個大女孩了。」因為月經來。)
我們整理了我爸爸的衣服,分送給有需要的人。他每天穿的那件短外套,掛在食物儲藏室裡,我在口袋裡發現他的皮夾。裡面,有一點錢,有駕照,而且皮夾折攏的部分,有一張相片塞在一張報紙剪報裡面。相片,是舊的,花紋裁邊,照的是排成三行的一夥工人,都注視著鏡頭,全戴大盤帽。歷史書裡典型的照片,附加在某次罷工事件,或是在提到人民陣線時的旁襯圖片2。我認出了我爸爸,在最後一排,表情嚴肅,樣子很不安。大部分人在笑。報紙剪報是榜單,女師專入學考的榜單,根據成績排名。第二個名字,是我。
我媽媽恢復了平靜。她招呼上門的客人,一如往常。一個人的時候,她臉色就衰垮下來。每天,一大清早,店還沒開門,她養成先到墓園走一走的習慣。
禮拜天,在回程的火車上,我逗我兒子玩,好讓他乖乖的不吵鬧,頭等車廂的乘客不愛噪音,不愛小孩動來動去。突然間,我愣了一下,「現在,我還真是個中產階級」,還有「一切都太遲了」的想法,猛然上心頭。
後來,在那年夏天,我等我第一次的教職分發,心裡直想,「我必須把這一切說清楚」。我的意思是,以我爸爸為題材來寫作,他的一生,以及從我青少年時期就存在的,他和我之間的距離。階級的距離,可是,是一種特殊的,無以名之的階級。就像分據兩處,不相交的愛。
接下來,我動手寫小說,他是主角。寫到一半覺得反感。
不久前,我明白了是不可能用小說來呈現的。要描述為升斗折腰的一生,不應該先決定藝術表現形式,也不應該尋求一些「至情可感」,或者是「撼動人心」的事情。我拾掇我爸爸的話語、他的動作、他的喜好,他人生裡的一些重要事件,還有我曾和他一起分享的生活印記。
回憶裡,詩意闕如,也沒有歡喜快樂,沒有讓人會心的一抹微笑。平鋪直敘的文筆自然的流露紙頁,這種寫法,就像我以前寫信給我爸媽,報告生活近況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