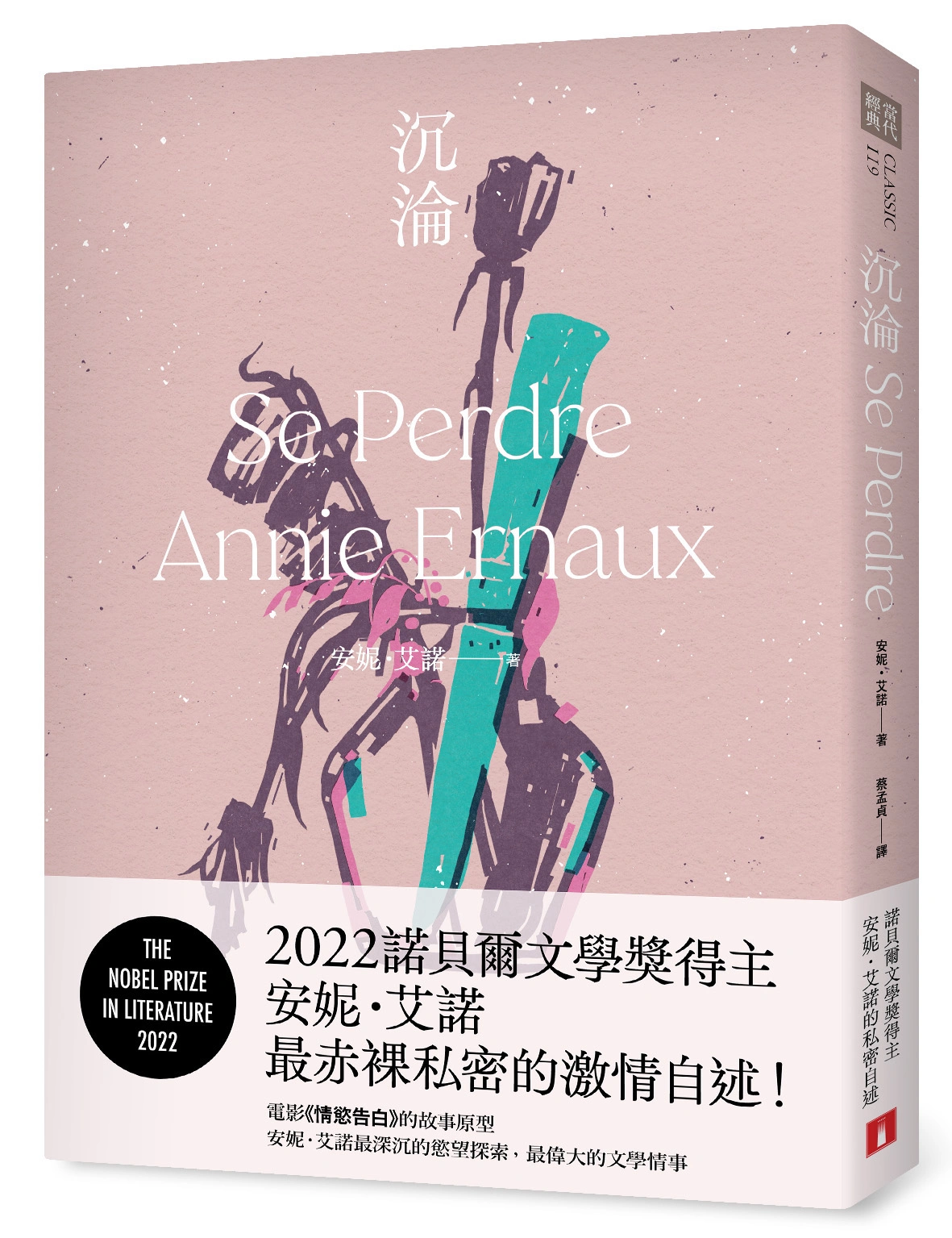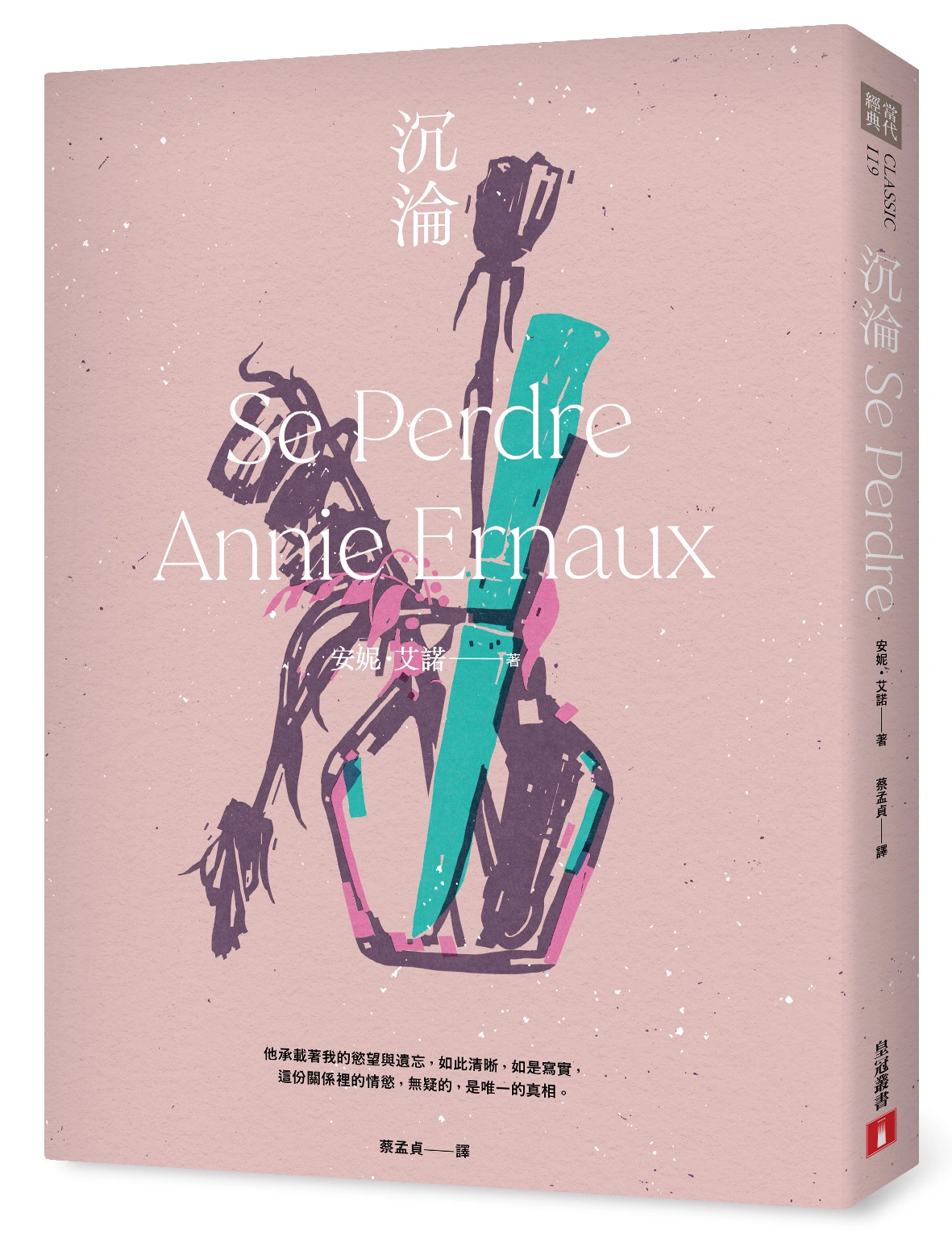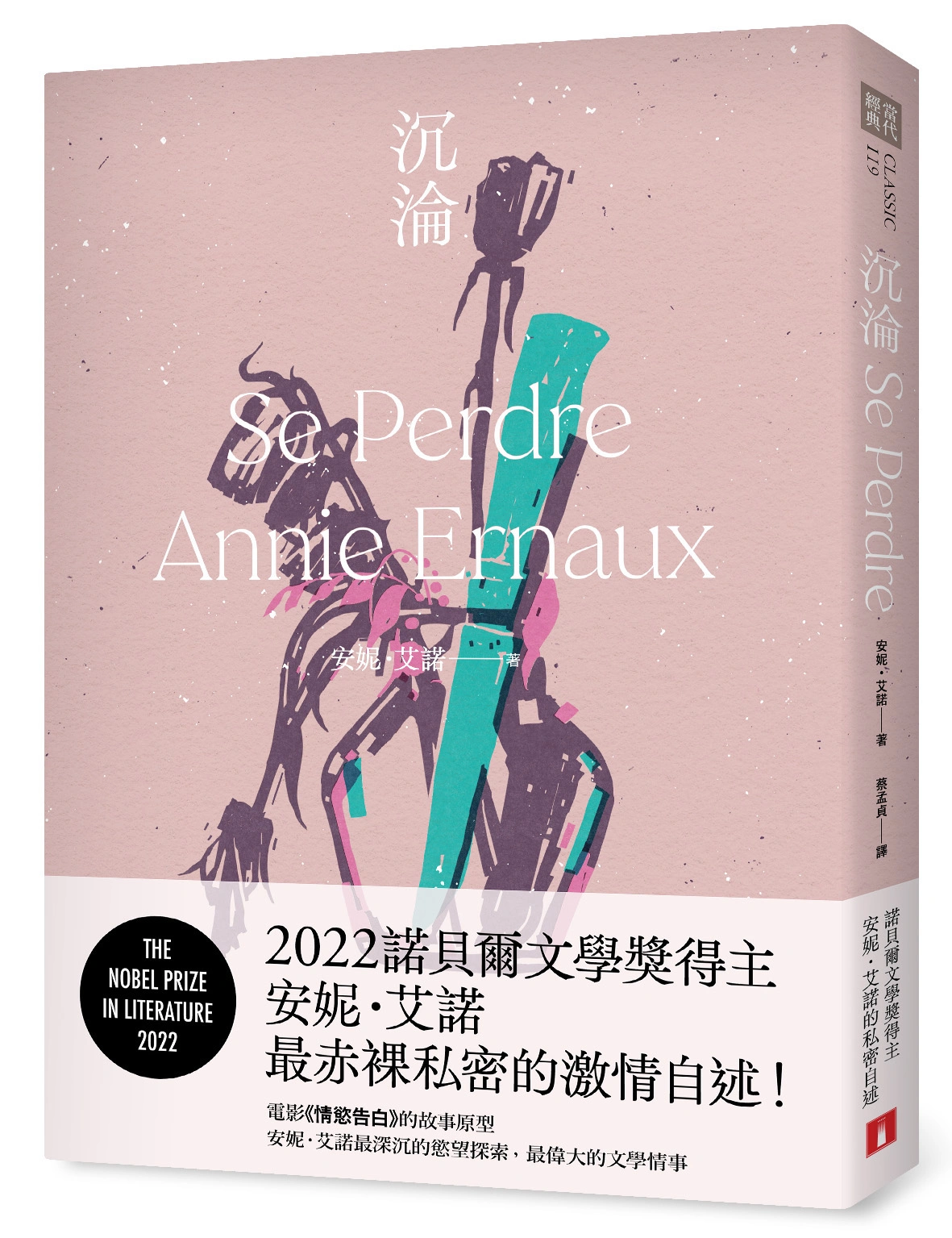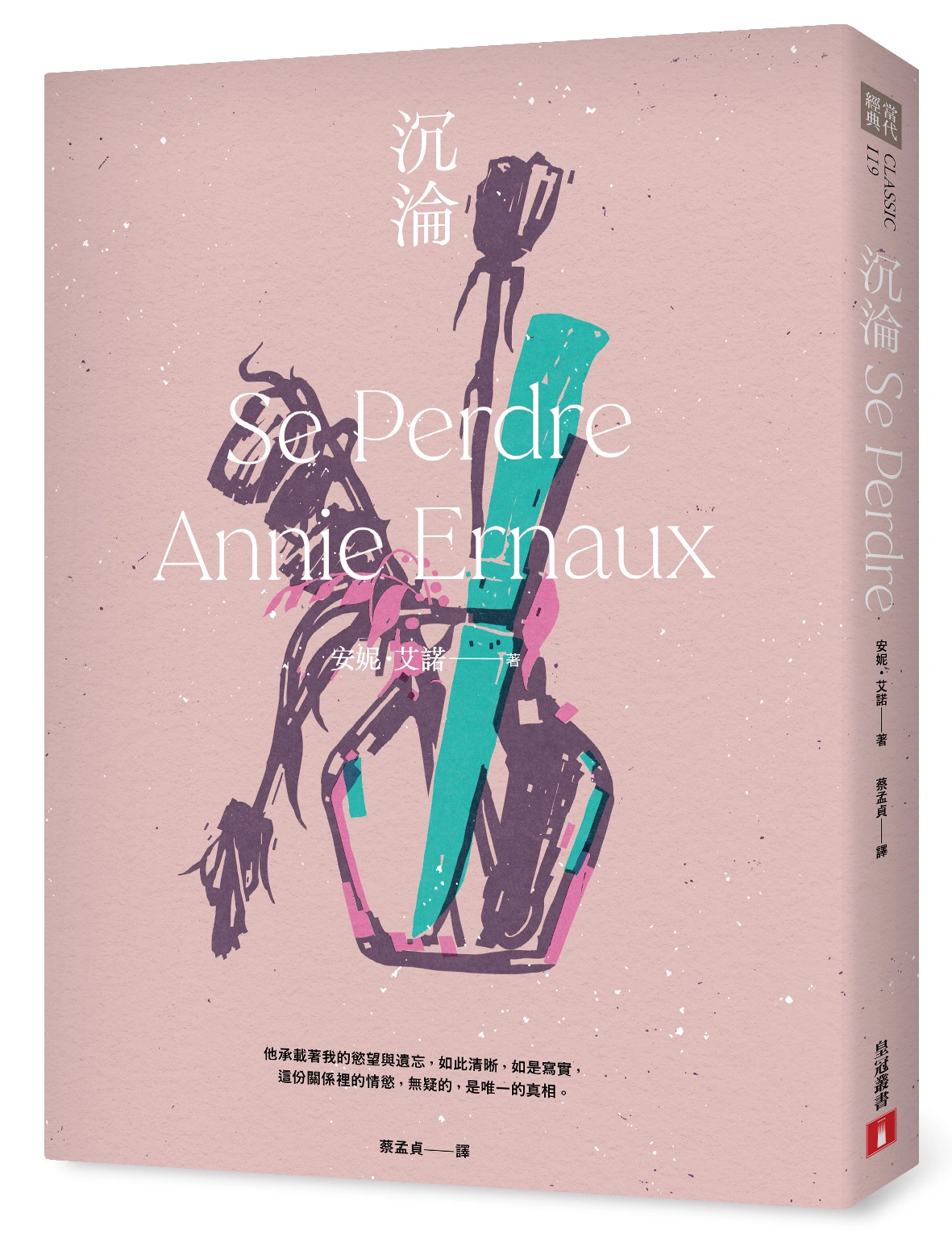內容試閱
十月
一日星期六
十二點四十五分。班機延誤了三個小時。苦樂參半,到頭來,他打不打電話來其實沒有什麼差別,同樣地緊張難耐。從十三歲起,我就嘗過這種滋味了(G. de V.、C.G.菲力普是三大要角,接著是P)。「美麗的愛情故事」展開了?我好怕死在車上(今晚,在巴黎和里爾之間的路上),好怕碰上什麼,阻礙你我再相見。
二日星期天
疲憊,無力。從里爾回來後,四點才睡。在大衛的小套房裡做了兩個小時的愛(大衛和艾瑞克是我的兩個兒子)。青腫、歡愉,還有揮之不去的及時行樂的想法,盡情享受離別前的每一秒,心力交瘁,搶先在恐怖的危險警告「我太老了」之前。但是,我三十五歲的時候也可能嫉妒一位年逾五旬的美麗婦人。
索堡公園,水道縱橫,冰冷潮濕,空氣飄著泥土的氣息。七一年間,我到這裡參加高等教師資格會考,那時候我怎麼也想不到我會再回到這個公園,身邊跟著一位蘇聯外交官。此刻,我看見了數年之後的自己,再度踏進這裡,重溫今日漫步的足跡,就像我為了憑弔六三年的一段回憶,一個月前跑到威尼斯去一樣。
他迷大車、愛豪華、搞人際關係,極少人文氣息。連這些都像回到過去,像我丈夫的形象,令人討厭的模樣,而它出現在這裡的原因是,它與我過去的某個生命片段相吻合,那是非常甜蜜、積極的時期。我甚至不怕跟他一起坐車。
該如何才能讓我的依戀維繫長久些,讓他也偶爾感到要拴住我的心並不是那麼簡單……
三日星期一
昨晚,他打電話來了,我還在睡夢中。他想過來,我沒辦法(艾瑞克在此)。翻騰的夜,這分慾望,我該拿它怎麼辦呢?還有,今天,我是見不到他了。我哭了,出於這分慾望,出於想要他的這分真實的飢渴。他反映了我自己最「意氣風發」的部分,也是最年少輕狂的我。極少人文氣息、迷大車,開車時愛聽音樂,「彷彿」,他是「我年輕時候的男人」,金髮又帶點莊稼漢的味道(他的手、方正的指甲),他帶給我滿滿的歡愉,完全不想對缺乏人文氣息這點再多加苛求。我還是得真正地睡一點覺才行,體力已到達極限,無力再做任何事。悲慟和愛情,無論是在我的心靈,或是對我的肉體而言,代表的都是同樣的一件事。
艾荻.皮雅芙(Edith Piaf)的歌:「神啊,把他留給我吧,再一會兒就好,一天、兩天、一個月……足以迸出愛火,然後傷痛的時間……」我走得愈遠,陷得愈深。母親的病和辭世讓我看清了有人相伴扶持的需要。每回鬧著對S說:「我愛你。」他總回答:「謝謝!」大約與「謝謝,不客氣」的意思相去不遠。這樣的問答我覺得很有趣,的確。然後,他說「妳等著看我太太吧」時,言辭間又是幸福、又是驕傲。我,我是作家、妓女、外國人、豪放女;我不是大家珍藏、炫耀,又會撫慰心靈的「瑰寶」。我不會撫慰人的心靈。
四日星期二
我不知道他是否有意繼續下去。「外交」病(一笑!)。但是,淚水已經瀕臨決堤邊緣,因為歡笑成了泡影。多少次,我癡癡地等,裝扮得「美美的」,滿臉堆笑,最後卻是一場空。兩人世界沒有成真。而他,在我的感覺上,是如此地難以捉摸、神秘難測,必要的時候,想必他也會是個不折不扣的、表裡不一的偽君子。打從七九年他就入黨了。那副得意之情,跟升官、通過考試沒什麼兩樣。他曾經是蘇聯最優秀的公僕。
今日唯一感到幸福的時候:在RER(巴黎地鐵快車線)上,有個小混混上前搭訕,我粗話衝口而出:「還不給我閉嘴,看我給你兩巴掌……」我成了最最平常、醜陋的搭訕場景的女主角(還有兩個配角在一旁觀看),在一輛空盪盪的地鐵快車上。
難道與S的幸福已成過往雲煙?
五日星期三
昨晚,九點,電話:「我來了,在妳家附近,在瑟吉……」他過來,我們躲在我的書房裡兩個小時,因為大衛也在。這一次,他毫無忌憚。我無法成眠,無法擺脫他的肉體,就算人已走,卻仍盤據我心。這正是我悲哀之處,我無法忘卻另一個人,無法成為獨立自主的個體,我是空洞的華麗詞藻,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連軀體都得依附在另一具軀體才得以生存下去。經過這麼一個夜晚的折騰之後,實在難以定心工作。
六日星期四
昨天晚上,他到瑟吉來找我,我們去了大衛的小套房,在勒本漢街上。燈光昏暗,他的身體若隱若現,同樣的狂熱激情,幾乎整整三個小時。回程路上,他開得飛快,收音機開著(「紅與黑……」,去年的流行歌曲),閃大燈。有一款超強馬力的汽車,是他很想買的,他指給我看,十足的志得意滿神情,外帶一點莊稼漢味道(我還在休假,我們可以再見面,他對我說),而且還鄙視女人:那些女政客,他快被她們笑死了,她們開車技術之爛……而我卻覺得這些頗能助興,我對這些有獨特的性趣。愈來愈神似「我年輕時候的男人」的理想形象,就像《清空》(Les Armoires vides)裡描繪的樣子。來到房子門口,最後的一場戲上演,真棒,我感覺到了,這個除了「愛」之外,找不到其他字眼可以代替的東西:收音機繼續響著〔播放依夫.杜岱爾(Yves Duteil)的〈小木橋〉〕,我的嘴唇輕輕撫遍他的全身,直到他達到高潮,就在這裡,他的車裡,洛賽爾巷內。之後,我們在對方的眼裡失去蹤影。今晨,醒來的時候,我重溫那場景,一遍又一遍。他回到法國還不到一星期的時間,跟在列寧格勒的時候相較,已經是如此的難分難捨,動作如此的大膽放縱(我們幾乎施展了所有的床上功夫)。我做愛跟寫作的時候總是這樣,彷彿完事後我就要死了似的(再說,昨晚在回程的高速公路上,確有乾脆出車禍、死掉算了的意念)。
七日星期五
慾望之火沒有熄滅,相反地,伴隨著更痛的苦、更強的力道重燃了。他不在身邊的時候,我已經看不清他的臉孔了。就算我倆在一起好了,我看他的感覺也無法像從前一樣,他有了另一副面孔,如此的親近,如此的一目了然,像是替身。幾乎總是我採取主動,但卻聽由他的渴求來進行。昨晚,他打電話來時我已經睡了,司空見慣。緊繃、幸福、慾火。他喃喃唸著我的名字,重重的喉頭音,重音和下顎顫音落在第一音節,第二音節於是顯得益發短促,「安──妮」,從來沒有人這樣叫過我的名字。
我想起我在八一年間抵達莫斯科時(接近十月九日)眼前的那位蘇聯士兵,如此的高大、那般的年輕,我的淚水情不自禁地灑落,落在當時這個幾乎可說是完全存在想像裡的國度上。現在,我有點像是在跟那位蘇聯士兵做愛,好像七年前的所有情緒一股腦地全宣洩在S的身上。一個星期以前,我還看不出任何火花。借用安德烈.布魯東(Andre Breton)的句子:「我們做愛,如陽光熾熱,如棺槨蓋定,砰然有聲。」差不多這意思。
八日星期六
勒本漢街的小套房。剛開始有點懶懶的,漸漸溫柔甜蜜,終至精疲力竭。在某個時刻,他對我說「我下星期再給妳電話」=這個週末我不想見面。我微笑以對=沒問題。心痛、嫉妒,雖然明明知道把見面的間隔拉長一點是比較好。我陷入狂歡之後的疑慮不安之中。我好怕自己顯露出黏人、年老色衰的樣子(因為年老色衰所以黏人),我不禁自問該不該玩點欲擒故縱的把戲,孤注一擲!
十一日星期二
昨天晚上他十一點離開。這是第一次接連著幾小時做愛,沒有喘息的時間。十點半,他起身。我說:想要點什麼嗎?他說:要,妳。二度進房。十月末將會多麼難熬,因為月底他太太就來了,我們的關係也等於劃上句號。但他會這麼輕易地放棄嗎?我覺得他似乎非常眷戀我們在一起時迸出的快感。聽,他放縱情慾,激情性愛情不自禁的叫聲!是喬治亞人的尋歡禮儀!現在他竟敢問我:「妳爽嗎?」剛開始沒有。今晚,首度嘗試肛交,儘管這是他的頭一遭。的確,有個年輕男子在自己床上是能教人忘卻年齡和歲月。這分對男人的需要,是如此的恐怖,幾可比擬對死亡的渴望,而它一直掏空我的心靈,何時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