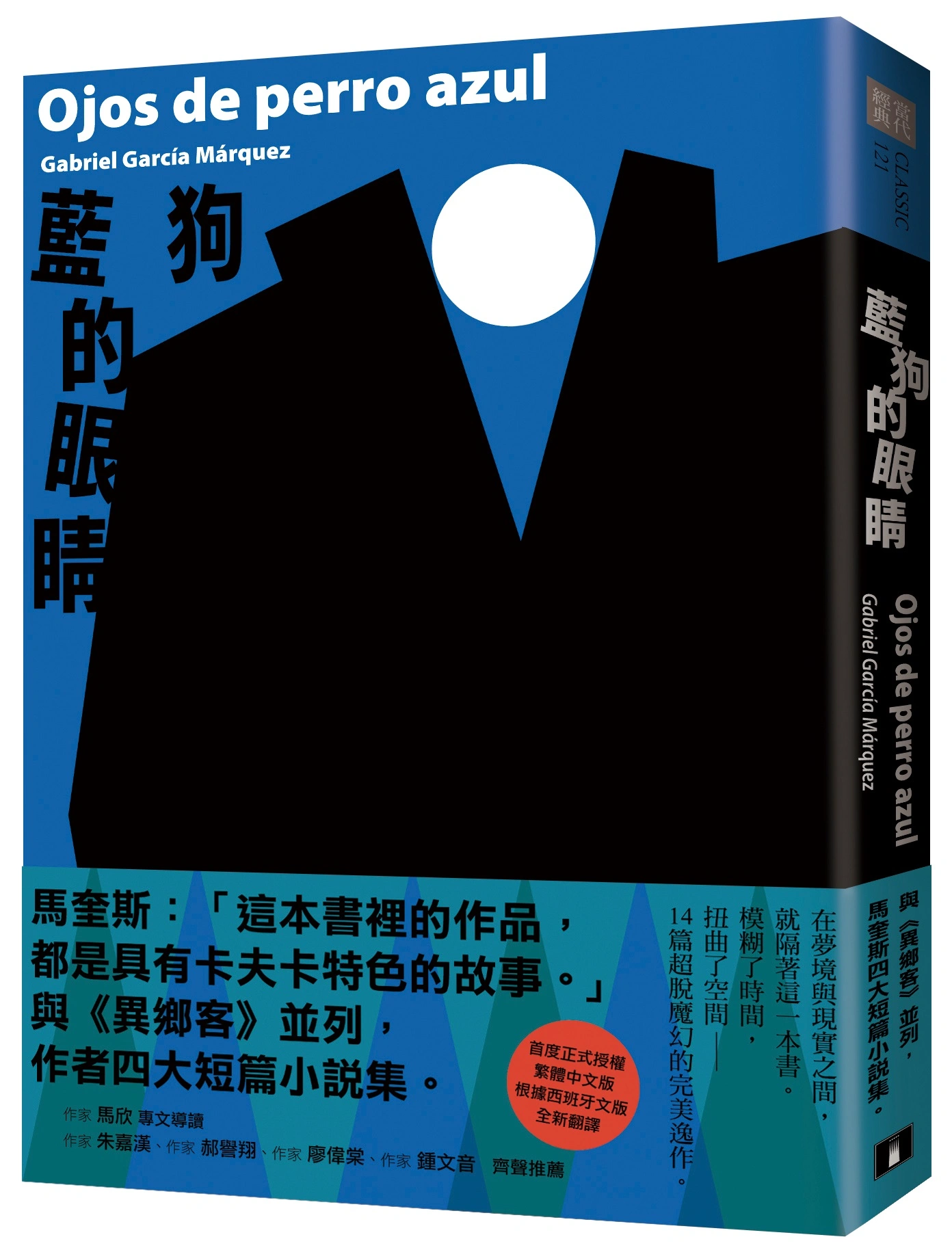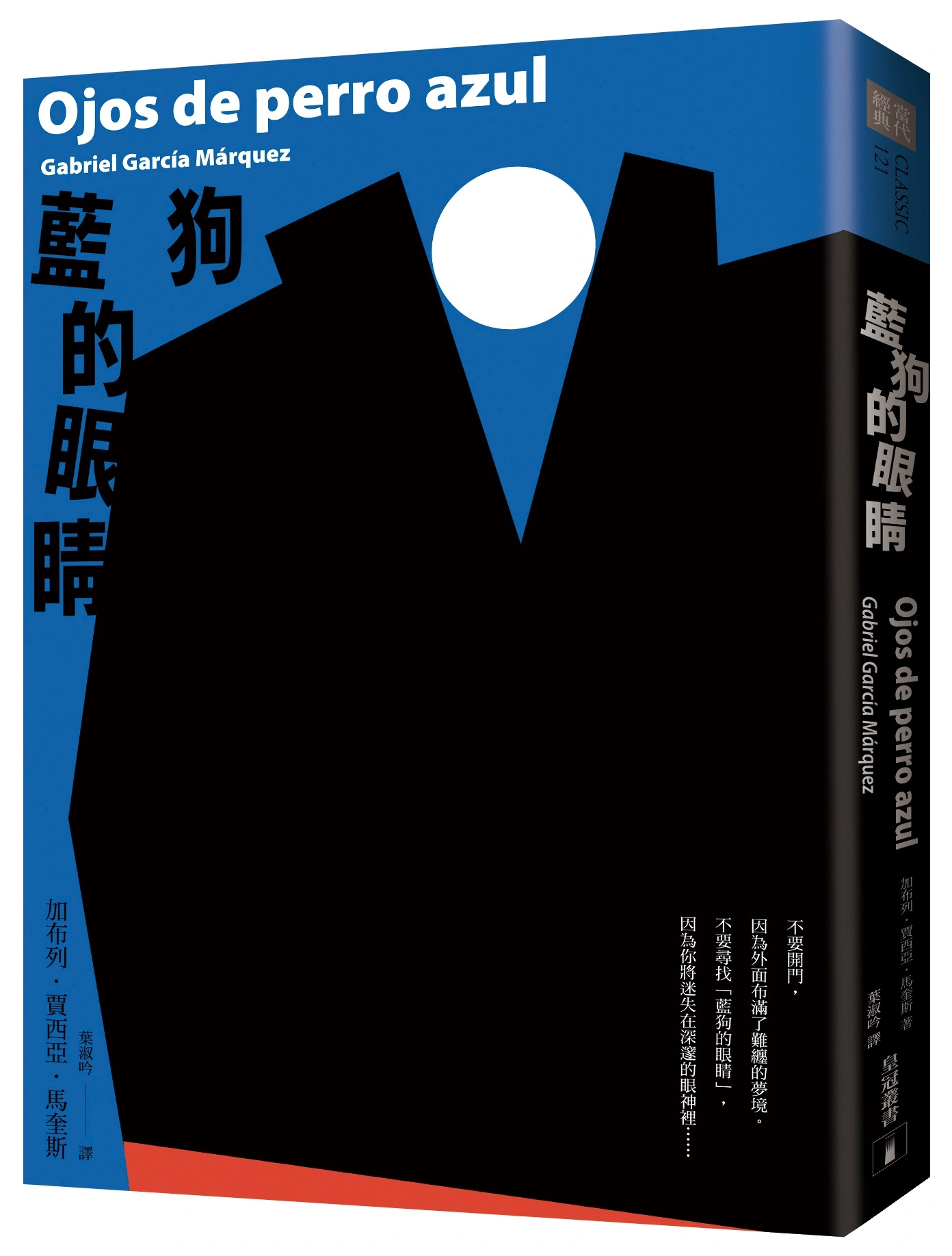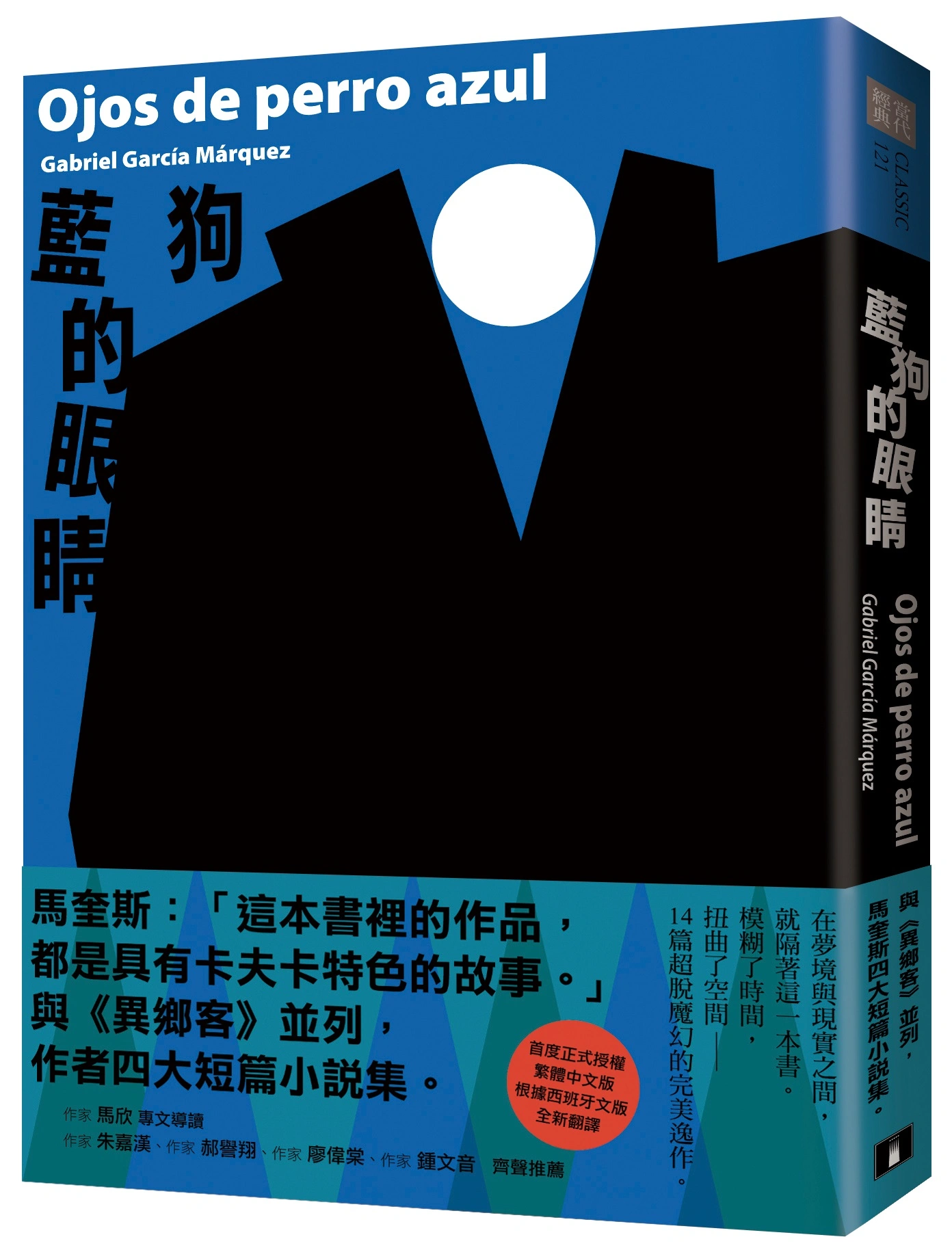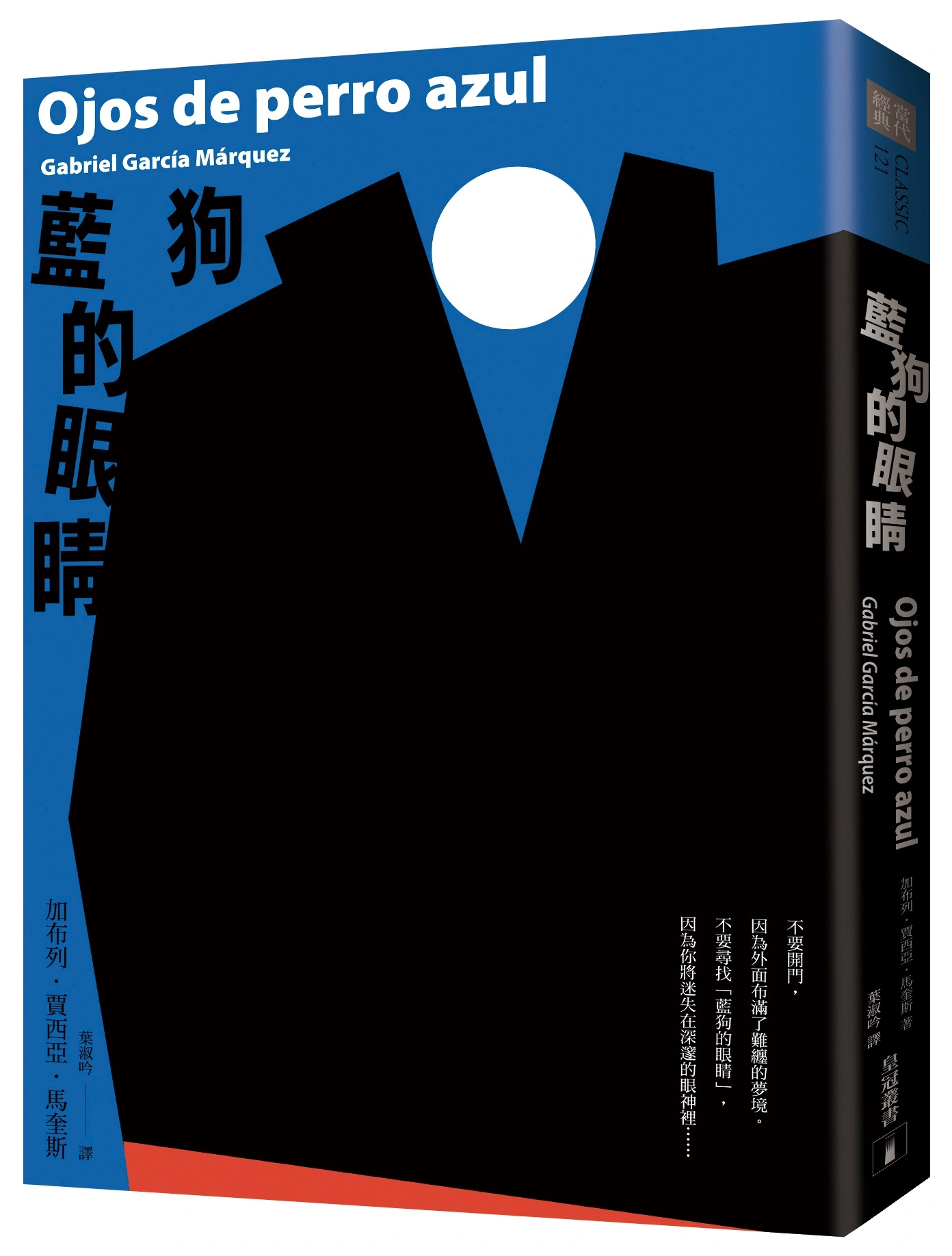內容試閱
第三度認命
那個噪音又出現了。他已經很熟悉那個冰冷、尖銳的噪音從天而降,但此時此刻,他感覺到高亢的聲音充滿痛苦,突然之間難以習慣。
那聲音是隱約的,是尖銳的,在他腦殼裡咆哮。他的頭骨內有個蜂巢。那聲音彷彿連續上升的螺旋,越來越響亮,在腦內衝撞,引起失衡、走調的震動,伴隨身體的一定節奏,搖晃他的脊椎。有個東西與他的人體結構格格不入;有個東西「曾經」正常,此刻卻如同一隻骨瘦如柴的手拿著鐵鎚在他的腦袋裡狠狠地猛敲,勾起他這一生所有嘗過的苦澀。他頭痛欲裂,一股猛烈的衝動浮現,他想握緊拳頭,用力壓住浮起青筋和紫筋的太陽穴。他多麼希望舉起靈敏的手掌,逮住此刻以鑽石的鑽頭般鑿著他的噪音。他發著高燒,當他想像那個噪音在他發燒滾燙的腦袋瓜裡,沿著每個飽受折磨的角落追著他,不禁像隻貓一樣瑟縮成一團。他會捉住那個噪音,但不可能。那個聲音有著滑溜溜的皮膚,可以說沒有形體。但是他打算用他熟習而來的策略來捕捉,使盡所有絕處逢生的力氣,牢牢地抓住它久久不放。他不容許它再次刺穿他的耳膜,從他的嘴巴,從他的每個毛孔,或從他的眼睛竄出,當它呼嘯而過,他的眼珠子會應聲剝落,瞎了的眼只能從一片駭人的黑暗的最深處,瞪著那個噪音逃之夭夭。他不容許那個噪音猶如碎玻璃或是碎冰塊擠壓他的腦壁。那個噪音就是這樣:沒完沒了,就像孩子一頭撞上水泥牆;就像對所有自然界硬物的猛力衝撞。但是只要能圍捕它,逼它無處可逃,就不用再受折磨。他要一步步地斬除那個如影隨形、變化莫測的形體,然後抓住它。現在,他終能使盡所有力氣,搾壓它,把它扔到人行道上,狠狠地踩踏,直到它真的一動也不動,直到可以氣喘吁吁地說,他已經殺死那個折磨、逼瘋他的噪音,此時此刻那個噪音躺在地上,像任何普通的東西,完完全全失去了生命的氣息。
但是他沒辦法壓住自己的太陽穴,他的手臂萎縮了,此刻變得像是侏儒的手臂,小小的,肉肉的,胖胖的。他試著甩甩頭,他甩完後,那個噪音反而用力扎根在腦殼裡,擴大變硬,並深深受到引力影響。那個噪音變得沉重和堅硬,就因為太重太硬,若是逮到了,肯定在摧毀它時,就像是拔除一片片鉛製花瓣一般吃力。
他「以前」也曾感覺過這個噪音頑固的存在。比方說,他在自己第一次死去的那天感到它的存在。當時,他看見一具屍體,卻發覺那具屍體竟是自己。他看了看,摸了摸,他感覺自己摸不著,不具形體,甚至根本不存在。他是一具實實在在的屍體,他逐漸能感覺得到,死亡正行經他那具生病的青春肉體。屋內的氛圍開始變得凝重,彷彿灌滿水泥,而他就在水泥塊的中央—那些曾在空氣還沒變成水泥塊時的物品都在原處,他被仔細地安置在一具棺材裡面,棺材是水泥的,但也是透明的。那一次,他的腦袋裡也出現「那個噪音」。他感覺他躺在棺材另一端的腳板彷彿距離好遠好冰冷,那一端放著一顆枕頭,因為棺材實在大大,不得不做調整,好讓他死亡的身體能穿上他的最後一件新衣裳。他一身白衣,下顎綁著一條手帕。他感覺自己穿著壽衣很好看,有一種死亡的美感。
他躺在棺材裡,準備下葬,然而他知道自己並沒有死;如果他想要起身,很容易就能站起來,至少是「靈魂」的部分吧。但是沒有必要,還是讓自己死了躺在那裡吧—為了「死亡」而死,他生的病就是死亡。許久以前,醫生已斬釘截鐵地對他的母親說:
「夫人,您的孩子生了重病:他死了。不過啊,」他繼續說。「我們會盡一切所能救他遠離死亡的威脅,我們會採用一套複雜的自動供給養分系統,延續他的器官功能運作。唯一失去的是人腦功能和肢體動作,我們會從他身體繼續的正常成長,知道他還留著一口氣。這只是一種叫『活體死亡』的病,一種真實和真正的死亡……」
他還記得那些話,不過已經模糊不清。或許他其實從沒聽過,只是他的大腦在傷寒侵襲而體溫升高當下的想像。那時他正處在癲狂狀態,當時他剛好讀了防腐處理法老王的故事,當開始發燒,他感覺自己化身為故事裡的主角。他的生命自此出現一塊空缺,從那時起他開始無法分辨、或記不得哪些是他在瘋癲中的想像,或者哪些是真實人生的事件。因此,他現在滿腹疑惑。或許醫生從沒說過這種詭異的「活體死亡」,這有悖常理,自相矛盾,很簡單的道理就是:它們相互牴觸。這讓他開始懷疑他其實早就死了,十八年前就已經死了。
從那時開始—他七歲死掉那一年,他的母親派人替他訂做了一個綠色木頭的小棺材,但那是給小孩用的。醫生叮嚀要給他做個大一點的棺材,一個成人能躺進去的尺寸,因為那個小小的棺材,可能會妨礙肢體的成長,他會長成一個畸形的死人,或不正常的活人,或者停止生長會讓人無法察覺他的病情是否好轉。他的母親聽進忠告,幫他訂做了一個給成人躺的、比較大的棺材,然後在他的腳底塞了三個枕頭,好調整空間大小。
很快地,他在棺材裡長大,因此每一年都會有人替他拿出一點最後那個枕頭裡的填充羊毛,給他空間繼續成長。他就這樣度過了大半輩子。十八年過去了(現在他二十五歲),他長到最終的正常身高,不過木匠和醫生估算錯誤,那口棺材多了半公尺長。他們以為他會長到跟他那個半個野蠻人的巨人父親一樣高,但並沒有這樣。他從父親身上唯一繼承到的是一臉鬍子,那是濃密的藍色鬍子,他的母親總是幫他修剪整齊,讓他能儀容端正地躺在棺材裡。大熱天時,他會覺得鬍子特別不舒服。
但是比起「那個噪音」,他還有個更擔心的東西,那就是老鼠。更準確地說,他在這個世界上,從小開始最擔心害怕的莫過於老鼠。這種噁心的小動物就是被他腳邊燃燒的蠟燭氣味吸引過來的,牠們咬破他的衣服,他知道牠們很快就會啃咬他,吃掉他的身體。有一天,他清楚地看到了牠們:那是五隻胖老鼠,身體滑溜溜的,牠們從桌腳爬上棺材,打算吃掉他。等到他的母親發現時,他就只剩下殘骸,剩下堅硬冰冷的骨頭。但最令他毛骨悚然的,不是被老鼠啃食殆盡,因為只剩下骨架他還是能繼續活下去;他最感到痛苦不堪的,是自己對那種動物與生俱來的恐懼。光是想著那些毛茸茸的小動物跑遍他的身體,從他的衣服皺褶鑽進去,用那冰冷的腳摩擦他的嘴脣,他就忍不住起了一身雞皮疙瘩。其中一隻甚至爬上他的眼皮,想啃咬他的眼睛。他看見老鼠是那樣巨大,那樣醜陋,奮力想要咬穿他的視網膜。這時他相信他將再一次面臨死亡,把自己完全交給逼近的狂風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