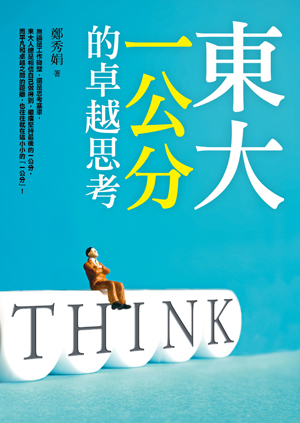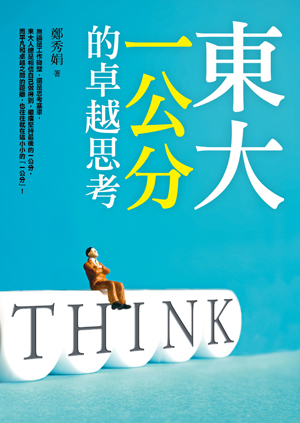內容試閱
幫助你登上高峰的「低氧腦」
聽到我要去念東大,而且又是拿留日獎學金時,台灣的家人和朋友都為我感到驕傲。我還記得,甫到日本,有個年輕的日本女生一知道我是東大生,便目不轉睛地看著我,興奮地說,自己這輩子終於認識了一位東大的「真人」了!
進入東大當外國人研究生,我的目標是考上東大社會情報學研究所,成為正式的東大學生。但是,我周遭的人,包括在東大念書的台灣學長、指導教授,都建議我去申請其他的科系。
他們苦口婆心地勸我,日本交流協會只支付兩年的獎學金,不要浪費時間,應該趕緊報考其他的學校或科系。他們提出的理由是,從來沒有台灣人能夠考上東大社會情報學研究所,而且,就算是日文流利的外籍留學生,也很少人能夠第一年就考上。
於是,我開始思考,還有哪些學校可以選擇,並且進一步嘗試去思考、了解各種可能性。我蒐集了設立傳播相關科系的大學資訊,也詢問東大社會系的上野千鶴子老師是否能收我當學生。
此外,我也評估了自己現有的資源及留學目標。自從有了留學念頭之後,我對於留學期間要做什麼、該完成什麼目標,都已經有非常清楚的概念與想法:
第一、體驗日本的生活。
第二、好好念書。
第三、拿到學位。
第一論「體驗日本的生活」,東京是日本的經濟文化重鎮,觀光景點及文化活動都勝過其他城市。
第二論「念書」,撇開東京大學響亮的名氣不說,東大本身的教育資源十分豐富,而社會情報學研究所已有四十幾年的歷史,師資陣容、藏書量、學者人數等資源都比其他學校優渥,想要念書、做研究,這裡是絕對首選。
第三論「學位」,雖然大眾傳播的許多理論來自社會學領域,但對於傳統的社會學理論,我完全是個門外漢,即使考上了社會學,即使上野老師肯收我當門生,要在兩年內完成論文寫作,順利拿到社會學碩士學位,也是一大挑戰。
評估所有主觀及客觀條件後,我毫不猶豫地選擇報考東大社會情報研究所。確定目標之後,接下來就是徹底去執行。我花了很多時間準備入學考試,先研究過去入學考試的考古題,發現它們都是申論題,內容包羅萬象,除了傳播理論、傳播法規之外,日本國內時事及世界上曾發生的重大新聞事件都在出題範圍之內。因此,我買了幾本有如百科全書般厚重的日本時事年鑑來做研究。
每年定期出版的《朝日Keyword》(現已停刊)、《智慧藏》(現已停刊)、《現代用語的基礎知識》等書刊,幫助我瞭解日本最新的時事和社會動向。
這些年鑑分門別類整理出媒體、政治外交、金融等不同主題的內容,不過,每本年鑑的編者對於同一個新聞事件又會有不同的立場及見解,因此,我特別蒐集了好幾個不同年份、不同作者編著的年鑑,藉以幫助我鑑往知來,從不同角度來理解、詮釋、思考這些社會現象和事件。
為了能夠讀懂這些年鑑,我先查字典,把看不懂的漢字全部標上日文發音,並背下書中艱澀的內容,再嘗試用自己的話來重新描述整個新聞事件,然後再用日文寫下,請日本學長幫忙修正,不斷地反覆「閱讀」、「消化」、「重組」、「輸出」這幾個步驟,努力寫出符合日文文法的申論題。
為了順利考取東大研究所,我讓自己隨時處在「低氧腦」的狀態。「低氧腦」這個名詞是我自創的,意即「就算面對惡劣的環境,仍然專注地向前邁進」。馬拉松選手在接受長跑訓練時,會特地挑選在氧氣稀少的高地進行跑步練習,讓自己的身體適應低氧狀態;接受過低氧訓練的馬拉松選手,經歷了惡劣環境的考驗,以後不管到任何地方比賽,都可以應付多變的天候和環境。
那段日子,我努力調適心情,讓心中的雜念和外界的誘惑徹底淨空。從確定要考東大的八月底開始,一直到隔年二月初考試為止,我每天做的事情都一樣:念書、上課、吃飯、運動。早上八點到圖書館等開門,念書念到晚上九點圖書館關門才離開,除了圖書館休館日外,沒有一天間斷。
皇天不負苦心人,經過近半年的埋首苦讀,我終於通過了研究所入學筆試,接下來就是面試。
我記得,主考官之一就是我在第一堂課差點因為打瞌睡從椅子上跌下來的授課老師,他在問完所有專業問題後,抬頭看了一眼牆上的鐘,發現還有一些時間,於是又問了我一個基本問題:「我們上課時說的日文,你聽得懂幾成?」
我老實地說:「日常的會話大概是八成,但是上課的內容大概是七成吧。」
一般人可能認為,主動坦承自己日文程度不佳,大概很難考上以入學審核嚴格出名的東大研究所。但是,我不僅考上了,而且還成為「東大社會情報學研究所」創系以來第一位錄取的台灣學生。
這段期間鍛練出的「低氧腦」,讓我往後不管求學或工作,都能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完成目標,也成功地克服語言障礙的關卡,在東大的求學生活有如倒吃甘蔗,漸入佳境。此後,當我面對其他困難,或是覺得自己快要撐不下去時,就會回想起這段寶貴的經驗,讓它幫助自己勇敢地走下去。
專注在當下
在準備報考東大研究所時,我從來沒有想過,如果失敗的話,該怎麼辦?因為我全神貫注地朝向艱鉅的目標前進,連思考B計畫的時間和心力都沒有。後來,我才知道,當初我在做的事,其實類似「瓦倫達效應」(The Wallenda Factor)。所謂的「瓦倫達效應」,是指不考慮失敗或成功後的結果,只專注於當下的工作。
瓦倫達是一名傑出的高空雜技演員,每次,當他走在空中鋼索上時,總是把精神專注在如何走完鋼索。高齡七十三歲的他從未有過失敗經驗。然而,一九七八年,他在波多黎各進行走鋼索表演時卻不幸失足身亡。他的妻子也是一位高空雜技演員,在他死後不久回憶說:「瓦倫達在掉下去前的好幾個月裡,一直在想掉下去的事,這是他頭一次興起那樣的念頭。在我看來,他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不要讓自己掉下去,而不是好好地走過鋼索」。
如果,我們在做任何事時,總是先想到「事情有可能失敗」、「失敗了該怎麼辦」,就會很難專注在當下,甚至因為太過擔心失敗,反而不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