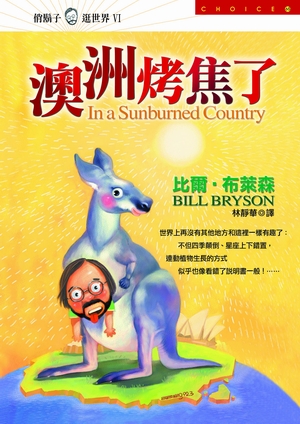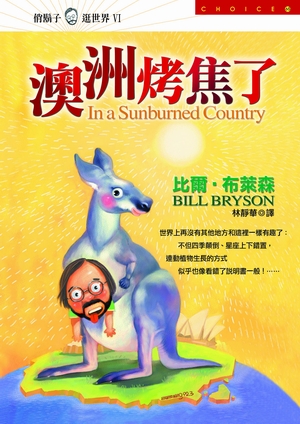內容試閱
一頭栽進了澳洲『裡面』
雪梨人也許並不自知,不過他們都有個明顯的特質,就是樂於向外來的訪客介紹他們的城市,我就有另外一個這樣的參觀機會,這一次是『雪梨前鋒晨報』(Sydney Morning Herald)的記者蒂德蕾‧麥肯,一位甫步入中年的、和藹可親的女記者。蒂德蕾帶著一位年輕的攝影師格蘭‧杭特到飯店來接我,我們步行前往雪梨博物館。這是一棟造型優美時髦的新建築,它的目的是想不失有趣又富有教育意義,然而兩個目標都沒達成。你會發現館內的展品在陳列上都經過精心設計--成箱的移民藝術品,一間陳列室內擺滿了一九五O年代迄今的各類雜誌--但是參觀完畢,你會發現你還是不很瞭解它的真正用意。不過我們倒是在館內的咖啡廳喝到很棒的拿鐵,蒂德蕾就在這個時候說明這一天緊湊的行程。
待會兒我們要散步到圓環碼頭(Circular Quay),搭渡輪過港到塔隆加動物園(Tarongar Zoo)碼頭。
我們不去參觀動物園,但是會步行走一趟小天狼星灣(Little Sirius Cove),再爬上陡峭的克雷蒙角(Cremorne Point)樹林去蒂德蕾家拿毛巾和『布基板』,再坐車去曼力(Manly),一個可以俯瞰太平洋的郊區海灘。在曼力用過午餐後,我們就可以換上泳裝,帶著『布基板』下海--
『對不起我打個岔,』我打斷她的話,『到底什麼是「布基板」?』
『喔,那個很好玩,你會喜歡的。』她輕鬆的說,但我覺得她有點在迴避我的問題。
『是,但那是什麼?』
『一種水上運動,好玩極了。是不是好玩極了,格蘭?』
『好玩極了。』格蘭附和說。他和任何人一樣,反正底片有人付錢,正忙著按相機的快門。喀嚓、喀嚓、喀嚓,正說著,他迅速拍下三張我與蒂德蕾談話的照片。
『可是到底要怎麼玩呢?』我不放鬆。
『那是一塊迷你衝浪板,你帶著它划水到海上,等大浪過來你就騎著浪衝回岸上。很簡單,你會喜歡的。』
『萬一有鯊魚呢?』我不放心。
『喔,這裡幾乎沒有鯊魚。格蘭,上一次鯊魚咬死人到現在有多久了?』
『喔,幾百年了。』格蘭說,想了一下,接著說:『至少有兩個月了。』
『兩個月?』我脫口大叫。
『至少。鯊魚的危險性都被過份誇大了,』格蘭又說:『過份誇大。裂流的危險性還大些。』說著,他又繼續拍照。
『裂流?』
『就是以某種角度衝向海岸的暗流,有時會把人捲進海裡。』蒂德蕾解釋,『不過,你放心,這種事不會發生在你身上。』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會在你身邊保護你。』她平靜的笑著說,乾掉杯子裡的拿鐵,提醒我們得繼續上路了。
三個小時後,我們完成了其他各項活動,來到曼力附近一處叫淡水海灘(Freshwater Beach)的海邊。這是一個大U字形的海灣,四周圍繞低矮的灌木林。在我眼中算是大浪的凶猛海潮,不斷從巨大而喜怒無常的海洋衝上沙岸。遠處幾個有勇無謀的傢伙穿著濕透的泳裝,正朝向冒著白色泡沫、猛烈拍向海岬的海浪衝過去;近一點,三三兩兩的泳客划著衝浪板,一而再、再而三的往具有爆發威力的浪花堆裡鑽進去,似乎樂此不疲。
蒂德蕾一再催我們下水,彷彿急著想去喝那鹹死人的飲料,於是我們開始脫衣服--我故意慢吞吞的,她則是迫不及待--脫到只剩她早先指示我們穿在外衣底下的泳裝。
『萬一你被裂流捲走,』蒂德蕾說,『要訣是不要驚慌。』
我望著她,『你的意思是叫我平靜的淹死?』
『不,不,只是要冷靜。千萬不要逆著海浪游,要越過它。萬一還是不行,你就這樣揮手--』她大幅度的、懶洋洋的揮手,大概只有澳洲人在海上快溺死了才會有這樣的反應,『等救生員來救你。』
『萬一救生員沒看見我呢?』
『他會看見你的。』
『萬一沒看見呢?』
但是蒂德蕾已經涉水走了,她的腋下夾著『布基板』。
我害羞的把上衣丟在沙灘上,身上只剩一條鬆垮垮的泳褲。格蘭大概從來沒在澳洲的海灘上看過如此怪誕罕見的景象,此刻更是不得閒,抓起相機拼命對著我的肚子照特寫,喀嚓、喀嚓、喀嚓、喀嚓,他一路跟著我下水,相機一路快樂的唱著。
嘆一口氣,我慢吞吞走進淺綠鑲乳白色的海水中。海灣出乎意料的淺,我們涉水走了大約一百英尺,海水仍然只到我們的膝蓋,不過感覺到水流已相當強勁--如果你不稍稍使點力,很可能會被沖倒。再往前走五十英尺,水深已到腰部,海浪開始轉強。如果在西班牙陽光海岸珊瑚礁似的海水泡過幾個小時,以及在緬因州一走進冰冷的海水立即後悔的兩次經驗略去不算,我幾乎可以說毫無下海的經驗,而且老實說,我實在不善於在變幻莫測的海水中行走。蒂德蕾則高興得尖叫。
她教我如何使用衝浪板。它的原理很簡單。浪來時,她便跳上衝浪板,順著浪頭衝出去,大約有數碼的距離。接著格蘭轉個身,衝得更遠。毫無疑問,看起來確實好玩,好像也不太難。我有點躍躍欲試。
我擺好姿勢,等待第一個浪,跳上衝浪板,結果卻像鐵錘般沈下去。
『你是怎麼跳的?』格蘭大惑不解。
『不知道。』
我再試一次,仍然相同的結果。
『不可思議。』他說。
接下來半個小時,他們兩人先是帶點好笑,繼而有些詫異,最後只有憐憫的看著我,因為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消失在海浪中,而且被海潮捲走的距離大約有愛荷華州的波克郡那麼大。每次浪頭過來,我就會消失一段時間,然後浮出水面,氣喘吁吁的分不清東南西北,因為我所站立的地點離前一個浪頭的距離,從四英尺到一點四英里不等,然後立即又被另一個浪頭刮走。不久,海灘上的人都紛紛站起來下注,大部分的人都同意,他們絕對做不到我那樣。
以我的觀點,我的每一次海中經驗基本上大同小異。我努力模仿蒂德蕾教我的優雅的踢水動作,盡量不去想我身在何方,以及我很可能會溺斃的事實。如果不去做負面的評斷,我想我的表現還算差強人意。我不能假裝我玩得很開心,但是人人都樂意涉足這樣的險境還能期待樂趣無窮,對我而言的確是不可思議。今天我是豁出去了,我知道,這一切終將結束。
或許是缺氧,我幾乎已迷失在我自己的小小天地裡,正當我準備要再衝進浪頭時,蒂德蕾一把抓住我的手臂,沙啞著嗓子說:『小心!一隻藍母。』
格蘭立刻露出警覺的表情,『在哪?』
『什麼是藍母?』我大驚,以為又有什麼我沒被告知的危險。
『一隻藍色水母。』她說,指著一隻小小的、別地方稱做『葡萄牙戰士』的水母。(後來我從一套名為《澳洲的致命生物》的皇皇巨著中的第十九冊,看到有關這種生物的介紹。)我目送牠漂過去,詫異的眨眨眼。牠看起來一點也不起眼,像一只拖著一根線的藍色保險套。
『牠危險嗎?』我問。
疲憊、傷痕累累、幾近全裸、又淹得半死的我站在海水中發抖,但在我們聽到蒂德蕾的回答之前,不妨先讓我引述一段她後來刊登在週末版『前鋒晨報』的一篇文章內容:
『當攝影師按下快門時,布萊森和衝浪板已經被一波裂流拖行四十公尺。這一波裂流和先前的裂流不同,是從南到北,先前的恰好相反,是從北到南。布萊森不懂,他沒有看到海灘上的警告標語(作者註:這段話千真萬確,不過作者要在此說明,當時他沒戴眼鏡;他信任他的女嚮導;他忙著觀察茫茫大海上有沒有鯊魚出現;而且他拼命忍著隨時可能拉出來的大便。)他更不知道藍水母正往他那邊漂過去--這時候距離他已經不到一公尺--萬一被這種會膨脹的小東西螫到,他可能會有長達二十分鐘的痛苦,如果運氣不好,他還有可能因為過敏反應而一命嗚呼。』
『危險?不。』蒂德蕾回答,大夥兒這時都喘著氣目送藍水母漂過去,『不過,最好不要被牠刷到。』
『為什麼?』
『可能會有點不舒服。』
我以有趣與欣賞的眼神望著她。長途汽車旅行會使人不舒服,硬梆梆的長板凳坐久了會不舒服,單調乏味的對話會使人不舒服,被『葡萄牙戰士』螫到--連愛荷華人都知道--卻是痛不欲生。我忽然想到,澳洲人在面臨處處危機的環境下,已發展出一套對應的新詞彙。
『嘿,又來一隻。』格蘭說。
我們目送另一隻水母漂過去。蒂德蕾仔細察看海流。
『牠們有時是跟著浪過來的,』她說:『我們還是趕緊離開吧。』
我自然不待她說第二遍,拔腿便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