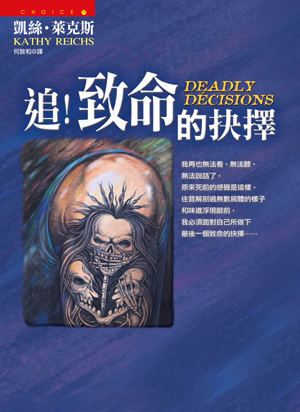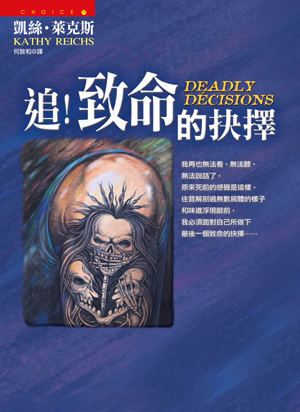路上車輛不多,不到二十分鐘,我便已把車子停在安大略路的街邊。我關掉引擎,環顧四周,緊張的情緒讓胃裡的東西翻攪掀起陣陣噁心的感覺。比起眼前即將進行的冒險,我還寧可做連續十年的雷射磨皮手術。
『迅速酒館』就在我正對面,夾在一間刺青工作室和機車用品專賣店之間。這個地方的破舊程度,和克勞得爾帶來我辦公室的那張有克特在裡面的相片中所看到的差不多。透過那扇模糊不清、上次清洗時間可能是在水瓶座時代沴的玻璃窗,我看見裡面的霓虹燈管亮熾熾打出百威和莫森啤酒的廣告。
我將一罐防身噴霧瓦斯放進夾克口袋,拉上拉鍊,下車,鎖上車門,便向對街走去。才走在人行道上,我就能感受到一陣陣足已搖撼整棟酒館的音樂震動聲響。門一推開,一道混合煙味、汗味和酸臭啤酒味的氣流便向我迎面撲來。
在門內,一個保鏕上上下下地打量著我。他穿著一件黑色T恤,上頭印有一顆嘴形呈尖叫狀的骷髏圖,中間橫過一行字『注定一死』。
『小甜心,』他油嘴滑舌地說,眼睛斜睨著我的胸部。『我好像戀愛了。』
這個男人缺了好幾顆牙,一副流氓惡棍模樣。我完全不理會他的搭訕。
『等妳準備好想來點特別節目的時候,記得回來找我雷米,甜心。』
他用毛茸茸的手摸了我手臂一下,才做出手勢讓我進去。
我從他旁邊走過,心裡只想讓這個已缺了牙的雷米再少掉兩、三顆門牙。
這個地方感覺就像阿帕拉契山的釀酒小屋,只是多了撞球檯、音樂點唱機和鎖在角落鐵架上的電視。酒館裡一邊是吧台,另一邊是沙發雅座,中間的空間則塞滿桌椅。整間酒館黑漆一團,唯有框在吧台和窗戶上的聖誕節燈飾放射出一點點微弱的光芒。
等我眼睛適應這裡的黑暗,才很快將整個酒館掃過一遍。這裡的顧客多半都是男性,衣著邋遢,個個蓄留長髮,看起來就像剛在製片廠演完西哥德族人的臨時演員。這裡的女人都用強力髮膠將頭髮盤繞定型,並把胸部擠進袒肩露背的胸衣中,向世人顯露她們傲人的乳溝。
我沒看到克特。
在我穿過人群走向酒館後半部時,聽見有人叫喊和腳步拖地的聲音。我低下頭,吃力地穿過這群啤酒肚海,幾乎快把自己擠壓貼上了牆壁。
在吧台附近,一個長著拉斯普丁式眉毛、雙頰削瘦凹陷的惡漢站了起來。鮮血從他臉上流下,染紅了他身上的運動衫和掛在頸子上的項鍊。在他對面的一張桌子前,有個胖臉男人怒目瞪著他,手上倒拿著一個莫森啤酒瓶向前揮刺,逼迫他的對手留在座位上。那個拉斯普丁發了聲喊,抄起椅子向這個胖臉男人扔去。我聽見一陣玻璃碎裂聲,這個男人和他手中的酒瓶全一股腦摔在地上。
酒館裡的顧客全擠了上來,空出桌子和吧台高凳,不願錯過這場精彩好戲。保鏕雷米也出現了,他拿著一根棒球棍,一躍就跳上了吧台。
真是夠了。我決定到外面去等克特。
才往大門口走了幾步,我的手臂就被一雙突然伸出的手抓住。我掙扎著,想擺脫這個人的鉗制。但他用的力道很重,我的手臂被他緊緊掐住,肌肉全擠貼上了骨頭。
我憤怒地轉過身,只看見一張特徵鮮明如沼澤短吻鱷的臉。這張臉就架在一根粗短的脖子上頭,帶有一雙如珠子般凸出的眼珠,以及既窄又長突向前和脖子形成一個鈍角的下巴。
抓住我的這個男人噘起嘴唇,吹出一聲尖銳的哨音。拉斯普丁僵住了,一時之間,酒館裡突然全靜了下來,所有人都看向這個吹口哨的人。在這突如其來的寧靜中,只聽見喬治.史崔特悠揚的歌聲。
『嘿,別鬧了,輪到我的「展示與解說」時間了。』這個男人說話的音調出奇地高。『雷米,把那該死的瓶子從塔克手中拿走。』
雷米跳下吧台,插進打架的那兩個人之間,肩上仍扛著那根球棒。他一腳踏住塔克的手腕,稍微施加重量,就讓他手中的半支破瓶子滾落一旁去了。雷米把破瓶子踢開,伸手拉起塔克。塔克張嘴正想說話,卻被抓住我的那個男人打斷了。
『你他媽的閉嘴,聽我說就好。』
『你在和我說話嗎,JJ?』塔克搖晃了幾下,才張開雙腳保持住平衡。
『你最好用你他媽的屁股打賭我是。』
<……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