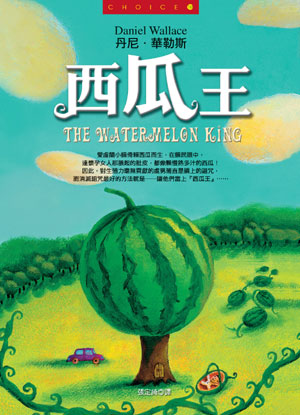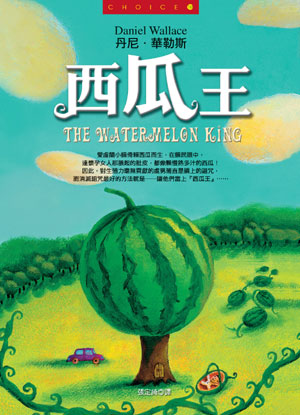內容試閱
下了高速公路幾哩,小鎮已經在望,屋頂和教堂的塔尖露出在長長一排濃密的松林之後。一座空心磚砌的廢棄加油站,顯得老舊、荒涼,加油機生了鏽,變成褐色,孤伶伶站在市鎮邊緣,野草從龜裂的混凝土縫隙裡鑽出來,已然把它當作土壤。加油站的大門早已拆掉,雖然陽光燦爛,室內卻很黝暗,而且有點陰森,所有家具裝潢都拆得精光,只剩四面牆。我試著想像十九年前,她第一天來此,在這個加油站停車,停靠在加油機旁,等候某個身穿油膩工人裝的鄉下老粗,拿塊骯髒的橘色抹布擦擦手,擋著玻璃反射的強光迎上前來。她的頭髮該是赤褐色,用絲巾束在腦後,她的眼睛是綠色的,臉上長著少許雀斑。她的微笑──有人告訴過我,那是她最動人的特徵──想必曾為那個男人綻放。但這些影像一閃即逝。我真的不瞭解當年的她,無法在腦海裡確切重現她的模樣。
姑且假設她趁他加油的時候走下車,繞到加油站後面的女廁所。這兒也沒了門,只有馬桶、褪色的鏡子和洗臉盆。設想她的臉曾經反射在這面鏡子裡,就跟現在我的臉一樣,感覺真奇怪。如果鏡子有記憶,而且能叫出從前儲存的畫面,我就可以拿自己的臉跟她對照,比較兩者多相似,哪些地方一樣,哪些地方不一樣。頭髮、嘴巴、眼睛、下巴。但即使不做這種比較,我也看得出相似之處:我們都對即將發生什麼事一無所知。
『嗨,我叫露西‧萊德。』她對鏡子裡的自己說。或露出她的招牌笑容,聳起肩膀,『露西‧萊德。哈囉。』
我看著自己。我說:『嗨,你好。我叫湯瑪斯。』鏡子舊到照不出什麼東西。比一塊白鐵皮好不到哪裡去,真的,我幾乎看不出自己的長相。白臉、褐髮、綠眼睛。嘴巴、鼻子、耳朵的比例,充其量可說是正常。中等身材。美國人,十八歲,走路微跛。跟鄉下空氣一樣平凡。
我繞到位於加油站前方的電話亭──這種電話亭現在已經找不到了──長方形的玻璃盒,超人換裝用的那種。裡面的電話居然還能用。轉盤撥號。我打給安娜。
『好啦,』我道,『看來我差不多到地頭了。』
『你從加油站打來的?』
『應該說殘餘的加油站,』我道,『它已經不營業了。』
『滄海桑田,嗯?』她道。『十八年了。』
我想到通往我們農場的那條路,一度那一帶除了樹什麼也沒有,那是在所謂的『開發』之前,這兒的發展卻正好相反:樹木都長回來了。我猜再過一陣子,就再也找不到什麼足以顯示加油站曾經存在過的東西。
我說:『我想我該到鎮上去。』
『我想你是應該。』她道。
小鎮就在山坡上,但現在看起來很遠。在長得很高的野草叢中,我看到一塊殘留的老招牌,原本鮮豔的紅、綠、黑油漆,已經破舊褪色,歪向一邊。上面寫著:歡迎光臨愛虛蘭,世界西瓜之都!
『所以,』我道,『再告訴我一次。』
『告訴你什麼?』
『我做這件事的原因。』我覺得口乾,腦子裡聽見自己心跳的聲音。
『因為男子漢都這麼做,』她道,『他要踏上旅程。』
『他為什麼那麼做?』
『找尋自我。』她道。
『我是男子漢。』我道。
『沒錯,』她道,『你是男子漢。』
『所有妳告訴我的那些事,』我道,『關於我母親在愛虛蘭那兒的遭遇,都是真的?』
『是的。』她道。『很瘋狂,但確實是真的。不過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湯瑪斯。一切都改變了。我確定。』
『當然。』我道。
我覺得像一個晚了十八年才奉命偵辦一件破不了的懸案的偵探。安娜和我想出來的計畫是這樣的:四處看看,找人聊聊,問幾個問題。借問,是的,午安,請問妳聽過露西‧萊德這名字嗎?是的,夫人,沒錯:萊德。我們知道她在母親去世後離開伯明罕地區,託庇於父親,他『雇用』她(似乎是照顧沒什麼出路的女兒的權宜之計)巡視他位於本州的幾筆房地產;因為執行這項工作,她於是在愛虛蘭長住下來,最後死在這裡。是的,夫人:人長得很漂亮,據我聽說是如此。謝謝妳。非常謝謝。哦,還有一件事,夫人。順便請問一下:還聽說她去世那天,生下一個孩子,是兒子,取名湯瑪斯。湯瑪斯‧萊德。其實我要找的人是他。是的,夫人。
如果妳看到他,請通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