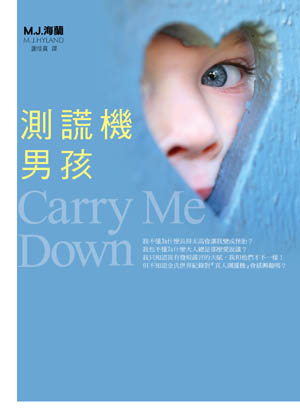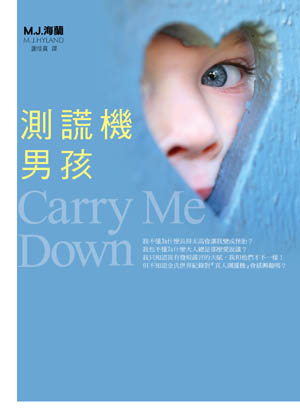內容試閱
那是冬季一月裡一個陰暗的星期天,我和爸媽坐在廚房桌前看書。爸爸背對桌子坐著,腳抵著牆,一本書擱在腿上。我媽坐在我右邊,她的書放在桌上,我坐得離她很近,椅子面向窗戶,靠近爐子的熱氣。
桌子中央有一壺熱茶,我們每個人有一個杯子和一個盤子,盤上盛著火腿和火雞肉三明治,如果這些不夠我們吃飽喝足,東西還多著呢。食品儲藏室裡滿是存糧。
我們不時停止閱讀,聊個兩句,氣氛融洽得彷彿我們合而為一,在看同一本書,而不是三個人各看各的。
這種日子是完美的日子。
小小的方窗外面看得到一條鄉間小路,小路通往哥瑞鎮,遠方則是一片雪地。雪地盡頭視線未及之處有一棵樹,我每天都經過那裡。樹過去兩哩路便是哥瑞國民小學,聖誕假期結束後,我就得回去上課。
在小路一隅,就在我們家前門左邊,有一支路標,上面有兩塊牌子,大牌子在上方指出都柏林的方向,小牌子在下面指著墓園。我們一家人可以再獨處兩天,就我們三個,這樣正合我意。我不希望日子有任何變化。
媽的書快看到最後一頁了,我拿出一付紙牌推向她的手肘。要不了多久,她就會放下書本找我玩牌。我看著她的臉,等她開口。
突然間,她闔上書本站起來。
『約翰,請跟我來。』她會帶我到走廊,遠離我爸。她會帶我到爸看不見的地方,彷彿我是垃圾似的。『現在就來,不要帶書過來。』她說。
我們站在又陡又窄的樓梯下,樓梯通往他們的閣樓寢室——那是樓上唯一的房間。媽倚著樓梯欄杆,雙臂抱胸,雙手的皮膚像粉筆一樣又冷又白。
『我今天的樣子和平常不一樣嗎?』她問。
『沒有啊,怎麼了?』
『你剛剛在廚房的時候又瞪人了,你瞪我。』
『我只是在看妳。』我說。
她不再倚著欄杆,靠過來用雙手按住我的肩膀。她身高五呎十吋,儘管我只比她矮一吋半(譯註:五呎十吋約一百七十八公分、矮一吋半的約翰約一百七十五公分),但她施加手勁,硬逼得我壓低身子,壓到她弓起上半身,屁股向後翹。
『你瞪了我,約翰,你不該那樣瞪人的。』
『為什麼我不能看妳?』
『因為你現在十一歲,不再是小嬰兒了。』
我們的貓咪克里托發出叫聲,惹得我分心。牠和初生的小貓們關在樓梯下的儲物間。我想去看克里托,但母親更用力地按壓我的肩膀。
『我只是在看妳嘛。』我說。
我想跟她說盯著東西看並不幼稚,但她手臂的重量壓得我渾身打顫,抖得說不出話。
『為什麼?為什麼你非要那樣瞪我不可?』她問。
她弄痛我的肩膀了,手勁大得驚人。當她坐在桌前或我的床尾和我說話、逗我笑的時候,她看起來就會輕盈一點、嬌小一點,也漂亮一點。現在我生氣了,氣她又高又大又重,氣她把我生得如此高大,遠遠超出同齡的人。
『我也說不上原因,我就是喜歡看妳嘛。』我說。
『也許你應該改掉這個習慣。』
『為什麼?』
『因為會嚇到人哪。你那樣瞪人,誰都會覺得緊張的。』
『對不起。』我說。
她放開我的肩頭,站直身子。我靠上前去,親了她唇邊一下。
『好啦,沒事了。』她說。
我又親她一下,伸出手臂攬著她的脖子想要抱她,但她推開我。『不要,這裡好冷。』
她轉身,我跟著她回到廚房。
爸深色的鬈髮亂糟糟的,劉海垂下來蓋住眼睛。『把門關上。』他說,但目光沒有離開書頁。
『已經關了。』我說。
『好,那就別打開。』
他對著手上的書《顱相學與罪犯的頭顱》微笑。
我爸已經三年沒有工作了。自從我們和奶奶同住,他就沒做過事。在我們搬進奶奶家之前,他在威克斯福特當電工,但他討厭那份差事,每晚下班回家後都說他痛恨工作。現在他不上班,窩在家裡看書,說是在準備三一學院(譯註: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是愛爾蘭歷史最悠久的大學名校,出過多位知名作家。)的入學考試,還說他應該能輕鬆考上,因為他去年做過門薩協會的入會智商測驗,成績亮麗。(譯註:門薩協會的宗旨是促進高智商人士的交流,入會唯一條件是在智商測驗取得高分)
『妳看窗外,』我對媽說:『雪花是斜斜地飄下來耶。』
『對耶,看起來很像麵粉過篩吧?』她說。
『但麵粉過篩不會斜斜地落下來啊。』我說。
她伸出舌頭舔嘴角,這一舔便沒把舌頭縮回去。我俯身過桌子去摸她舌頭。
『妳的舌頭冰冰的。』我說。
爸看看我們,媽緊緊閉上嘴巴。
『我像蟋蜴嘛。』她說。
她對我微笑,我也報以笑容。
『真是一對怪人。』爸說。
克里托不叫了。大概是聽見我們說話,知道我們在附近令牠覺得心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