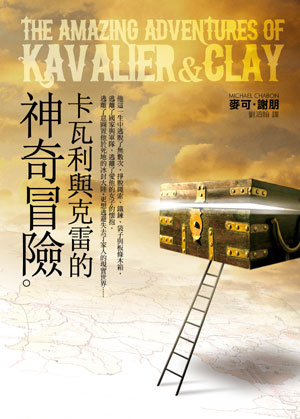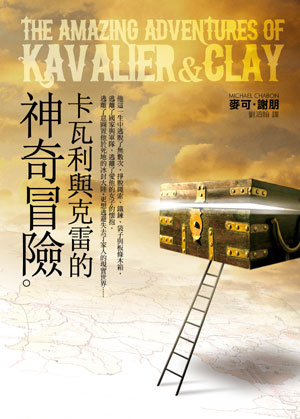內容試閱
孔恩布魯遞了支菸給他,替他點燃,然後走向扶手椅坐下,也替自己點了支菸。喬瑟夫‧卡瓦利和負責看管魔像的長老都不是第一個來找他幫忙的人,先前也有人希望能利用他對付監獄牢房、束縛衣和鐵籠的專長來解開專制國家的邊防大鎖。不過在這天晚上之前,他全都拒絕了,倒不只是因為這樣的要求不實際或非屬其專長,而是手段太過極端且時機尚未成熟。然而此刻,他坐在椅子上,看著從前的學生絕望地翻著皮夾裡一式三份的複寫文件、火車票和蓋了章的出境卡,孔恩布魯還算靈敏的耳朵聽到了巨大鐵鎖扣上鎖頭的哐啷聲,關於這點他毫不置疑。移民署在亞道夫‧艾克曼的領導下,已經不只是憤世嫉俗地敲詐勒索,而是光天化日,令人髮指地偷竊了。申請人付出所有,換來的卻是空無一物。英國、美國閉門坐視──喬瑟夫還是因為有個美國姑姑的堅持和他僥倖在蘇聯國家出生的地緣關係,才終於拿到美國入境簽證。而同時在布拉格,連一堆老舊無用的河底淤泥都難逃入侵者巧取豪奪的命運。
『我可以把你送到立陶宛的維爾拉,』孔恩布魯終於開口,『到了那裡,你就得自己想辦法。梅麥爾已經落入德軍手裡,或許你可以從普利庫爾那裡出去。』
『立陶宛?』
『恐怕非得如此不可。』
過了一會兒,男孩點點頭,聳聳肩,然後在一只刻有克羅采幣與霍夫青俱樂部黑桃標誌的菸灰缸裡捻熄手上的菸。
『不要老想著從哪裡逃,』他引用孔恩布魯常說的一句老話,『把煩惱留著去擔心往哪裡逃。』
*
裝著布拉格魔像的箱子,完全遵照猶太律法的規定,只是個簡單的松木箱,但卻與門同寬,長度足以容納兩個青春期的男孩頭對著頭或腳對著腳躺平。木箱就放在這個空房間的正中央,在兩個結實的鋸木架後方。雖然經過了三十幾年,但這房間的地板看起來還很新,光亮平滑,一塵不染,牆上的白漆也清潔無垢,甚至還有點新漆未乾的氣味。在此之前,喬瑟夫總是盡量不去思索孔恩布魯這個逃脫計畫中的怪誕之處,但在這麼一個彷彿不受時間拘束的房間裡,看到這麼一個巨大的棺材,一股悚然不安彷彿沿著他的脊椎與頸背爬了上來。孔恩布魯也一樣,慢慢走近大木箱,顯然沒什麼信心;伸出的手也遲疑了一會兒才碰到松木箱蓋。他小心翼翼地繞著木箱,輕撫著釘子頭,數著釘子的數目,觀察釘子與蝶式鉸鏈的狀況,也檢查鎖著鉸鏈的螺絲釘是否完整。
他們把魔像搬出公寓,再用借來的斯柯達靈柩車送回葬儀社──孔恩布魯在一九○八年學會開車,他說是由法蘭茲‧霍夫青的高徒漢斯‧克魯茲勒親自教授的──這一路上沒有發生任何意外,也沒碰到任何官員。唯一看到他們把棺材搬出公寓大樓的,是個半夜失眠,名叫皮爾岑的失業工程師;他們對他說,住在四十二號的拉撒路老先生臥病多年後終於過世了。第二天下午,皮爾岑太太捧著一盤雞蛋餅乾來到四十二號房,赫然發現一位形容枯槁的老先生,帶著三位身穿黑色和式晨衣、美豔但舉止不甚端莊的女子坐在矮凳上;他們的衣服上都縫了撕裂的絲巾,屋內的鏡子也遮了起來。事後證明,在接下來的七天中,這樣的裝置擺飾對薇莉夫人的恩客來說還挺新鮮的;有些人因此完全失去狎妓的勇氣,有些人卻覺得在死人房裡做愛彷彿犯了褻瀆的禁忌,因此感覺格外刺激。
喬瑟夫爬進棺材裡,躺在這一度是布拉格猶太人希望所寄的空殼旁;經過十七個鐘頭後,火車接近波蘭與立陶宛邊界的小鎮歐辛雅尼;由於兩國鐵路的軌距不同,乘客和貨運都必須在此停留六分鐘換車,從蘇維埃監造、漆黑發亮的快車換成沙皇時代老舊怒吼的慢車,也從波蘭的鎮壓臣服換成波羅的海國家的菲薄自由。巨大的史達林級火車頭平穩安靜地駛進月台,發出一聲善感中甚至有些哀傷的嘆息,讓人頗為訝異。車上乘客陸續下車,動作大多非常緩慢,彷彿生怕因表現出急切或緊張的情緒而引起不必要的注意。這些乘客中有很多人和喬瑟夫‧卡瓦利年紀相當,穿著繫腰帶的外套和燈籠褲,頭戴敬虔派的寬帽,井然有序地朝著移民和海關的官員前進,他們跟當地蓋世太保的特務代表都在一個房間裡等著,房裡有座圓火爐,燒得屋子裡熱過了頭。月台上的腳伕是群可悲的老弱殘兵,有些人看起來連帽盒都拿不動,更別說是扛起巨人的棺材了;他們打開魔像和跟著一起偷渡的夥伴所乘坐的貨車廂車門,瞇起眼睛,滿臉疑惑地看著眼前的重擔,他們不但要把貨物卸下車,還得扛到二十五公尺外等著載貨的立陶宛貨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