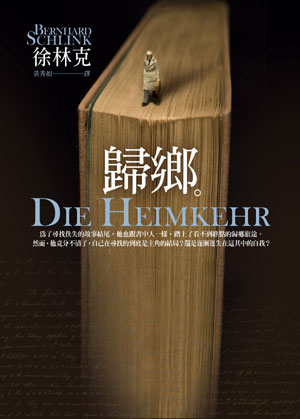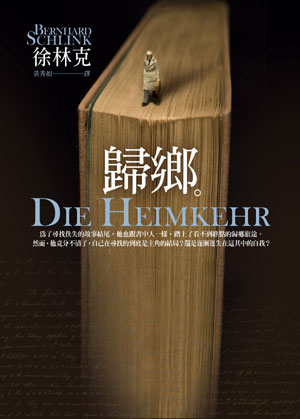內容試閱
4
當我躺在床上時,從未聽過腳步踏在鵝卵石上的聲音。我的祖父母晚上從不外出,也不見有人來訪。與他們共度幾個夏天後,我明白了,他們在傍晚工作。
一開始,我從未想過他們靠什麼過活。我知道的是,他們賺錢的方式和我母親不同,並不是早上出門,下午回家。我也知道,桌上出現的許多食物──但不是所有食物──都來自花園。我甚至已經知道「退休金」的意思,卻從未聽祖父母說過這些。從前,我在購物途中或家中走廊上,聽過上了年紀的老人談論退休金時發出的怨言。因此我從未將他們當成退休老人,也從未想像過他們的經濟情況。
祖父過世後留下了他的回憶錄,這時,我才首次得知他來自什麼地方、曾經做過哪些事、靠什麼過活。他很喜歡在散步或漫遊時說故事,卻甚少提到自己的事,但其實他有很多能說的故事。
他應該可以告訴我關於美國的事。十九世紀的九○年代,因為山坡滑動,掩埋了房子,毀壞了園圃,造成村民傷亡而引發移民潮,他的父親和村中許多人一樣,攜家帶眷遠赴美國,這些孩子將成為勇敢的美國人。他們先搭火車到巴塞爾,接著乘船到科隆,然後繼續搭乘火車、船與汽車到漢堡、紐約、諾克斯維爾與漢茲堡──他的回憶錄中提到了雄偉的科隆大教堂、遼闊的呂內堡草原、寧靜而又波濤洶湧的大海、自由女神像的問候,遇到較早移民美國,已獲成功或遭遇失敗的親戚。祖父的兩個姊妹在漢茲堡過世,但一個心腸冷硬的親戚卻不讓她們長眠在其經營的墓園中,只願讓她們葬在墓園旁──於是我終於瞭解那懸掛在祖父母臥室中,用兩塊木板標示的可憐墳墓照片的由來,那照片攝於一個小巧玲瓏、有著一扇石門,由鍛鐵柵欄包圍的墓園前。這些新移民雖能適應新生活,卻不快樂,他們患了鄉愁,一種可能致命的疾病。祖父的回憶錄中提到,村中的教堂經常宣讀、或於教區紀事錄中記載「某某人」在威斯康辛、田納西或奧勒岡州,因濃重鄉愁而過世的消息。移民第五年後,出發時的六口之家只剩四人,帶著村中木匠製作的大行李箱返回故鄉。
祖父原本也能告訴我義大利與法國的事。當他學會紡織與紡紗的技術後,曾在杜林與巴黎工作多年,他的回憶再度披露了他對造訪風景名勝、認識風土人情有多感興趣,另外還有微薄的工資、惡劣的居住環境、皮耶蒙區男女工人的迷信、天主教與「政教絕對分離」間的衝突、法國民族主義的壯大……他的回憶也揭露了鄉愁對他的折磨。他接掌瑞士紡織廠的管理工作,娶妻生子、建立家庭,在瑞士的土地上買了棟房子──終於,他不再違背自己的天性,而是與其共存。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他換到另一家德國紡紗廠擔任管理階層,但無須放棄在瑞士的家,於是他成了每天進出國境之人,直到一次世界大戰後,通貨膨脹導致他的薪資在德國、尤其在瑞士變得一文不值時才結束。當時他試著及時搬回還有點剩餘價值的物品,以平衡損失。直到今天,我仍在使用一條相當結實、耐用且沉重的毛毯,那就是他從一所已廢棄的德國野戰醫院搬回的眾多物品之一。由於縫製馬氈是健康強壯的婦女才能從事的工作,即將臨盆的懷孕婦女無法勝任,所以祖父又接下一家瑞士紡織廠的管理工作。
他一直保持對德國的忠誠,總對德國人在異國的命運感同身受──也許因為他想到,他們必定飽受思鄉之苦,就和他從前時常經歷的一樣。當祖母烹煮食物時,祖父總在一旁幫忙,他的工作就是將盛著已清洗但仍然潮濕的沙拉的金屬網拿到門外甩乾。但是一次又一次,他過了很久都沒回到屋內,於是祖母要我去找他。我看到他站在門前,若有所思地看著因揮動金屬網而散落在石板上的水滴。我問道:「怎麼啦?爺爺?」是水珠讓他想到了分散世界各地的德國人。
祖父母經過了一次世界大戰、全球性流感與通貨膨脹的考驗,祖父也成功接管瑞士的紡織廠,取得兩項專利後,轉手賣出得到豐厚的利潤,然後兒子終於誕生了。從此刻起,祖父的回憶便間或黏貼在一頁頁相簿上:爸爸戴著紙折的帽子,騎著竹馬;一家人坐在樹蔭下的桌旁;我爸爸穿著西裝、打著領帶,到高中參加新生報到;全家人騎著腳踏車,每個人都單腳著地,另一腳踩在踏板上,好像馬上就要出發。某些照片則散置於回憶錄中。學生時代的祖父、剛成為年輕丈夫的祖父、退休的祖父,以及去世前幾年的照片。他看起來總是嚴肅、悲傷、孤孤單單,彷彿無法察覺他人的存在。而最後一張照片上的祖父,年老瘦弱的脖子突出於寬鬆的襯衫領口,上面頂著一張皺紋滿佈的臉,如同烏龜將頭伸出殻外;他的眼神變得畏怯,內在的靈魂已準備隱退至獨來獨往、不與人交際以及固執的外表後方。他曾告訴我,他終生飽受頭痛之苦──從左邊的太陽穴開始,經過左耳,延伸到後腦──但這「不值一提」。他從未對我提及他的憂鬱,他甚至不知道憂鬱、孤單與膽怯都能經由診斷而一一確定其名──但當初又有誰知道呢?然而他也極少出現嚴重到無法站立或不能工作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