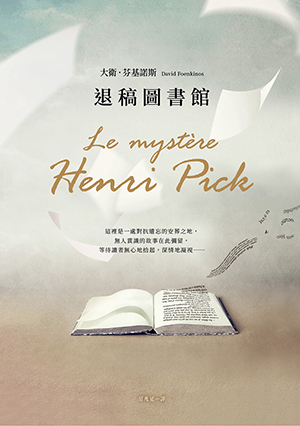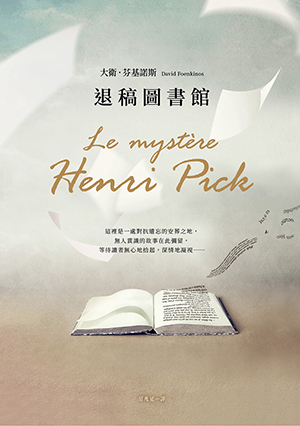內容試閱
*
瑪嘉麗並不特別喜歡閱讀,但身為養育兩名稚齡男孩的媽媽,她必須快點找到工作,尤其是她丈夫只有一份雷諾車廠的兼職。法國本土製造的汽車愈來愈少,危機在這一九九○年代初期開始生根常駐。在簽署工作合約的當下,瑪嘉麗想起丈夫的兩隻手,一雙總是沾滿油汙的手。這種不便不可能發生在即將成日與書本為伍的瑪嘉麗身上,兩者有著根本的差異。從兩人雙手的角度來看,這對夫妻各自擁有南轅北轍的職涯方向。
說到底,顧維克還挺喜歡工作時有個以平常心看待書本的人作伴。他承認我們可以和同事融洽相處,而無需每天早上談論日耳曼文學。顧維克負責提供讀者建議,瑪嘉麗管理後勤,一搭一唱和諧完美。瑪嘉麗不是那種會質疑主管決策的部屬,但仍忍不住對退稿書的想法表達自己的疑慮:
「何必要存放這些沒人要的書稿?」
「這是來自美國的構想。」
「所以呢?」
「是為了向布勞提根致敬。」
「誰?」
「布勞提根,您沒有讀過《夢見巴比倫》嗎?」
「沒有,這不重要,反正這是個怪點子,而且您真的希望他們親自過來這裡寄存書稿嗎?到時候我們得要應付這一帶所有的神經病,大家都知道作家是瘋子,那些沒能出版的作家只怕會更嚇人。」
「但他們總算能有個立足之地,就把這當作是慈善事業好了。」
「我懂了,您希望我當個失敗作家的德蕾莎修女。」
「對,差不多就是這樣。」
「……」
瑪嘉麗逐漸接受這是個立意良善的構想,懷著一片善意投入籌備工作。期間,尚皮耶在專門報刊上刊出小廣告,特別是《閱讀》和《文學雜誌》,鼓勵每一位有意將書稿寄存在退稿圖書館的作者親自跑一趟克羅宗。這個構想立刻大受歡迎,吸引了許多人前來。某些作家大老遠橫越整個法國,到這裡卸下他們失敗的果實,過程猶如一趟朝聖之旅,是屬於文學界的孔波斯特拉。長途跋涉數百公里只為告別無緣出版的缺憾,其中蘊含十足的象徵意義,而這條路的終點就是埋稿之處。或許在克羅宗所在的這個法國省區裡,那號召力更是銳不可當,因為它名叫菲尼斯泰爾,意為大地的盡頭。
*
歷經十年光景,圖書館最後存放了近千份書稿,尚皮耶成天端詳它們,著迷於這些無用珍藏的力量。二○○三年,他生了一場大病,在布列斯特的病床上躺了好一段時間。這場疾患對他來說有兩重痛苦,他寧可搞壞身子也不願意離開他的書本。就算躺在醫院的病房裡,他仍持續向瑪嘉麗發號施令,密切掌握文壇動態,盤算著需要採購的書籍,什麼都不許錯失。他把最後的氣數用在自己始終難以忘情的書本上,但大家似乎不再對退稿圖書館感興趣,他對此感到難過;最初的三分鐘熱度退燒後,只剩下坊間的好口碑讓這項計畫得以苟活下去。美國也一樣,布勞提根圖書館開始面臨困境,沒有人願意收留這些被遺棄的書稿。
返回工作崗位的顧維克形銷骨立,任誰都看得出來他時日無多。地方居民出於某種善意,突然間感染了一股借書熱潮,但幕後的推手其實是瑪嘉麗,她明白這將是尚皮耶最後的幸福。疾病讓尚皮耶變得虛弱,他沒有發覺突然湧入的讀者其實都並非自願前來,而因此深信自己傾注一生的心力總算有了結果。巨大的滿足感撫慰著他,他準備離開了。
瑪嘉麗還拜託了幾位朋友隨便寫本小說,用以填補退稿書的架上空間,甚至連自己的母親都沒放過:
「可是我不會寫作。」
「所以現在正是時候,妳可以寫一些往事。」
「我什麼都記不得了耶,而且我常寫錯字。」
「根本沒人在乎,我們需要書稿,就算是妳的買菜清單也行啦。」
「真的嗎?妳覺得會有人想看?」
「……」
瑪嘉麗的母親最後選擇抄寫電話簿。
創作打算直接存放在退稿圖書館的書,並不符合這項計畫的宗旨,但無所謂了。瑪嘉麗這幾天搜羅而來的八份手稿令尚皮耶開心極了,他將之視為熱潮回溫,表示一切都還有希望。他沒剩多少日子可以見證圖書館的成長,於是要瑪嘉麗答應他至少會保存過去這些年累積的書稿。
「我會的,尚皮耶。」
「這些作家信任我們……不可以辜負他們。」
「我保證它們待在這裡會很安全,這裡永遠會保留位置來收留沒人要的稿件。」
「謝謝。」
「尚皮耶……」
「怎麼了?」
「我想要謝謝您……」
「謝什麼?」
「謝謝您送我《情人》這本書……好美的故事。」
「……」
他牽起瑪嘉麗的手,久久都沒有放手。幾分鐘後,瑪嘉麗一個人坐進車裡才開始流淚。
*
隔週,尚皮耶.顧維克在床上嚥氣。大家紛紛談起這位會讓人很想念的有趣人物,但沒有幾個人參加在墓園中為他舉行的簡樸喪禮。這男人最後會留下什麼?這天,我們或許可以明白當初他堅持要創建和拓展退稿圖書館的原因:那是一處對抗遺忘的安葬之地。之後不會有人來他墳前追思,就像沒有人會特別去閱讀被退件的書稿一樣。
*
瑪嘉麗當然遵守了保存書稿的承諾,但卻沒時間持續壯大這項計畫。過去幾個月來,市政府千方百計找地方撙節支出,特別是文化方面的開銷。顧維克過世之後,瑪嘉麗負責打理圖書館,連想聘用一名臨時人員也不行,一切由她一人包辦。最裡頭的書架漸漸遭到忽略,塵埃覆蓋在這些無主之言上。瑪嘉麗因工作而分不開身,少有心思去關注這些書稿,她怎麼也沒想到存放這些退件書稿的嘗試將會徹底改變她的人生。
***
黛兒芬.戴斯佩羅因為工作的關係,已經在巴黎住了快十年,但她始終覺得自己是個布列塔尼人。她的個子看起來比實際上更高大,但這與高跟鞋無關,很難說清楚為什麼有些人就是有能耐壯大個頭兒,是因為理想抱負、因為童年備受關愛,還是因為篤信自己前程無量的緣故?或許這些都有一點。黛兒芬是個令人想要傾聽和追隨的女子,魅力四射卻從不盛氣凌人。母親是位法文老師,她自幼便與文學為伍,小時候成天過目母親班上學生的作業,著迷於上頭紅色的批改字跡。她仔細打量錯字和拙劣用詞,從此銘記不該犯下的錯誤。
高中會考結束,黛兒芬前往雷恩唸文學,但她一點都不想成為老師,她的夢想是進出版業工作。每年暑假,她會安排自己到出版社實習,或從事任何能讓自己接觸文學圈子的差事。她很早就接受自己沒有寫作的才能,但也不因此感到沮喪,一心只想著一件事:和作家們共事。第一次見到米榭.韋勒貝克時,那股流竄全身的悸動她仍記憶猶新。當時她還是法雅出版社的實習生,韋勒貝克的《一座島嶼的可能性》就是由法雅出版,有一次他短暫在黛兒芬面前停留,倒不是真的在打量她,而比較像是要聞嗅她。黛兒芬支吾地說了聲您好,不過對方沒有回應,但這卻成了她眼中最難忘的交流時刻。
等到週休回父母家,她竟能對這個無關痛癢的時刻滔滔不絕一個鐘頭。黛兒芬很崇拜韋勒貝克,欣賞他對小說的獨到見解,耳聞這位作家引發的眾多爭議,她只感到厭煩,韋勒貝克的文采、絕望、風趣其實更值得大家議論。她提及韋勒貝克的口吻就像兩人是舊識,彷彿在走廊與他擦肩而過,就足以讓她對其作品擁有比其他人更深刻的理解。黛兒芬高談闊論,爸媽一臉莞爾地看著她,基本上他們教養的理念在於盡其所能培養女兒的熱情、興趣和讚歎事物的能力,就這一點來看,他們是相當成功的家長。黛兒芬發展出一項本事,能夠感受催動文氣的內在脈動,當時每一位認識她的人都認為她前途無量。
結束在格拉塞的出版實習之後,黛兒芬獲得錄用擔任新進編輯,這個職務少有像她如此年輕的臉孔,但她的一帆風順其實是天時地利配合的結果。黛兒芬初入出版社時,高層正好希望為編輯團隊拉皮並增加女性員額,社裡交辦她負責幾位作家,坦白說都不是什麼重量級的人物,但他們都很開心有一位年輕女編輯全心全意的照料。只要有些空閒時間,黛兒芬也負責瀏覽郵寄來的投稿作品,勞倫.比內的第一本小說,關於納粹親衛隊員海德里希的驚人作品《HHhH:希姆萊的大腦叫作海德里希》,就是她提議出版的。當初看到這份稿子,黛兒芬立刻衝到格拉塞社長奧利維.諾拉面前,懇請他用最快的時間讀完這本小說。她的滿腔熱情有了回報,格拉塞簽下比內,剛好就在伽利瑪出版社找上他之前。幾個月後,這本小說榮獲龔固爾首本小說獎,黛兒芬.戴斯佩羅也因此在出版社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