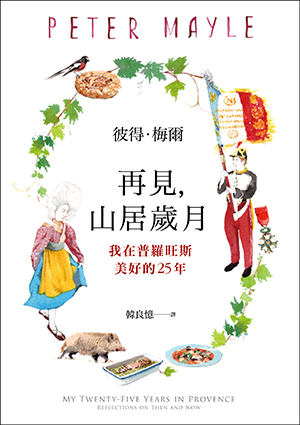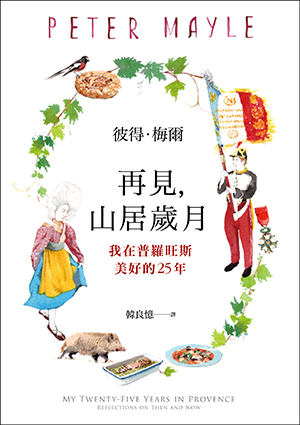內容試閱
一切始於天氣忽然變好。我和妻子珍妮為了躲避英國夏季的爛天氣,來到蔚藍海岸,想在風光優美如詩之地,好好地度假,為期兩週。眾口皆云那裡一年當中足足有三百天陽光普照,我們去的那一年偏偏就不是這麼回事,老天動不動就下起滂沱大雨。海灘上的遮陽傘濕透,傘布扁扁的,變成一團團;那些一身古銅色肌膚、負責巡邏海灘的年輕人擠在沙灘小屋中,泳褲濕答答。尼斯海濱英國人漫步道邊上的咖啡館裡,坐滿悲慘的父母和耍性子的孩子,大人原本答應小孩可以弄潮戲水一整天。《國際前鋒論壇報》上有條消息說,熱浪正襲擊英格蘭。我們準備離開尼斯,希望熱浪能延續到我們返家時。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需要得到某種慰藉。我們考慮越過邊界到義大利,要麼跳上航向科西嘉的渡輪,要不就開一大段路,南下巴塞隆納,趕過去吃晚飯。不過我們後來決定探索法國,不走高速公路,轉而行駛沒那麼寬廣的次級道路。我們心想,就算下著雨,沿路風光也會美麗一點、有趣一點,勝過加入主要幹道上由卡車和露營拖車形成的北上車流。再說,我們對法國的印象始終局限於巴黎和蔚藍海岸,接下來所到之處將是全新且未知的領域。
***
我們一邊喝著粉紅酒,一邊又瞧了瞧地圖,發覺呂貝宏山脈北側散落著好些村落。看來大有可為,而且從那裡回英國多少算是順路。我們吃了一頓恰到好處的普羅旺斯午餐,菜色有芥末兔肉和味道特別細緻的蘋果塔,送餐給我們的侍者簡直像樣版人物── 白圍裙、大肚腩,那一把八字鬍更是濃密得教人過目不忘── 我們蓄勢待發,不論迎面而來是什麼樣的崇山峻嶺,我們都作好準備。
我們駛離艾克斯,天空漸漸雲開日出,我們越往前走就看見越益大片的藍天。太陽依舊未露臉,但是下午的天氣越來越舒服。當我們遠離艾克斯,來到鄉間時,景色的轉換讓這個午後更顯宜人,風光優美而遼闊,常是一片又一片的荒野。葡萄園和向日葵花田遠遠多於房屋,眼前所見的房舍屋宇又是那麼迷人──石塊飽經風霜,屋瓦褪色,綠蔭蔥蘢,屋旁不是有兩三棵古老的梧桐樹,就是有兩排夾道的絲柏。我們後來才發覺,這正是典型的普羅旺斯鄉間風景,而我們當場愛上這般情景,且深愛至今。
空曠的田野間或變成一座座村莊,村中教堂的尖塔居高臨下,統領著塔底那一堆零亂分布的石屋。有幾幢屋子樓上的窗口晾曬著當天清洗的衣物,在我們看來,那是一個徵兆,顯示村民正等著陽光照耀,而在氣象預報這件事上,當地人始終是專家。果然,當我們駛入地圖上的「呂貝宏自然區公園」時,太陽出來了,陽光燦爛又歡暢,令萬事萬物看來鮮明而潔淨,大地景觀如蝕刻畫一般鑲在天邊,在尼斯度過的那些灰暗的雨天簡直像出現於另一個星球。
這會兒,我們可以遠遠地往呂貝宏山瞧上兩眼。山脈走向長而低矮,山勢看來並不崎嶇險峻,是讓人看著舒服的山。呂貝宏山甚至有條馬路看似從南到北,穿山越嶺,而我們正要往北走。我們在盧瑪杭(Lourmarin)村外選了這條路,朝向北方,可是這條路只有頭幾公里是平直的瀝青路,跟著就變得七彎八拐,那是我頭一回坐在車裡卻覺得暈船。雪上加霜的是,路面狹窄,往往一側是陡峭的岩壁,另一側為千丈懸崖,還有對向來車。來的若是機車,倒也不難閃躲,雖說有些騎士可真是把馬路當賽車道;若是汽車,倘若我們緊挨著岩壁,就勉強仍可通行。拖車和露營車則構成挑戰,尤其在轉彎處,我們拚命靠向一側,差一點就要擦上岩壁。我們提心吊膽,屏住呼吸,珍妮非常明智地閉上眼睛。
馬路總算逐漸變平變寬,我倆鬆了一口氣。路標指向文明的前哨 ── 奔牛村(Bonnieux),這村子美如風景明信片,地勢居高臨下,屹立於山頭,山谷風光一覽無遺。我們在地圖上查找下一站,目光被「波希村」(Village des Bories)這一行粗體字吸引。我們心裡直納悶,波希是什麼啊?是享有特權的小部落成員,可以建立自己的村落嗎?也或許是稀有高山動物的庇護區?還是說,這年頭人心如此開放、愛自由,那裡搞不好是天體村?我們決定去瞧瞧。
我們好不容易來到那村落,一個天體人士也沒見著,眼前是一幢幢非凡獨特的小屋,由採自當地的六吋厚石岩板堆砌而成,完全沒有水泥。這二十八幢波希小石屋的外觀有點像巨大的蜂巢,建於十八、十九世紀。有羊圈、烤窯、一間養蠶室、牲口棚和穀倉,想當年可都是符合生活所需的現代化設施,且都保存良好。
沉浸於歷史後,難免需要吃點、喝點什麼,好提神醒腦一下。幸好再往前走一會兒,勾德(Gordes)村裡就有。勾德如今已成典範,兼具田園之趣和世故老練之妙,有好旅館、餐廳和精品店,夏季時有絡繹不絕的遊客,然而彼時它還是個寂靜、幾乎無人居住卻美得驚人的小村,有如石頭搭建的電影場景。
勾德歷史可追溯至公元一○三一年,我們橫越主廣場時,一邊走一邊不難想像,此地自開村以來並未改變多少。村屋的外觀呈現著淡淡的蜂蜜色澤,那是千百年來的陽光留下的痕跡。多年來,不時有密斯脫拉風吹颳過整個普羅旺斯,石塊的表面皆因風化作用而變得光滑。廣場邊上有家咖啡館,更給這個下午增添樂趣。
我們坐在露天座位上眺望周遭的鄉野,說不定就是在那一刻,夫妻倆起心動念,想要改變生活。我們都覺得,要是能居住在此地,豈不妙哉。我們在職場打滾已久,在倫敦和紐約工作多年,已準備好要過簡單一點、陽光多一點的生活了。
***